最近这一星期,我在微博热搜上看了两部电视连续剧:中国原生家庭图鉴——阿耐同名小说改编电视剧《都挺好》和真的“Bigbang”——由李胜利引发的娱乐圈大地震。


屏幕前的我,诅咒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和衣冠禽兽的“明星”,议论着苏明玉到底要不要和解,抹着眼泪看“李胜利瓜藤”牵扯出的女性受辱、被害案件,为最初曝光李胜利事件的记者姐姐竖起大拇指……

每一件事都像是在眼前发生,每一件事又像是会马上消失不见——除了单位福利和打折促销,刚刚过去的“三八妇女节”要展现给社会的真正含义以这样的方式提醒着我们:
女性首先是人,其次是女人。
实现男女平等这件事,不知还需多久,我们只知道权益不是他人给予的礼物。
挣扎在“被爱”与“被尊重”的漩涡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福。其中,
父母的教育方法、其自身的思想观念都是造成不幸的慢性毒药。
在《都挺好》中:二儿子毕业旅行要2000,给!女儿补习功课要1000,没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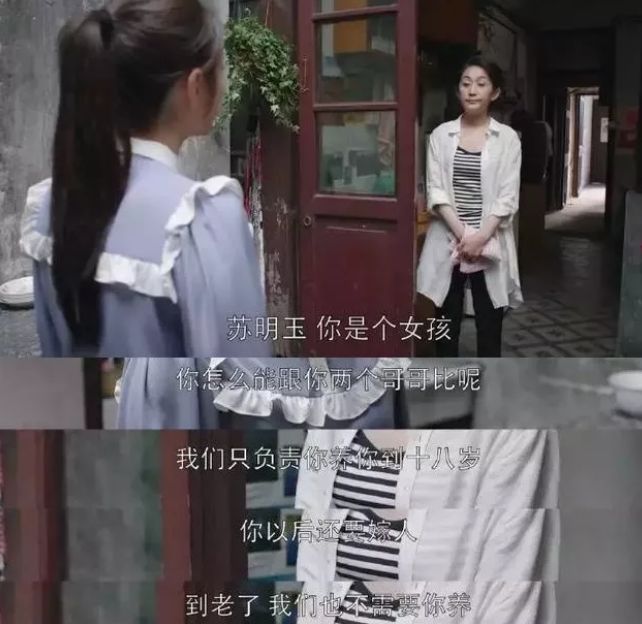
大儿子出国留学——卖房子也要上!女儿要考清华——上师范吧,便宜,不想去?那就别上了。

在妈妈极其强势的“重男轻女”观念中(再加上爸爸的自私自利和软弱),这个表面上“都挺好”的家庭,实际上,分崩离析,一片狼藉。
于是,微博上出现了关于苏明玉和樊胜美谁更惨的讨论——遇上贵人、干脆果敢的苏明玉至少能事业有成,而普通平凡、却心比天高的樊胜美只能被拖累一生。
其实,她们谁也没有比谁更幸福,都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从本应最亲近的人那里收获了一生的痛苦。
去年冬天,微博上曝光了出租房里一段监控视频:视频中,母亲突然将正在吃饭、写作业的女孩推到、拳脚相向,但另一方面却对儿子偏爱有加;其父亲更是一进门便踹了女孩一脚。
令人心寒的是,仅在这段被曝光的视频中,女孩就被虐待了6分钟,而更令人心碎的是被打女孩不哭不闹、习以为常的反应——仿佛
遭受了家庭带来的痛苦,只能自己生出坚硬的外壳。

我们无法看见这个女孩的未来,但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混”出来的是苏明玉,“混”不出来的大概最多能活成樊胜美的样子。
然而,苏明玉的顺遂职场太过理想,可遇而不可求。即便干脆利落、杀伐决断如她,不还是一样要
一边保持着自己的自尊,一边被原生家庭捆绑
一生
,挣扎在“被爱”与“被尊重”的漩涡,剪不断理还乱。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像是游戏中的升级打怪。即使我们能在父母的爱中长大,还会有来自社会的“恶意”在随时等待着我们的挑战。我是女孩子,爷爷奶奶重男轻女,但我很幸运,从小妈妈告诉我:“女孩子并不比男孩子差。女孩子不可以看轻自己。”
小时候,我比较调皮,被叫“假小子”,老师戳着我的脸说:“班里有几个女孩子像你这样。”我心里不以为然,但长大后回想,其实大多数孩子成长的全程都充斥着这样的声音。
中学时期,我们可能会听到:“别看女孩子初中学习好,高中就跟不上了。”
文理分班,我们可能会听到:“你一个女生怎么学理科了?”当然,理科班女生少也是事实。但并不代表女生学理科不正常,男生学文科也同理。

过了四年自由快乐的大学时光,才知道之前的评论与进入社会之后的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暂且不谈职场性骚扰,仅仅只是偏见就很可怕:“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
“你怎样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入职面试时这样的提问对于女性求职者是家常便饭,也是理所当然,而这些问题的底色全是悲凉和无奈。更别提,前几年坊间流行的那种说法:“人分三种:男人、女人和女博士。”
我想,除了男艺人,男性大概永远不会在工作场合听到以上问题。
3月7日,2019中国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会上发布了《2019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联合国妇女署的林加蕾女士表示,尽管女性的领导力不输男性,但现实中男性领导者的数量却远多于女性,级别越高差距越明显。中国上市公司中,女性领导者只占总数的9.4%。

图片来源:论坛官网
她认为,导致此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性别偏见造成的
同工不同酬、限制晋升机会
的现象,另外社会中对于
男女不同的性别期待
,比如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也限制了女性发展。据统计,中国女性每天承担的无偿家务劳动时间占到她所有劳动时间的44.6%,是男性的2.4倍。
为什么?
男女有别
吧。毕竟,都9102了,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农村部分地区,还有许多诸如家族聚餐时,女人不能上桌的习俗。
都是“男女有别”惹的祸?
很多公式化的表达对什么是自然生理的,什么是个人希望的,只会含糊地一带而过,男女差异究竟来源于自然本性,还是仅仅因为社会秩序需要它被当成人们愿意的,这个问题悬而未决。
在我国古代,最初的“男女有别”指的是“大部分时间男女不应在一起,必须在一起时则应避免任何身体上的接触”。此后,男女从身体上分隔开的概念被逐渐类推到行为上的不同:
男、女应分工做不同的事,或同样的事负责的内容不一样,即男女社会分工不同。
“男女有别”的概念在有意无意中被社会、甚至是女性自己强化。这
到底是由于社会秩序的需求,还是个人的希望,从来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缠足一直被很多人视作在以男权为主的中国家庭体系中,女性受制和受害的证明。这种理念根深蒂固,在此不多做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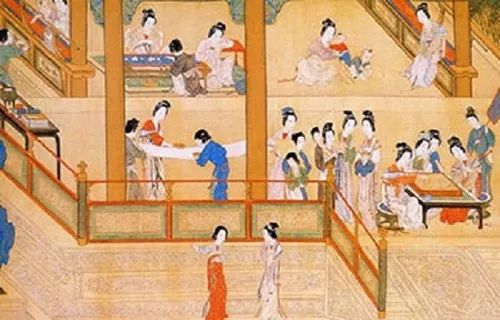
在2005年出版的“海外研究中国丛书”中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简称“《闺塾师》”)一书中,作者高彦颐提出了另一种视角:
缠足已成了残酷的、父权的“旧中国”压迫下的女性的绝对特性,
问题是她们的个人声音和阶层差异,被淹没在一个否定的普遍历史中。“旧中国”似乎是无时间限制的,其中的女性是姓名不详和一样的,每个人因此被剥夺了历史。
作者认为,在古代女子缠足的发展中,女性对缠足专有的仪式及其背后的信仰,都说明了这一习俗绵延长久和传播广泛的原因:虽然缠足对男子有着吸引力,但如果没有相关女性的长期“合作”,缠足不可能长存千年之久。《闺塾师》所要表达的是,
儒家传统的持续性和千千万万女性艰难取得的成就在女性史上不容忽视。

然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女孩开始缠足的年龄(6岁左右)与男孩搬出女性闺房而进入宗学或私塾
开始接受
指导的年龄一致。这两种行为虽说均是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与教育:
但却通过缠足的方式,分离领域学说被镌刻到了相同年纪女孩子的身体上。
缠足的初衷和女性对缠足的态度,我们都无法确切的知道。我们也无法对历史中的人物感同身受,历史长河中“幸存”的诗词歌赋体现的女性的只言片语也只能体现少数上层社会女子的生活状态,
但是在
最初逐渐构建起来的“男女有别”的社会秩序中,事实上,形成了几乎全社会范围内理所当然的“男尊女卑”。
性别刻板印象是对男女两性的压迫,无论男人女人都应当设法摆脱这种压迫,争取过上自由的生活,使每一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