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白嘉轩是族长,他是典型的“守成者”,在他看来,乡约就是天经地义的乡村规范,他是怀抱着田园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而他的对手鹿子霖,是标准的“投机者”,抓住新时代所带来的一切机会,他们才是白鹿原真正的主宰。白嘉轩的感召力只能停留在昔日的荣耀里,他维护的是过去的尊严,而现实中,贪婪人格的鹿子霖往往能获取最大的利益。
以身体原始欲望行走的黑娃和田小娥是白鹿原上的异端,他们是“本能者”,他们的生命如电闪雷鸣。活得虽然短暂,可是那种轰轰烈烈活法,却是惹人瞩目的。这些人物,在这片土地上,按照陈忠实的话说:“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了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点击上图,购买《三联生活周刊》总第700期封面系列文章:《巨变时代的中国人格类型:白鹿原寓言》
点击上图,购买《三联生活周刊》总第700期封面系列文章:《巨变时代的中国人格类型:白鹿原寓言》
很多人觉得白嘉轩的塑造,是陈忠实唱给白鹿原的一曲挽歌。作为一个胸怀仁义、心有大志的族长,最后被社会浪潮挤落在社会角落,家业和族事都趋于没落。这是他人生和他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没落。
浓缩了传统文化负荷的白嘉轩所面对的,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乡村的衰落,是晚清至民国以来的趋势;而基层政权的不断整合,使得宗族和他所代表的儒家正统观念更无容身之所。

电影《白鹿原》剧照,演员张丰毅饰演白嘉轩
白鹿原上有两个代表白鹿精魂的人物,一个是白嘉轩的精神偶像朱先生,另外一个是他的女儿白灵。实际上,这两个人物的不断启示和关联,使得白嘉轩在尘世间的挣扎,不脱离正道。
陈忠实在村里做调查的时候,听老人们讲故事,说到他的某位长辈,从村落里走过的时候,腰永远是挺得笔直的,个子很高,从村里走过去的时候,那些在村落街巷旁喂奶的女人们,都会吓得躲回自己家的院落。这就是白嘉轩的起源点,陈忠实说,族长的禀赋、气性,在那一刻他有了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加上他从“蓝田县志”上抄下来的北宋年间吕氏大儒所制定的“乡约”,自然就融进了这位族长的血液。白嘉轩的人生故事和际遇,开始不断延展开来。
 电影《白鹿原》剧照
电影《白鹿原》剧照
白嘉轩是依照祖宗规矩定下来的族长,可是他在小说开篇就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他的历任妻子的死亡,使他面临着无后的恐惧,也面临着族长在他家断绝的可能性。他“六娶六亡”的故事已经成为乡村的传奇,性在白嘉轩这里,脱离了欢悦的主题,而变成了只有传宗接代的唯一功能。即使是如此,白嘉轩巨大的雄性力量,还是通过小说开篇而传播开来,特别是他初当族长整修祠堂开始,他的强大,从开始的带点生殖崇拜的描写,进而进入到文化层面。
白嘉轩从一开始也是浑噩的。小说开始写他因为风水原因,用鬼祟的装穷伎俩去骗取鹿家的土地的时候,他身上的深藏的文化基因特别的明显。“心里燃烧着炽烈的进取的欲火,脸孔上摆出的却是可怜兮兮的无奈。”他的装腔作势连自己的母亲都骗过了;而他开始的发家史,委实也不太高明,所谓的“种药”,不过是种植鸦片。这一片段同样来自历史事实,清末民初,关中大片土地种植鸦片,当时的游记对这种景象有很多记录。包括斯诺的《西行漫记》里都记载了“沿途的罂粟摇晃着肿胀的脑袋”。白嘉轩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种植鸦片,而是不断重复:罂粟就是罂粟,药嘛。
只有当他的精神导师,也是他的近亲、姐夫朱先生带着他用犁彻底毁灭鸦片田的时候,白嘉轩才感觉到人生的觉醒。朱先生是有现实人物做依据的,理学在清末虽然已经式微,可是在关中还有关中学派,牛兆谦就是关中学派的最后传人。他在乡村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是传奇,类似夜观天象,判断明年如何种植庄稼;或随手一掐,帮人算出走失的黄牛在哪里;甚至他死后多年,被红卫兵挖掘了墓葬,可是里面连墓砖都没有,异常朴素,人们再次传说他生前已经有了掐算,这是他神话遗留多年的象征。不过他真正的价值,在于维系这片土地上的正统观念,向人们传递儒家礼法,包括编纂与众不同的《蓝田县志》,联合南北知识分子,在上海报纸上发表抗战宣言。牛才子的墓葬地离陈忠实家很近,自然使作者升出了崇敬仰慕的心理。
以往白嘉轩是混沌过日子的,可是朱先生不断用各种儒家规范去刺激他,点燃他,包括用最简单平易的歌谣去争取他向善,最典型的如劝他放弃与鹿子霖争夺寡妇地产的那首四句诗文。白嘉轩本来就是有慧根的人,这种日积月累的点化,使他的族长身份逐渐确立起来,他有意把宗族当做他的一切,而社会性的唯一表现,也在他的宗族中:他对当官毫无兴趣,对政治天然疏远,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仁义、内省、自励上,与此同时,他去监督着每一个破坏宗族规范的人,任何有违宗族道德的人,都会被他严厉打击,哪怕是他的亲生儿子。
 电影中滋水县令古德茂亲自送来“仁义白鹿村”的牌匾,从此白鹿村也被人称为仁义庄
电影中滋水县令古德茂亲自送来“仁义白鹿村”的牌匾,从此白鹿村也被人称为仁义庄
做人,成为他的最高追求,交农事件中,长工鹿三代替他出头,他大为感动,就是一句话:三哥,你是人。虽然白嘉轩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是朱先生每每在关键时刻的点化,使他完全成为旧的礼法在乡村生活的典型代表:他买地有限,愿意自己劳动,和长工鹿三关于农活的交流,是真心的交流;他的慎独精神也是严谨的:“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
白嘉轩后来被打断了腰,只能像狗一样行动,当地人都叫他“锅锅儿”,可是,他还是很快下地劳动,不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废物;而且,他在精神上,还是“很硬很直”。就在他的腰被打断不久后,他做出了要修塔震慑住田小娥的妖气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在全村的反对中做出的。满村的人都在田小娥的死宅前烧香企求保护,白嘉轩的儿子、准备继承他的族长位置的白孝武和村民们也都企求他给那“婊子”修庙的时候,他愤怒地走出门,觉得自己哪怕成为孤家寡人,也要造塔去邪——他的凛然之气,是整个村庄在乱世里生存下去的主心骨。他的坚强贯穿了小说始终,到死也没有动摇。
在从朱先生处获得了“乡约”并且将之刻在石碑上的那刻起,白嘉轩的族长身份有了外化的特征。以往自己家门楼上的“耕读传家”还只是代表着他的家风,而严正、清明、繁琐的乡约刻在石头上,并且摆放在祠堂里的时候,他的族长身份获得了某种形式上的确定。一直想辞去学馆职务的老秀才也放弃了回乡,而是想留下来,帮助他在白鹿村教化民众,实践“乡约”。
不过时代的巨变超越了白嘉轩的设计,就在他刻碑立石的同时,鹿子霖当上新政府任命的乡约,直接与他抗衡,而白嘉轩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中也会迷惑:乡约怎么成了官名了?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族长要保护宗族利益,在以往的统治体系下,宗族是政府在乡村统治的顺延,所以双方会有协商空间,可是民国政府没有给白嘉轩这个空间,所以有了“鸡毛传信”交农事件。貌似反对官府的行为其实质还是在行使族长的权力,保护族人不受欺压,他的起事人的身份不是秘密,白嘉轩受到了族人的赞许。也就是与此同时,他与新政府的无法相容也暴露了出来,当他想用自己去换取被监禁的族人的时候,新成立的法院体系已经让他的义举显出挫败感来:新政府的办事人员宣传了民主精神后,让他快走快走,再不走就是无理取闹,破坏革命机关秩序。
在一个乡村不断进行现代化变革的时代,白嘉轩的族长任务显得难以完成。他的壮举尽管还是被四邻传播,但是,仅仅限于整治赌徒,包括治疗大烟鬼,他的努力,仅仅在于恢复乡村日常的生活秩序,所有的公众事务,日益集中在以鹿子霖为代表的新政府手中。村落里所掀起的种种轩然大波,包括军阀的抢粮、国共合作、农民协会,到还乡团对农民协会的镇压,再到抓壮丁抗战,这种发生在乡土之上,却是对旧有乡土传统进行着巨大破坏的各种变化,陡然变得和他没有关系了。白嘉轩本来就不愿从事政治,可是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也并不是他所能从事的。他只能表现出超脱的态度,儿子回家问他,一切权力归农协,这是什么意思。他大喝道:这和咱屁不相干,你该操心自己要办的事情。他买来了轧花机,成为白鹿原上少有的新机器的使用者。
在农协革命失败后,白嘉轩还有挣扎,他代表族人去向准备惩罚农协会员的田福贤和鹿子霖磕头,要求惩罚他的不教导族人的过失。可是田和鹿只是在最表面给予了他尊敬。
 电影《白鹿原》剧照
电影《白鹿原》剧照
在公共事务上的被排斥,使白嘉轩不得不在家庭树立样本。他在家族内把“耕读传家”视为了头等大事,因为害怕失传,所以,他命令自己的儿子在长工鹿三的带领下进山去背粮食,让他们受苦,是为了让他们明白“啥叫粮食”;长子白孝文婚后有贪色迹象,他及时制止,不过,这种制止只是暂时的,遇见真正有破坏力量的田小娥,白孝文宁愿舍弃家业,背离家族而去;他特别喜欢小女儿白灵,可是当白灵开始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家族给自己定下的姻缘的时候,他就开始勃然大怒,最后索性割裂了父女情谊,只当对方死了。在没有政治倾向的白嘉轩看来,白灵加入共产党或者国民党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不能背叛乡村的伦理准则,事关礼教大局的事情,他都不能含糊。
儿子和女儿的背叛,是对他的双重打击。白嘉轩再次显示了他为了礼法而割舍亲情的人格特征,白孝文和田小娥的私情,起初只是杀人的闲话,可是当他在雪夜立在窑洞口,目击闲话被证实的那一刻,他的心境真是惊天动地:“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终点,猛然狗似的向前一纵,一脚踏在窑门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也栽倒了。”能承受一切的白嘉轩不能承担之重,是自己的儿子,一个从小受他严格教育,有潜在族长的可能,而且刚刚主持了惩罚田小娥的男女私情的仪式的儿子,毅然决然地躺在了田小娥的床上,这代表着他所辛苦建立起来的体系的崩溃。他对田小娥的憎恨是发自内心的,两个人代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稳定的、宗法的、严谨的系统,另一个却是无根的、淫荡的、本能的系统,加之田对白家的毁灭性打击,使他在众人反对的时候坚持说,要挫骨造塔,要让对方永不见天日。这位敦厚的长者同时也是个冷血的食人者。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他被击中要害后还站了起来,鹿三明白他,对他说:嘉轩,你好苦啊。可是白嘉轩特别明白维持礼教,必然自己要承受许多痛苦,所以他说:在咱们庄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
也就是这种忍劲儿,使白嘉轩能够在宗族的大事来临之时挺身而出。乡村的求雨、祭祀等仪式还是脱不了族长的领导,白嘉轩的表现,使他无愧于族长的称号。“他用左手再接住一根红亮亮的钢钎儿,啊地大吼了一声,扑哧一响,从左腮穿到右腮,冒出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戳戳直立起来。”这是老族长的最后的辉煌。
随后,是一个曾经熟悉的乡村体系不断崩溃的过程。尽管白嘉轩还在不断地努力去做乡民们的代表,包括去县城营救曾经伤害过他的土匪黑娃,可是,面前的亲生儿子的拒绝让他完全无力:这事比不得族里的事啊。你回去咯。他去营救自己的仇人鹿子霖也是同样的失败,县长完全没有把他的请求当做一件要紧的事情。在颠倒白鹿原的一系列政治风云中,白嘉轩是完全的失败者,昔日县令授予他们的“仁义白鹿村”成为一个久远的梦想,暴动、杀戮、灾祸、国难接踵而来,他完全没有力量在里面起到一点作用,甚至老对手鹿子霖都在依靠阴谋诡计主宰着白鹿村上的风云变幻,而他,只能和他的人生导师朱先生一起,哀叹白鹿原沦为各个党派、各个利益集团的鱼肉。
难怪朱先生去世的时候,白嘉轩在雪野上奔跑着,几次滑倒,巨大的哭吼声能够把房梁上的灰尘都震落下来,他哀号的是:白鹿原上再也没有这样一位好先生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好先生了。
 电影《白鹿原》,老年状态的白嘉轩
电影《白鹿原》,老年状态的白嘉轩
白嘉轩的一生,磨难重重,早年丧妻还只是个民间传奇,可是后来的人生一点不轻松。他在交农事件中虽然是领导,可是却被乡民们指责为缩头不出;大革命中他也被游斗;土匪将之打残;女儿离开家庭后,在延安“肃反”中被杀害,临终变成白鹿来托梦,他才暴露了自己始终埋藏的、对女儿的巨大的感情;族长之位后续无人,几个儿子显然都不是好的人选;家业凋零,儿子们不能守成。可是他还是坚持,凡是出生在白鹿村炕脚上的村民,只要是人,最后都会跪在白鹿村的祠堂里面。他的信念没有改变。不过此时,他只能做一些修订家谱的事,其余任何事情已经与他无关了,有评论者觉得他是抱着“农民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
最后的打击迟早要来,跪在祠堂里面并不代表宗族还受他的控制,儿子白孝文离开祠堂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人迟早要离开原上,白鹿原外面的世界已经打开,村庄已经不是昔日的田园景象。同样是白孝文,最后使用心计,枪毙了起义的、已经彻底在心灵上回归白鹿原的黑娃,白嘉轩就是目睹了这个场面,才“气血蒙眼”,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早年严重伤害了他的儿子,还在给他持续的伤害。不过这种“眼不见为净”的状态,使他的“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和所有器官不再绷紧,全都现出世事洞明者的平和与超脱”。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700期封面文章《白鹿原上的人格类型: 守成者,投机者和本能者》。点击下图,可购买白鹿原系列封面文章。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以下封面图
一键下单「新茶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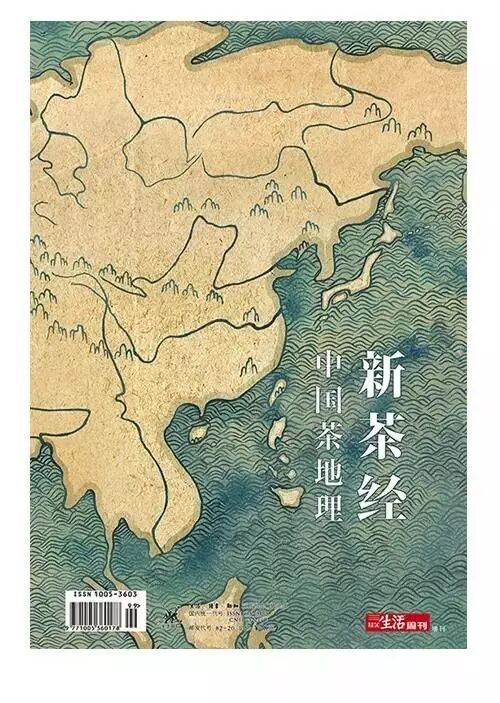
▼ 点击阅读原文,今日生活市集,发现更多好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