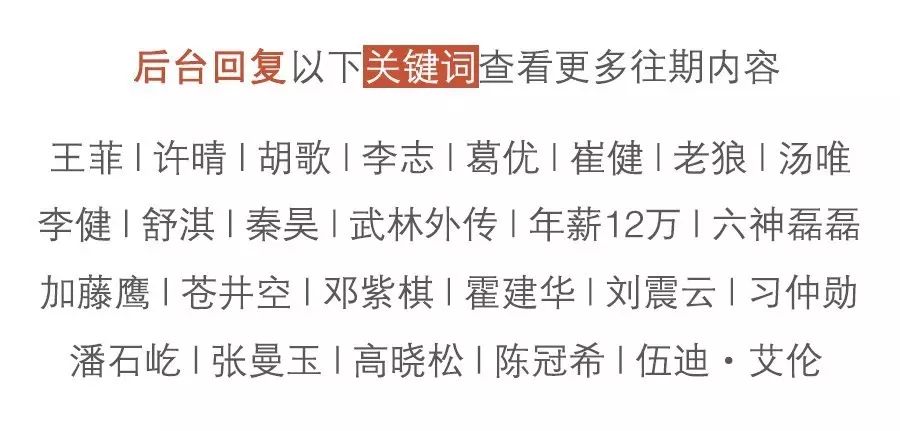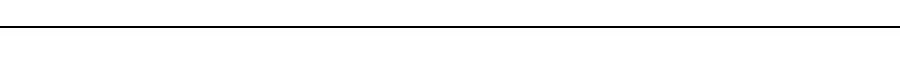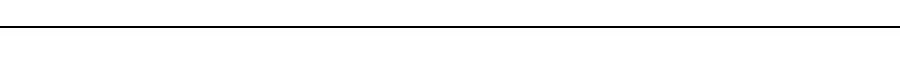大选之外,这是一个“90后”中国女性跨越“两个美国”,试图了解外部世界的故事。
文 ✎ 黄昉苨
编辑 ✎ 卜昌炯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那一晚,嫁给美国人刚半年的陈艾瑜感觉“对美国的所有信任被瞬间删除了”。与她的绝望相对的,是周边社区的平静无事,以及丈夫的保守大家族里特朗普支持者的喜悦。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2016年的这场大选仿佛将国家撕成了两半。”《纽约时报》曾用技术手段,根据投票结果的差距,画出了“两个美国”。
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包括全美超过80%的郡县,它的边界却被沿海地区的民主党支持者所侵蚀。
希拉里·克林顿的美国包括了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它们被包围在特朗普支持者的汪洋大海中,像一串断断续续的大岛礁和小岛链,虽然面积不大,却拥有美国过半的人口数量。
作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成长、在纽约接受高等教育的写作者,陈艾瑜天然属于小岛链上“自由主义共和国”的国民。大选促使她试着“打开一个耳朵去听和我们不一样的声音”,随之而来的圣诞假期则让她不得不随丈夫深入“汪洋大海”,去与和自己政见截然相反的人欢庆佳节。
大选之外,这是一个“90后”中国女性跨越“两个美国”,试图了解外部世界的故事。
尽管在美国已经生活了5年,陈艾瑜在大选之前几乎没见过声称自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美国人。
到美国后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居住在纽约的“自由主义泡泡”中。在她想象里,特朗普的支持者要么是随身带枪、脖子被晒红的白人男子,出门横着走路;要么是住在乡村,从没出过远门的闭塞村夫。她所在的翻译公司有一个白人男同事宣称要投特朗普,陈艾瑜气得跟他“划清界限”,“用最敬业的精神与他保持友好的距离”。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8日,纽约曼哈顿,一名特普朗的支持者在总统大选之夜静观选票结果
但在圣诞假期回家的第一天,她和丈夫就发现屋里添了新装饰——男孩子们的卧室门上,一幅大大的蓝底红边的海报,上面写着:特朗普,让美国伟大复兴!
在位于密苏里州圣查尔斯县的这个白人中产阶级大家庭里,万事都遵循着传统规矩。家族里的男性最常选择的职业是医生或律师,女性则虔信宗教,操持家务;男孩热爱打猎与运动,女孩的心愿是随慈善组织去第三世界服务贫民。
25岁的亨利·克里夫是第一个打破传统的人,他从纽约娶回了中国妻子陈艾瑜,把家安到了远离圣查尔斯县的大城市亚特兰大。当他的弟弟在神学院潜心学习,希望成为神父时,他研究的则是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
陈艾瑜生长在浙江省,在北京读完大学,收到纽约大学提供全额奖学金的硕士录取通知书后,来到纽约,认识亨利。她曾总结夫妇俩的共同点是“都热爱自由”、“叛逆”。
而现在,参加过亚特兰大抗议特朗普游行的年轻夫妇回到家中,只能看着亨利的外公在圣诞派对上对少数族裔客人大谈“特朗普是人民的大救星”。
“我们这儿做生意的人盼特朗普都盼了好久了,你知道吗?”外公对年轻夫妇邀请的来客说,“民主党征税实在太多,小生意根本做不下去,大企业也都跑到国外去,国家都被他们搞坏了……唔,作为律师,我不想轻率使用‘伟大’这个词,但必须得说,我关心美国这些小企业的命运,我的经验告诉我,特朗普上台对这个国家是好事。”
老人家侃大山侃得正起劲,亨利突然从背后冒出来,笑嘻嘻地问:“外公,您可真能说,为什么不对全家人大声说出您的意见呢?”
外公瘪瘪嘴,不再讲话。在这里,避免与政见不同的人聊政治是一种美德。2016年年中,外公身在加州的长子特意在Facebook上@他,给他推荐了《共和党60大佬关于唐纳德·特朗普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来自共和党内特朗普的反对者:
“美国的政治现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特朗普极受欢迎。对此,我们有义务来清晰陈述我等的反对意见:
“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与影响力,他的见解在原则上充满了矛盾与摇摆。他可以在一句话中,从孤立主义摇摆到军事冒险主义。
“他对贸易战的鼓吹,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导致经济灾难。
“他充满恨意的反穆斯林言论削弱了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严肃性。他的言论更威胁到美国穆斯林被宪法所赋予的自由。
“他坚持墨西哥应在美国南部边境筑墙的提议,激发了毫无帮助的情绪,并且建立在一种对我们南部邻国彻底的误读与蔑视之上。
“他彻彻底底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在投入丈夫老家这片红色的“汪洋大海”之前,陈艾瑜通过接触在纽约的知识分子朋友、阅读《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来了解美国。她喜欢何伟、欧逸文这些美国记者对中国社会有同理心的描绘,喜欢这些自由主义媒体在报道中展露的国际主义精神,对公平公正的坚持,以及对弱势群体细致入微的关切。哪怕婚后搬到了亚特兰大,她依然订阅这些报纸杂志,并准备了一本剪报本,每天把报上与中国有关的报道都一一收集起来。
“美国这个地方特别好的一点是,你不用怕自己是边缘族群,越是女性、少数族裔或者有什么残疾,你就越是受优待,生活会比别人容易。”大选前,她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美国人舆论的压力、社会的嘲笑,都是奔着那些最强、最掌握权势的人去的,因为他们相信掌握社会资源的人同时也肩负更多责任,所以有钱有势的人得活在媒体苛刻的审视下,他们的言行不一最容易被人揭发和指责。而普通人的日子可以过得很自由快活。”
也正因为这个信念,大选前《纽约时报》预测希拉里将有约85%左右的概率能赢得选举,陈艾瑜笃信不疑。
把非法移民斥为犯罪分子和强奸犯,反对同性婚姻,无视美国宪法“人皆生而平等”精神,还不止一次对女性口出污言秽语的唐纳德·特朗普,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像是正派人能投下去票的美国总统人选。
大选当天临近半夜,当特朗普赢得选举的局势逐渐明朗之际,一些前所未见的事情发生了:一家在纽约创建的、通过短信为人提供危机心理干预的公益组织(Crsis Text Line)迎来求助高峰,求助短信数量攀升到了平时的8倍,“选举”和“害怕”成了当晚的关键词。凌晨一点至两点,美国预防自杀生命热线(National Suicide Prevention Lifeline)涌入了660个求助电话,是平时的2.5倍。第二天,一些专门服务于LGBTQ青少年的自杀求助热线也被打爆,其中一位负责人告诉媒体,上一次他们机构这么忙碌,还是奥兰多同性恋夜店大屠杀的时候。
政见分歧在家庭中也投下了阴影。回家那天,站在屋后的小溪边,亨利对最小的妹妹说:“特朗普是个大坏蛋!”“对的,你知不知道?”陈艾瑜接着问。
11岁的小姑娘低头沉默了。表情好像有点迷惘,又好像有点受伤。
陈艾瑜一度想象不出该如何面对丈夫的家人,想到他们给特朗普投了票,就难过得不愿与之相处。
对像她这样的自由派年轻人来讲,这次大选结果不逊于另一次“9·11”——被撞倒的高塔,是她们心中对美国的信念:民主就这么容易败给独裁吗?为什么拥有了自由的环境,美国人还是那么轻易被仇恨煽动?
发现贴在家里的特朗普助选海报后,亨利在接下来24小时里都没怎么跟父母讲话,陈艾瑜亦是如此。当晚,他们去见了老朋友:住在中产阶级社区中的自由派老夫妇。他们是他俩在故乡能找到的仅有的聊大选的人。
“老实说,大选后,如果我得知某个人把票投给特朗普,我对他或她的尊重感就会消失一点。”这家的女主人说,“我们从前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你对残疾人得怀着平等对待的心,你不能欺凌弱小,你必须对世界抱有爱意……可是现在呢?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所作所为却完全与此相反。”
“那些非法移民,好多是连饭都吃不上一口的穷苦人,女人,小孩,给一点点工钱就能拼命干活,可是电视上看到的抗议者,吃得好胖好胖,举着对非法移民的抗议牌大吼:‘滚回你们祖国去!’为什么?他们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美国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女主人说得几乎哽咽。
在充满了愤懑以及伤感的氛围中,陈艾瑜问出了那个问题:“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出来阻止特朗普呢?”
“不,我们不能。”对方平静地说。
与陈艾瑜抱有类似情感的民主党支持者可能不在少数,但这里的人更习惯用另一种方式去处理问题:尊重大选结果,同样坚持行使批评与抗议的权利。当选总统后,特朗普与互相抨击多时的美国多家互联网企业高管举行了会议。此前,有些与会嘉宾还曾暗示说想用自己研发的新火箭把特朗普送到外太空去。
现在,他们齐聚一堂。会场上,特朗普称:“你们需要任何帮助我们都会尽力满足。”会场外,谷歌、微软和苹果的数百位员工在一份声明上签名,表示如果政府要创建任何根据种族、宗教信仰或原国籍对人民区别对待的数据库,他们会拒绝参与这类工作。
当选两周后,特朗普到访了对他批评甚多的《纽约时报》总部,成为第一个拜访该报办公室的候任总统。在那里,他会见了记者、职员,与大家座谈,甚至抚着记者弗兰克·布鲁尼的胳膊说:“我一定能让你为我写点好话。”
弗兰克注意到,出现在时报总部的特朗普“没什么热情去调查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或克林顿基金会”,“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愿意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对边境建墙一事绝口不提”并且“毫不犹豫地否定白人民族主义者”。
“在我们的会议快要结束时,他甚至预言自己或许可以完成前任们不能完成的事业: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建立持久的和平。”弗兰克随后在专栏文章《在时报总部会见一个渴望被爱的川普》中写道,“假如这真的成功了,我们到时候一定会写非常非常好的好话。”
“我想,要说我们能够做什么,答案就是米歇尔·奥巴马说过的那句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当别人走向道德洼地,我们选择继续往高处行)。我们应当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事,关爱他人,影响身边的人;当特朗普干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抗议,去抵制。”饭桌上,女主人擦擦眼角,告诉陈艾瑜,“也许人们的情绪就像钟摆一样,一时会摆到极端的地方,但终究会平静下来。不管到了什么时候,爱,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这家男主人收到过同社区的居民在邮件群里传播的假新闻,主要内容是“自从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丢失了多少工作岗位,经济衰退了多少”。他想跟这些消息较个真,于是一一核查了假新闻中的数据,指出错误,发回了邮件群里。
然后邻居愤怒地回应:“你为什么要用真相来歪曲我们的本意?”
经济,是很多分析家指出的特朗普在摇摆州获胜的原因。大选后,陈艾瑜第一时间买了一本讲述“锈带”(铁锈地带,也被称为制造带)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书。读着读着,她感觉书里的人“跟国内东北老工业区的人特别像”:曾经是骄傲的中产阶级,生活富足,但在全球化大潮中,随着企业外迁、整个工业带的衰败而越发困顿。
“当他们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的时候,民主党却在很激烈地讨论应不应该让变性人改上厕所,要不要把‘父母亲’改成‘家长一’‘家长二’,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利益遭到漠视的弱势群体。”
即便读完了这本书,她还是不能谅解夫家:他们并不是见识有限,或者生活困顿,平时也都一心向善,为什么却可以安心选择特朗普?“这是最让我难过的——他们有的选,然而他们选择了一个特朗普这样的人。”
亨利也收到过母亲转发的假新闻邮件,主要内容是奥巴马可能是穆斯林,以及他并不在美国出生,等等。亨利气得回邮件问对方:这些消息有说出任何可信的出处吗?你怎么会相信这个?
特朗普当选总统那几天,陈艾瑜的Facebook时间线被纽约朋友对新总统的抗议声占满了,她甚至觉得“自己不发声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很习惯失败了就转移方向,哪个投对了哪个就是好汉。美国人的精神在于他们的理想不会因为现实的羁绊而改变,反而会在逆境中更加坚定地团结起来。”
她为纽约人感到骄傲。“美国的声音就是这些个体的声音的总和,不会被一个人给压制。”
说完又补充道,“当然,我的Facebook上也全都是知识分子,我听不到另外一种声音。”
亨利的母亲,克里夫太太,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干活。大多数时候,她在厨房里:要把11个苹果削成细小的薄片,做孩子点名要求想在圣诞节吃的苹果馅饼;要把6条香蕉、5个芒果和一堆草莓切成小颗粒,做一份够15人吃的水果沙拉;拿出家里珍藏的风干鹿肉,和香肠、蘑菇、奶酪拌到一块儿,塞进烤炉,做成圣诞大餐最重要的主菜。有那么十厘米见方的一格是不加奶酪的,那是给吃不惯奶酪的陈艾瑜留的。
当食材的准备告一段落,她把削下来的果皮和残渣拿去喂后院里养的兔子。院子里还养着鸡鸭,2016年12月24日这天,一只鸡下了双黄蛋,个头大得惊人,她把鸡蛋拿给儿媳妇看,笑盈盈地拿笔在蛋壳上写下了“12·24 艾瑜”,让她第二天当早餐。
她对陈艾瑜带回家的中国朋友问了很多问题:中国人都不吃奶酪吗?中国人爱吃虾吗?你们都吃不惯美国菜吗?都喜欢在菜里放辣吗?
最后得出结论:艾瑜是个纽约范儿的中国姑娘。
对亨利·克里夫的父母而言,如下几点信念是坚定不移的:政府应当减税,不干涉民众的生活,尊重他们的信仰,保护生命、反对堕胎。
他们未必在生活中见过穆斯林,也不知道中国究竟有没有立交桥,但对于自己拥有多少权利,却清楚得很。
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保守中产阶级家庭。克里夫一家居住在远离都市的白人社区,家里简朴至极,除了圣母像,没有其他软装。“孩子的笑声胜过任何装饰”是夫妇二人共同的信念,他们生育了7个孩子,还从南美洲领养了一儿一女,儿女们从幼儿园到初中的课程都由克里夫太太亲自教授。他们的私家车上贴着贴纸: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底特律街头的废弃汽车。美国一些老工业城市的衰落让工人阶级和许多曾经的中产倒向特朗普一边
每一年,克里夫先生都会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去海地为当地人义诊。
克里夫家屋后是大片的林子与一条小溪,有时候人们会在那里猎鹿。亨利在林子里为他的妹妹建了一座树屋。
这种生活方式足以让他们向共和党投出坚定的一票。
特朗普和陈艾瑜至少有一个地方相似:他们都是《纽约时报》的忠实读者。《纽约时报》也试图去了解特朗普支持者的想法。“这个出乎意料的(大选)结果让我们看见美国各地白人工人阶级的浪潮”,他们在视频新闻中描述道。一个头戴印着“让美国伟大复兴”口号鸭舌帽的白人大学生对该报说:“我挺开心能看到这个(大选)结果。我没想到他能表现得这么好。在先前的民调中,希拉里·克林顿在大部分州会胜出。不过能看到这群与我价值近似的人对大选结果有所影响,实在是很有意思。”
“特朗普是有些言辞不大优雅。关键并不是他有多好,而是人们已经厌倦了被欺骗的感觉。希拉里身上就带有这种老派政客的风格:掩盖事实,欺骗民众。”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白人中年男子说。
如果新闻报道还能保持持平与客观的话,大多数时候,知识分子在专栏中对候任总统的吐槽毫不留情。
“特朗普正在组建一个由亿万富翁和偏执者组成的团队。我们需要用坚定的反抗来让他认清,”该报的另一位专栏作家写道,“他是被选举出来担任总统,而不是被加冕为皇帝。”
《华盛顿邮报》有专栏直接分析“怎样才能把特朗普从他的位置上挪出去”。
另一方面,反对这种意见的声音也同样尖锐。同样是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有人写道:“民主党精英现在就好比在开一个大型的顾影自怜的派对,除开有那么点可悲之外,这一幕简直称得上滑稽。”
《时代》周刊将特朗普评选为2016年年度人物,并称他是美利坚“分”众国总统。
这种分裂至今没有弥合。1月10日,奥巴马回到故乡芝加哥发表离职演说,没讲几句,台下的支持者们就开始吼:“再干4年!再干4年!”
奥巴马停顿了一下,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
在1月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梅丽尔·斯特里普炮轰特朗普:“这种羞辱弱小的本能,被一个掌握权力的人在公众场合下随意实践,它的破坏力正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去……当手握强权的人利用他们的地位随意欺辱个别人时,他就是在欺辱我们所有人。”
在YouTube网站的这段视频下面,网友吵成一团。自称是“工人阶级”的网友留言:“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心态,我决定投票给特朗普,在两个坏人当中,他坏得还更轻微点。而这个女人就是那种自由主义精英,还以为每个人都应该关心她想的那些事情,就好像她有多超凡脱俗似的。”
另一个头像为女性的网友则写道:“梅丽尔你闭嘴,你就是一坨垃圾,你知道每天不停地付支票、付支票那种过日子的感受吗?你们不过是一群被宠坏了的大嘴巴。我们这些人已经说出了我们的选择,你要是不喜欢,走开呀。”
吵嚷间,似乎很少有人记得特朗普在胜选时候说过的话了:“现在是美国弭平分歧伤口、团结一致的时候。”
对亨利与陈艾瑜来说,这样的局面委实令人沮丧。就在半年前,他们还对家庭、国家充满希望。当他们筹备婚礼时,当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是首位非洲裔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时,他们说服了父母,没去天主教堂行礼。最终在当地大学教堂举办的婚礼,完全体现出新婚夫妇多元化的理念:亨利请来非洲的朋友在婚礼上发言,请他出柜的同性恋表哥当伴郎,请残疾的大舅舅递上婚戒,陈艾瑜则让伴娘和花童穿上中国传统的旗袍。
主持婚礼的、为各种信仰人群服务的牧师听说他们的故事后,特意在婚礼上说了一段话:“出生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下的两个年轻人,能够相知相惜,走到一起,相比那么多比邻而居却从不知彼此所思所感的人,这一段姻缘,是多么奇妙呢。”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理想,大家都放下芥蒂,彼此言欢,”亨利说,“然后,‘嘭’的一下,大选了,他们都投了特朗普。”
关于保守家庭的圣诞节,有一点是陈艾瑜没想到的:候任总统特朗普并不是克里夫家庭的话题。
回到亨利家之后,除了兄弟们卧室门上的海报和很爱侃大山的外公,她没有接触到任何与特朗普有关的事物。全家人都默契地闭口不谈政治,电视机再也没调到新闻频道,整个圣诞期间都在播放体育比赛。
圣诞节一大早,克里夫一家聚在圣诞树下。亨利的父亲把几十份圣诞礼物一一分给在场的孩子。加上陈艾瑜,现在他们有10个孩子了。惊喜、赞叹与欢笑在克里夫家的客厅里此起彼伏,陈艾瑜收到的礼物包括一串圣诞主题的风铃、圣诞风格的厨房用品、一整套彩色的饭盒、一套小游戏,等等。
婆婆忙着上来跟她解释:“这串风铃不一定是配合‘耶诞’,而是整个冬天都可以挂在门上的……”
这个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送给媳妇的礼物,没有任何宗教色彩,风铃是雪花的图样,厨房用品的图案是红红绿绿的槲寄生,彩色的饭盒是“先锋女性”牌的,每个饭盒上都印着自信昂扬的女性形象。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6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一群包括多名华裔在内的特朗普支持者正在集会
这可能是他们印象中第一次面对一个分歧如此巨大的候任总统,但如何面对“意见不同”,他们并不生疏。在另外的情境下,这个传统的家庭,也会面临各种不理解与不认同。“以前我遇到过一个女客户,一听说我生了7个孩子,就对我说‘你真恶心’。我回答她说,等你看到账单的时候,就知道‘恶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圣诞派对上,外公得意地对陈艾瑜说,“拜托,这儿可是美国,随你怎么看不惯我,可别想逼我去干你乐意做的事儿。”
外公年轻时候参过军,一度在英国服役,那时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铁幕下的苏联。他大约也想不到,有天自己的外孙会成长为社会主义者。
特朗普并不是他们生活中唯一要面对的分歧。
当全家人跪着祈祷时,亨利双手抱在胸前,面色平静地看着他们。
陈艾瑜会对婆婆聊到她关注的女权话题:一部纪录片,入围了奥斯卡奖,“那部片子特别有意思,说的是一个留学生,她想关注家乡的女性议题,于是回到老家,跟拍一群上街抗议社会黑暗的女权分子……咦?妈妈,妈妈您听到我在跟您说话吗?”
克里夫太太没有回头,也没有回应。亨利转过头来,对着妻子眨眨眼,说:“艾瑜,我听着呢。”
刚结婚时,陈艾瑜告诉克里夫夫妇,按照中国的习惯,她婚后不冠夫姓,还叫陈艾瑜。
克里夫太太不是很理解这些在纽约泡过几年的小年轻在搞什么,也不是很懂“不冠夫姓”是怎样一种状态。圣诞前,陈艾瑜收到了婆婆的信,收信人写着“艾瑜·陈·克里夫”。
老右派外公总催亨利去他家“收破烂儿”,他有两盏灯罩碎了的蒂凡尼灯具。为了哄老人家开心,圣诞第二天,亨利出现在了外公家。看着一盏据说是某个先祖买的灯,他问外公:咱们家有家谱吗?
答案并不意外。这个最传统的美国保守家庭,也是来美不过百年的移民。
若从外婆那一系来看,亨利·克里夫是这个家族在美国的第四代。1892年,他的高外祖父带着年幼的子女从德国来到美国。
“上世纪80年代,你亨利舅舅上大学的时候,还回过德国,据说老家那儿的教堂里,有一整面墙,都刻着名字叫‘亨利’的家庭成员。”外公告诉亨利。
德国的亲戚也曾到美国来拜访过。
就在亨利翻着家谱的那间屋子里,这些人得知了柏林墙倒塌的消息。“他们坐在沙发上,彼此都说不出话来。只是抽泣,握手,”外公说,“那情形,叫看过的人一辈子难忘”。
“这是我的曾外祖父,亨利·J·韦斯特爵士。4岁时,他跟随家人从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来到美国,从埃利斯岛登陆。为了给家里的农场帮工,他在三年级时就辍学,但良好的智慧与常识使他随后入读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1961年,他被选为密苏里最高法院院长。当他退休之后,另一位律师曾形容他‘一丝不苟、在经济上和数字上都极其精确地引证先例,以逻辑与公正去判决案件……哪怕所有的法律书籍都被付之一炬,亨利·韦斯特恐怕也能作出正确的宣判’。能与这样令人敬佩的人分享同一个名字和同一份血脉,是一种荣耀。”
圣诞过后,亨利·克里夫在Facebook上更新了这样一条状态。
他的家族从踏上美国的第一代起,就是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他们守护传统价值观的出发点,同样是“民主”与“自由”。翻找了资料后,亨利告诉陈艾瑜,当时,亨利·韦斯特法官出身低微,兄弟姐妹都是做小生意的,因为这个缘故,他体恤底层平民的辛苦,抗议征税,抗拒政府对普通人生活的干预。
他耿直,虔诚,有原则。这些为人处世的风格,也随着他的女儿、外孙女,一路影响到亨利的生活。
他们的世界观已经过时了,亨利觉得。这个时代,人类不能只扫自家门前雪,世界各地的人应当团结起来,了解彼此,共同想法子应对全球变暖。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曾外祖父的尊重。
陈艾瑜一度注销了Facebook账户。看她总在忧愁特朗普上台,亨利给出的建议与心理医生在媒体上给大众的建议是一样的:不要再时刻关注新闻报道了。他建议妻子阅读一些欧洲的历史与文学著作,体会一下启蒙运动的思想内核。哪怕特朗普当选了,但西方世界从启蒙运动以来对民主、理性的信念并未被撼动。
她依然会惆怅“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也意识到,民主党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他们一直在说要尊重多元化,尊重弱者,但是却形成了嘲笑保守派的风气。如果你要伸张言论自由,是不是也得尊重与你观点相左的人的言论呢?可民主党一直以来都在喊口号,支持种族、肤色、文化、性取向的多元化,唯独没有包容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把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边缘化了,自己还没发觉。”
某些时候,她会想起亨利外公的话:“拜托,这儿可是美国!”
每个人都可以很不同,而他们的“不同”会受到保护与尊重。你可以发声,也可以用选票去改变,哪怕在特朗普当选的那一天,那长长的选票上其他选项,还同样是自己改善社会的机会:譬如亨利,在大选投票日当天,除勾选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他还面临着对另外十余个与佐治亚州市民利益有关的法案的选择。
他给拨款扩建亚特兰大城市铁路系统的法案投了赞成票。
“我需要有一个扎实的根基,才能根据新闻提供的事实做出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而不是完全跟着他们的意见走。”新年伊始,在亚特兰大城区欧洲风格的小公寓里,陈艾瑜重新拿起了写诗的笔,“我的声音和观点,虽然微弱,但在这个国家里会受到保护,是有人听、也大有人可以讨论的。”
久违的雪天又降临到了这座城市。有关部门早早发布警告,大小学校都在大雪降落前提早下课,以求最大限度避开交通不便。合上报纸,生活里的一切依旧井然有序。
邮箱里躺着克里夫太太寄来的感谢卡,这一次,收信人改成了“致亨利·克里夫先生与艾瑜·陈太太”。
距离特朗普入主白宫还差10天的时候,芝加哥在一片寒风中迎来了奥巴马总统的告别演讲。“……因此我希望你们相信,不仅仅相信我的能力足以带来改变,同样相信你们可以改变国家。我希望你们去相信,相信先贤在建国宪章中写下的信念,相信那些被奴隶和废奴主义者轻声传递的观念,相信移民、家庭主妇和为正义上街游行的人们高声传颂的精神,相信那些将旗帜插上海外战场与月球表面的人所重申的信条——那是每一个还未曾写完人生故事的美国人所共有的信念:是的,我们可以改变。”
对陈艾瑜来说,在总统选举前后,“美国”的含义多少有了些不同。
可以肯定的是,她并非一无所得。在面对特朗普的“迷茫”中,这个90后华裔女性也经历了“成长”:“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学习,并且打开了一个耳朵去听和我们不一样的声音。虽然,无比困难。”
(应受访者要求,陈艾瑜为化名)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新媒体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