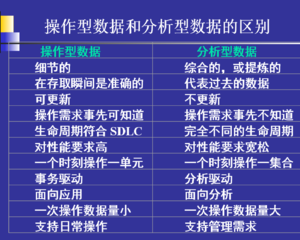民国历史学者周荫棠先生谈辛亥革命,归结为“士变而非民变”。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以民变为主流,辛亥革命则不然:“清朝的灭亡,不是由于铤而走险的民变,乃是由于激于大义、处心积虑、具有计划的士变。”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如果说这个观点,令今人别开生面,则得归功于他所使用的两个久违的概念:民变与士变。
民变是一个老词,今天虽有人在用,却也寥寥。前年在书店邂逅李文治《晚明民变》,翻开一看,其初版犹在1949年前。那么今人惯用什么说法呢,正统一点,叫“农民起义”,时髦一点,叫“社会抗争”“群体性抗争”。说到农民起义,不妨啰嗦两句。这是一个含混以至断裂的概念。据杨津涛《不存在什么“农民起义”》,中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几乎都不是农民,而是官吏、商人、军人等
(唐元鹏《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以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十二次农民起义为标本,发现三十五位主要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杨幺、杨秀清和萧朝贵——勉强属于农民,而且这三人的地位都不是老大)
;农民虽然构成了起义的主体,其参与未必出于自愿;从结果来看,起义并未造福于农民……相比名不副实的“农民起义”,他更愿意使用“民变”之说。
相比渊源有自的民变,士变应出自周荫棠的发明。它的立意,正针对民变而言。二者之别,不在领袖——民变同样可能由士
(知识人)
所领导,如洪秀全——而在参与的主体,顾名思义,民变的主体是民,士变的主体则是士。
谈及辛亥革命与士变的关系,我们的眼光不妨追溯至革命前六年。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这在当时,可谓划时代的大事,科举制已经推行了千余年,关乎一个阶层的利益和荣辱,甚至关乎一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秩序。然而,它所激起的舆论效应,却不像今人想象的那么激烈。1906年2月12日,莫理循在《泰晤士报》撰文道:“……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中国人的中国》)
其实,无论朝野,多少还是有点骚动,或者说异议之声,只不过,主流的声音,纵使不是赞美,那也如严复这般,一面感慨废科举的冲击力:“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占者之废封建、开阡陌”,一面对其损益、利弊不置一词:“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
这不是谨慎,而是困惑,严复身在局中,眼前迷雾重重,根本无法预见未来的方向。
废科举的杀伤力,要等到辛亥革命,才见爆发。科举制的消逝,彻底改写了士的政治生态,“学而优则仕”沦为明日黄花,倘若不愿沉浸于哀伤的旧梦,他们必须另辟出路,大体而言,一是留学,二是投军,三是从商,前二者的比重远过于第三者。数年以后,正是留学生和新军,联袂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后世有一种说法叫“清亡于废科举”,清朝之亡,自然不止废科举这一个原因,辛亥革命的发生,亦非以废科举为导火索
(若是如此,历史反射弧未免太长了)
,不过,它们的关系依旧亲密:废科举之变,才是真正的士变,其结果,一是为革命输血,二是为清朝掘墓。
说罢废科举,再来看辛亥革命,何以是一场士变,一目了然。以武昌首义为例。组织者包括三大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加上此前的日知会。这三者的领导人,几乎都是士或知识人:最著名的“三武”,孙武、张振武系日本留学生,蒋翊武欲留学而不得,在上海进入中国公学,那是革命党的摇篮之一;此外,曾担任共进会会长的刘公也是留学生,相形之下,日知会的领袖刘静庵更接近传统的读书人,博览经史,哪怕困于囹圄,依然手不释卷;就连武昌起义前夕牺牲的“三烈士”,刘复基是留学生,彭楚藩因科举制废除而参加新军,大概只有一个杨洪胜,与士无关。

革命的组织者是士,参与者呢,湖北新军与士能有什么关系?这得从其创始人张之洞说起。张之洞练兵,与袁世凯不同。拿招兵来说。袁世凯招兵,除了身体素质,格外讲究士兵的德行,故而有“会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等标准,张之洞看重的则是文化素养:1898年,他把工程队扩充为工程营,规定“专选二十岁以下兼能识字者方准收入”;1902年,他制定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即“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此后募兵,明确要求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譬如1905年湖北新军在黄陂招兵,入伍的96人中,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当然这与废科举有关。
招兵如此,练兵亦然。张之洞主张“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故此,他先后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将弁学堂、武高等学堂、武普通中学、陆军第三中学、陆军小学堂等,并规定“非学堂出身者不得充统领营哨各官”,这么一来,士兵必然踊跃从学,据说有一年湖北武备学堂招生120人,报名者超过四千。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的校门之上,曾高悬张之洞亲书的对联:“执干戈以卫社稷,说礼乐而敦诗书。”这正呈现了湖北新军文武双全的特色。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主力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与张之洞的湖北新军,军演之后,时人评价,前者“以勇气胜”,后者“以学问胜”。
那么,湖北新军的人员构成,士到底占据了多大比例呢?这实在难以考证,只能推测,我觉得不会低于三成,这里面,大多系读书人投笔从戎,还有一些,属于从军之后,到学堂深造,渐渐转型为知识人。此外还得注意,湖北新军,由陆军第八镇与独立第二十一混成协组成,相当于一个师加一个旅,共计16104人
(1907年数据)
,其中共进会和文学社成员超过两千人,同情革命的超过四千人,这些革命者的头脑与眼界,相较同侪,往往先进一步,所以在他们当中,士的比例还要大一点,也许可达到五成。基于此,称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源头,或者说狭义的辛亥革命——为士变,正可成立。
写到这里,大抵可以证成周荫棠的观点。不过我的目的,不止论证,更在借其论断,辨析辛亥革命的性质与逻辑。必须承认,士变是一个十分精妙的说法,由此名目,可知这场革命,局限于士及其相关的阶层,与民众几乎无关。试举两例。如曹聚仁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所述:“其后两年,辛亥革命到来了。我们乡僻地带(浙江兰溪),交通阻梗,不知秦汉,遑论魏晋,如‘革命’这样的名词,从来没听到过;乡间所说的,还是‘造反’,说是有人卖‘九龙票’。‘九龙票’,我也一直没见过,后来才知道这是光复会徐锡麟、秋瑾那一派所干的……”据陈渠珍《艽野尘梦》,武昌首义爆发之时,他正驻军西藏,听到革命的消息,遂策动部下湘黔籍官兵115名出逃,1912年6月前后,奔至青海,遇到一位随左宗棠出关而定居于此的七旬老人:“余询以内地革命事,但知:‘袁世凯为大元帅,孙文为先锋,国号归命元年。’亦道听途说,且误‘民国’为‘归命’也。”可见辛亥革命的话语传播,半年不达民众。
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第三节中写道:“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伟大领袖之言,似可一锤定音。作为士变,无关民众,构成了辛亥革命的一大特色——我曾总结辛亥革命的特征:“这是一场低烈度革命,而非高烈度革命;这是一场城市革命,而非农村革命;这是一场精英革命,而非大众革命。”——同时造就了其限度:肤浅、妥协、不彻底。以此为鉴,后来者学会了以士变引导民变,作为革命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