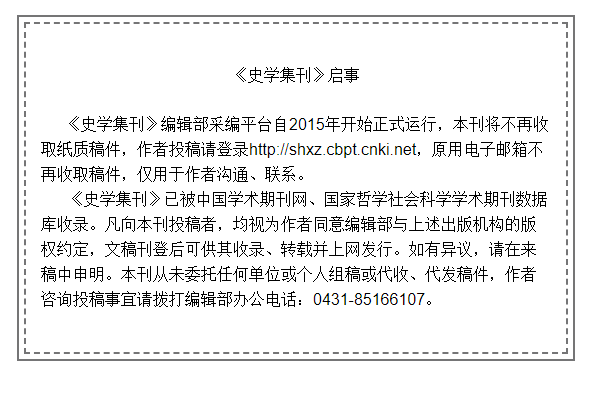原载《史学集刊》2018年第5期。
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的悖谬
赵德宇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天津300071)
摘 要: 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全盘继承了德川幕府的禁教“祖法”,后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取消禁教政策,日本基督教会迎来短暂的“小阳春”。然而,随着“文明开化”的退潮和《教育敕语》的公布,日本基督教再度遭受媒体和政府的打压,虽几经抗争,但最终转向全力支持政府对外侵略战争的“护国宗教”,由主张泛爱的上帝子民沦落为专制天皇制国家的仆人。观照明治时代的政治文化生态变化曲线,可以发现明治日本基督教经历的跌宕起伏是由专制天皇制的国家需求决定的。此外,基督教人士先天信仰不足也是日本基督教会走向异化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教育敕语》;“护国宗教”
明治时期的日本基督教会历经坎坷,最终成为天皇制国家的“护国宗教”。这一过程纷繁复杂,是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上颇引人瞩目的时代,在世界宗教传播史上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特殊标本。然而,在日本学界,有关明治时期日本基督教的研究虽然早在1956年就由创文社出版了《近代日本与基督教——明治篇》(这是十位日本学者围绕“明治维新与基督教”、“自由民权时代与基督教”等若干专题进行讨论的对谈录),但是迄今为止仍属于偏冷的研究领域,成果也多是对日本基督教人物所做的细密的个案研究。正如有日本研究者指出的:“在日本的基督教史研究中,是从接纳近代思想历程的角度,验证信仰意义的”,因而“基督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成为孤立的研究对象” 。[1]国内学界有关明治基督教的研究,亦属尚未真正开发的领域,笔者所见较集中的研究有张永广的专题系列论文。[2]该系列论文以诸多英文资料为主,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近代日本基督教教育,以及这种教育与明治专制天皇制国家教化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扼要追溯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史演化路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日本基督教会与明治政府之间从“自然冲突”到“被动妥协”,再到“主动配合”的宿命结局,追寻基督教信仰与日本政治文化生态发生冲突和被迫“转向”的不可逆的社会机理,从而对明治时代的日本基督教会做出历史定位。
一、从严禁到开禁
在进入本文论题之前,有必要扼要回顾一下近代以前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史。[3]天主教是在1549年由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弗兰西斯科·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传入日本的,在其后约90年间,其命运波澜起伏,既有光荣与梦想,也有惨烈与幻灭。一般估算信徒最多时达到75万人,[4]而集体屠杀教徒和殉教事件仅1612-1624年就高达149起,[5]死难教徒在2000-5000人之间,其中欧洲传教士约70人。[6]天主教最终在1639年被彻底驱逐出日本,“洋教”传日第一波结束。[7]时隔约220年后的19世纪中叶,在日本被迫开国的形势下,基督教又尾随列强来日本开始了第二波传教历程。
早在1855年曾担任佩里舰队首席翻译官,并见证了美日交涉全过程的美国传教士“汉学之父”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就对本国教会踌躇满志地表达了向日本传教的意愿:“日本要学习传播爱的宗教,日本人民和官吏必须要自我醒悟两个世纪前迫害天主教的错误,从而获得基督教传播的和平、清纯、温和的信仰,而且要摒弃对基督教曾经抱有的疑惑和恐惧心理。”[8] 1858年签订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中,写入了旅日美国人可在居留地设置礼拜堂的条款,翌年即有詹姆斯·赫本(James Hepburn,1815-1911)、约翰·里金斯(JohnLiggins 1829-1912)、詹宁·威廉姆斯(Channing Williams,1829-1910)、杜安·西蒙斯(Duane Simmons,1834-1889)等一批传教士来到日本。幕末来日的传教士都具有良好的教养并兼具一技之长,如其中的赫本边传教边行医,还编纂了日本第一部日英词典《和英语林集成》,[9]并致力于女子教育活动等等。虽然此时幕府并没有解除对基督教的禁令,但在幕末政治动荡期,传教士们已经于1862年和1864年分别在横滨和长崎建立教堂,并开始传教。1865年作为传教士日语教师的矢野元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新教教徒,这让赫本十分激动:“在这严禁基督教之地,迎来了最初的受洗者。”[10]可见,基督教初传日本之艰难。
1865年天主教传教士在长崎新建的大浦天主教堂献堂式上,发现了浦上村的众多信徒竟然是德川幕府初期天主教教徒们代代相传的后裔,他们作为 “隐切支丹”[11]始终坚持天主教信仰。这对传教士们而言宛如天降“福音”,然而,按照幕府的禁教“祖法”,这些“隐切支丹”是罪犯。加之,信徒们公然拒绝佛教僧侣参加他们的安葬仪式,并拒绝向寺院捐助,而在当时的檀家制度[12]中这些都是佛教寺院理应得到的最基本的权利。幕府终于“忍无可忍”,开始逮捕并迫害基督徒。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虽然标榜“诸事一新”,但在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上却墨守旧制,全面继承了德川幕府严厉禁教的“祖法”。新政府在明治元年3月14日公布了以除旧布新为主旨的“五条誓文”,然而,就在第二天公布的“五榜示文”之第三札规定:“严禁切支丹邪宗门,如若有可疑者,要报告所在官署,并予以奖赏。”[13] “切支丹邪宗门”之说立刻引发了西洋各国使节的抗议,认为把基督教称为邪教是对信奉基督教各国的侮辱。对此,新政府方面辩解说,“切支丹”与“邪宗门”是应该分开的两个概念,只是行文疏忽才被误解为切支丹就是邪宗门,但仍然拒绝解禁基督教。不仅如此,明治政府“更遣木户准一郎(木户孝允)将教囚士民三千七百余人迁移到其他诸藩,加以告诫,令改其信仰。教徒皆不畏刑,无一人服从告诫者”。[14]被指定接收这些村民的21个藩为取悦新政府也使尽招数迫使这些信徒弃教,甚至使用了五花八门的酷刑。[15]浦上村教众再次受难。
新政府迫害教徒的行为,再次引发了欧美舆论的强烈抗议。对此,明治政府在《日本政府关于弹压基督教致各国代表的声明》(明治2年12月18日)中称:“我们不排斥基督教本身,但是我们也不能允许基督教导入日本,如果认可信奉基督教,将招来深刻的国内龟裂,致使我国分裂。不过,即使如此(禁教)还是缓和的,希望认可,因为历来对天主教徒的处罚是磔刑。绝对不许可一般国民信奉基督教。”[16]之后,岩仓使节团游访欧美,沿途各国纷纷抗议明治政府无视人权的行为,并拒绝与岩仓使团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在列强的强硬外交压力下,几经反复,明治政府才被迫于1873年撤销了禁教布告,浦上村教民也被允许返乡。至此,日本政府放弃了自丰臣秀吉开始的近三百年的禁教政策。不过,“政府并非由此完全解除了对基督教的禁制,可以认为只不过是一种默许”,[17]直到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才真正承认了基督教在日本的合法地位。
在基督教解禁之前的1872年,约翰·巴拉(John Ballagh,1842-1920)就已经在横滨租界地创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新教教会——横滨公会,[18]第一代日本基督教的领袖人物植村正久、本多庸一、奥野昌纲、押川方义等人受洗。1873年东京基督公会、日本长老会成立,到1881年教会的势力已经渗透到日本各主要城市。为加速展开传教事业,开始出现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合并,比如1877年10月,横滨的基督公会与横滨、东京的长老派教会合并,组成 “日本一致教会”。[19]
传教士与早期日本教徒们为传教做了诸多基础准备工作。诸如:1868年由赫本等传教士翻译的《新约圣经》出版,传教士们还开展了医疗活动、救助孤儿和贫困者等弱势社会群体的慈善事业。这些活动宣扬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使日本人开始逐渐理解基督教。尤其是传教士们还亲身从事教授西方语言的工作,对此,正在仿效西洋的明治政府也是欢迎的。这些传教士在教学过程中显示出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众多学生,初期受洗的日本教徒多出自传教士们兴办的“英语塾”。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士们的上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对基督教的传统偏见,再加上欧化流行的大环境,信徒人数在稳步上升,1882年有4000人、1885年逾万人、1890年达34 000人。[20]
传教事业似乎度过了危险期而初见曙光。然而,日本基督教会可谓生不逢时,因为明治政府正在向日本臣民全力灌输作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忠君爱国思想,这就预示了双方冲突势所难免。
二、抗争与屈从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不违背臣民义务情况下,有信教之自由”,总算间接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但从对“信教自由”所设限制条件看,基督教信仰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更不能奢望得到政治上的安全保障,基督教可以随时被指责为“妨碍安宁秩序”和“违背臣民义务”。1889第一次大选中有9名基督徒当选为帝国议会的议员,这个结果招来了国家主义者和佛教界的攻击。攻击者提出:“日本皇室及国家与基督教势不两立、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对日本来说是祸害……基督教的社会伦理与日本不合等等。”[21]这些激烈的言论明确反映了排斥基督教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有源自佛教与基督教竞争的冲突。对此,基督教一方的内村鉴三、植村正久、小崎弘道等纷纷进行反击。然而, 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以忠君爱国为主旨的《教育敕语》成为对基督教致命的一击,“排耶”阵营开始利用《教育敕语》和忠君爱国思想对基督教人士展开了新一轮的人身攻击,“内村鉴三不敬事件”首当其冲。
1891年在第一高等学校任教的内村鉴三因基督教信仰,拒绝向天皇的“尊影”(照片)以及《教育敕语》礼拜,“第一高等中学嘱托教师内村鉴三出席该校敕语拜读式,对陛下之敕语和尊影不行礼,其不逊不敬乃最可憎之行为”。[22]其实,内村鉴三当时就表明自己对天皇的敬意绝不劣于他人。尽管如此,被忠君爱国思想洗脑的学生们仍然“义愤填膺”,并将此事传扬到社会。内村鉴三在与井上哲次郎的公开辩论中反驳说:“足下要证明基督徒对我国不忠、对教育敕语不敬,认为教徒没有遵从足下期望的仪礼。然,在此尚有胜过仪式的存在,即对敕语的身体力行。面对敕语不低头与不实行敕语,孰为大不敬?我圣明天皇陛下,会嘉奖胜过仪式上敬拜的实行上的敬拜,我对此坚信不疑。”[23]然而,国家主义者们并没有停止对基督教的舆论围剿,甚至辱骂内村鉴三为国贼,致使内村身心憔悴并被免职,陷于生活困顿。此即“内村鉴三不敬事件”。事件发生后,植村正久针对国家主义者的舆论围剿,撰文指出:“作为皇上的忠良日本臣民、赞成文明教育的一员、欲维护人类尊贵之一丈夫,必须反击这种弊害。”[24]但政府命令禁止发行刊载此文的《福音新报》,明显偏袒攻击内村鉴三的一方,从而纵容了仇教势力肆无忌惮地攻击基督教。此后又频繁发生了熊本英学校事件、山鹿高等小学事件、八代高等小学事件等无聊甚而编造的所谓“不敬事件”。甚至基督教会还因拒绝资助神社的祭祀费用而遭受攻击。
如果说在“内村鉴三不敬事件”时还有基督教人士出面为内村辩护的话,那么在仅过两年后发生的“《日本新娘》事件”中,基督教阵营则倒向国家主义者。1893年资深基督徒田村直臣在美国发表英文小说《日本新娘》(JapaneseBride),因主张男女平等触及日本家族制度的弊端而被认为是“暴露国耻”“讥讽同胞”。尤其是书中“我们日本人不懂爱情和情欲之间的区别”[25]一句,成为日本传媒和基督教界人士指责田村污蔑本国同胞的重要证据,并引起了“舆论的激昂”。日本各大报纸争相批判该书及其作者,又有内务省颁布命令禁止该书在日本出版日文版。而更令田村直臣难以忍受的是来自基督教阵营的落井下石。两年前还为内村鉴三辩护的植村正久指称《日本新娘》中所述“在日本,父亲是拥有无限独裁权力的君主”等内容,“绝不是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并认为:“作为一国国民,自己国家的(负面)事情,即使是真实的,也有对外保密的义务。而罗列虚构(负面)事情在外国人面前诽谤自己国家的行为,必须受到谴责和批判。”[26]不仅如此,日本基督教会还对田村直臣进行了两次宗教审判,结果“认定田村直臣氏已不能胜任其教职,现免去其职”,[27]最终取消了田村直臣的牧师资格。
上述一系列“事件”把基督教推入了“邪教”的深渊,日本基督教会上述“自残以谢天下”的策略并没能使自身顺利过关。当时日本社会甚至称基督徒为“非国民”,并借围剿基督教来推进忠君爱国的国民道德、国体论及国家主义的宣传运动。御用学者井上哲次郎乘势引爆了“教育与宗教之冲突”的论争。井上认定基督教违背《教育敕语》精神,并于1893年发表论文《教育与宗教之冲突》,宣倡排斥基督教的理论。井上认为,基督教所主张的世界主义与《教育敕语》规定的作为规范臣民的国家主义背道而驰:“一言以蔽之,敕语的要点乃国家主义。然而,耶稣教甚是缺乏国家之精神,不啻缺乏国家精神,且反对国家精神。由此,与敕语的国家主义不相容势所难免。”[28]井上还认为基督徒本身就是否认对天皇的忠诚:“保罗主义认为,之所以要服从执政者皆因其为神授……即这种服从并非是对执政者的服从,而只是服从神而已……如若耶稣教徒按照以保罗之言为最高忠诚的思维,就绝不会对我邦天皇有忠义之心。”[29]对此,基督教一方的高桥五郎在《国民之友》发表《排伪哲学论》,对井上之说进行了严厉的批驳,认为井上对基督教的攻击,实质上就是攘夷论的翻版。一时间诸多著名学者分别加入两大阵营,展开了一场大论争。反基督教一方有井上円了、村上专精、杉浦重刚等佛教界学者和国粹派人士,基督教一方则都是基督教人士,如植村正久、小崎弘道、松村介石等。
表面上看,论战双方都是学者,貌似学术论争,其实井上哲次郎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在1935年回忆说:“《教育敕语》颁布的当时,与今日大不相同,基督教徒们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30]上述论争实际上是井上哲次郎发动的一场普及忠君爱国等天皇专制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运动,目的在于清除对专制天皇制形成威胁的任何思想,而当时基督教可谓最异己的思想之一,因而遭遇舆论的政治攻击势所必然。
其实,日本基督徒们同样虔诚地表示要忠君爱国,更不反对专制天皇制。如前所述,饱受攻击的内村鉴三在“不敬事件”中就反复表达了对天皇的崇敬之心,他曾以“我爱两个J,JESUS、JAPAN”概括了其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基督教本土化理念。“耶稣加深且纯化了对日本的爱;日本使对耶稣的爱明确化并给予目标,这是当时内村内心的真实写照”。[31]再如,激烈批判井上哲次郎的高桥五郎也承认《教育敕语》是普遍性的实践道德,甚至论证《教育敕语》是日本民族的习惯伦理,而基督教信仰与日本的道德伦理绝无矛盾。基督教阵营所宣倡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基督教本土化的理念,实际上是对专制政权的一种无奈的妥协,正是这种妥协,使日本基督教无法逃脱御用宗教的宿命。
从井上哲次郎以御用学者身份出场围攻基督教开始,已经决定了日本基督教会一方的失败命运,加之媒体舆论的围攻,基督教一方早已筋疲力尽。不久,因日本政治外交形势的变化,论战偃旗息鼓。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基督教各派趁机结成同志会向政府靠拢,从事慰问伤员等支持对外战争的活动。本多庸一担任同志会本部委员长,由井深梶之助、村井知至、山路爱山、竹越与三郎等人负责为战争向教徒募集资金的活动。本多庸一甚至把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宣传为“义战”,鼓吹杀身成仁以报效皇国。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主流基督徒们认为日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1904年基督教会与神道和佛教一起参加宗教大会,论证日俄战争的正义性。日本基督教的高层人士本多庸一、井深梶之助等人,甚至出使欧美为日本政府做外交舆论工作,历陈日俄战争并非掠夺性战争。[32]本来主张泛爱的日本基督教,为获得自身的生存而丢弃了基督教的本旨,反而成为战争和杀戮的支持者。至此,被明治政府视为“体外异物”的基督教,终于自觉自愿地投奔到专制天皇制国家的麾下。
如上所述,虽然基督教尝试了多重回合的抗争,但仍然如同佛教传入时为了争得生存空间不得不以镇护国家的身份拥抱古代国家政治一样,最终也没能逃脱沦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护国宗教”的悲剧结局。
三、明治基督教“沦陷”的社会机理
在言必称西洋的明治时代,作为西洋文化根基的基督教反而举步维艰,这似乎是个难以理解的悖论。其实,如果观照明治基督教跌宕起伏的曲线就会发现,这条曲线与明治社会政治生态变化的大背景是吻合的。基督教在日本的沦陷可谓“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幕府末年基督教二度来日,可谓生不逢时。自丰臣秀吉到德川幕府残酷的禁教政策,使日本人对基督教有一种政治恐怖感,教徒就是罪犯已成为社会共识。近三百年对基督教的妖魔化宣传,也在日本民众间形成了对基督教文化的自觉抵触。加之,在檀家制度下,民众生活已经与佛教难解难分,磨灭了对其他信仰的需求。再看明治初年以天皇为轴心的日本统一国家开始起步,这与天主教初来日本时的战国纷争时代迥异。基督教传教士们面对的不是各自为政的大名,而是统一国家的明治政府,可以说基督教无隙可乘。总之,就来日时机而言,基督教的运气远不如他们三百年前的前辈,他们要面对的明治新政府急需确立天皇的权威,视基督教为“体外异物”如芒在背,这就注定了日本基督教会的坎坷命运。
明治新政府是通过1867年10月的“大政奉还”和同年12月的“王政复古”而成立的,因而虽然万事皆称“一新”,但其重中之重则是稳固“王政”。明治元年(1868)3月13日宣告重建古代天皇制的祭政一致统治体制:“此番据神武(‘记纪神话’所记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创业之基王政复古,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之制度。首要乃再兴、组建神祇官,以逐次复兴诸祭典。此旨布告五畿七道,复归往古……普天下之诸神社神主等,此后皆附属于神祇官。”[33]毋庸赘言,此布告的主旨在于复古,是在宣示“王政”要像古代日本那样掌控全国所有神社乃至民间神道信仰。同年10月,睦仁天皇参拜冰川神社,诏书曰:“崇神祇,重祭祀,乃皇国之大典,政教之基本。然自中世以降,政道渐衰,祀典不举,遂致纲纪之不振,朕深慨之。今方更始之秋……亲临视政,将先兴祀典,张纲纪,以复祭政一致之道。”[34]这道诏书乃告慰中世以来饱受压抑的历代天皇,可谓是明确复辟天皇制统治的宣言书,同时也强化了天皇对日本民众精神统治的权力。1870年3月专门设立了教部省,管辖全部神社和佛教各宗派以及民间宗教。1871年教部省制定了《三条教宪》:“应体现敬神爱国之旨;应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35]为了把皇室权威印在每一个日本人的心里,1872年把“记纪”神话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定为“纪元节”。[36]观照上述背景,明治新政府初期对宣倡上帝唯一信仰的基督教所采取的强硬政策就不难理解了。
一般认为,明治政府是在列强的压力下,对基督徒的迫害有所收敛,并默许了基督教在日本的存在,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天皇权威得到基本确认之后,新政府主持加速了全方位学习西方的步伐。作为标志性事件,明治政府于明治五年(1872)放弃了沿用千余年的阴历,改用西历,颇有学西洋“奉正朔”的意味。在此前后,开始了史称“文明开化”的西化运动,基督教顺势迎来了发展的“小阳春”。
然而,“小阳春”景致虽好,终是时光短暂。日本基督教的命运是由专制天皇制的国家需求决定的。明治政府要确立天皇对日本臣民的绝对精神统治,基督教始终是一个棘手的存在。明治政府不会忘记西教曾经使丰臣秀吉和德川幕府伤透了脑筋,作为绝对王权被神话的明治天皇更会因为人们信奉基督而感到酸楚。然而,西方列强又非常看重信教自由,禁止基督教会被西洋人看作是“不文明”的行为。明治政府一方面不喜欢基督教,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西洋人对自身的评价,这种选择的两难,预示了在日基督教的尴尬境遇。
随着《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的颁布,欧化主义逐渐退潮,于是基督教的厄运再次降临。有学者认为:“明治政府颁布的《教育敕语》激起了日本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国家主义’的强势话语下,日本的基督教运动陷入困境。”[37]这个判断大体是不错的,不过《教育敕语》所产生的效应不是日本基督教会陷入困境的开始,而是对文明开化时期放任基督教政策的矫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明治以来开始在全国被制度化实施的国民教育……自上而下强制铸造对以天皇为顶点的国家形成有用的人……为造就具有适应国家目的的人,在《教育敕语》和修身教科书中设定了忠君爱国的模式。”[38]
《大日本帝国宪法》虽然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但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以神国史观和天皇崇拜为核心的国家神道的国教地位。作为配套文件的《教育敕语》强制推行忠君爱国精神,并以此规范全体日本臣民的行为。《教育敕语》云:“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斯道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39]《教育敕语》是公认的日本近代“教育宪法”,其中所称“国体之精华”就是以皇祖皇宗为肇始的神国、皇国观念,因为天皇是神的后代,所以全体臣民不但要克己尊皇,还应“义勇奉公”。[40]而前述内村鉴三居然无视《教育敕语》的神圣性质,拒绝对其礼拜,实乃“大逆不道”,因而受到社会舆论围攻甚至人身迫害也是理所当然了。
其实,明治政府早在前述《日本政府关于弹压基督教致各国代表的声明》中已经认定基督教绝不仅仅是宗教问题:“值得考虑的是,本事件(弹压浦上基督徒事件)当然不仅仅限于宗教层面,他们蔑视祖国的宗教,危害很大。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天皇之权威,是以我国宗教为基础构成的,天皇乃国民尊崇的天照大神乃至天孙之后裔。基督徒公然藐视全体国民都要考虑的神圣,他们(基督徒)拒绝去祭祀天照大神的神社参拜,此乃蔑视天皇之行为。”[41]显而易见,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为基督教定性,对以神国、皇国观念为基础的专制天皇制而言,与基督教之间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冲突,更是政治上的对立。
基督教独尊上帝与日本只尊天照大神后裔之天皇,双方都宣称自己的崇拜是唯一的信仰。而明治时期的日本怎能容得下两个“唯一”,一个日本人心中更不能有两个神。更现实的问题是,基督教还反对杀戮,甚至主张“爱仇人”,自戕生命更被看作是对上帝的亵渎,而《教育敕语》却要求日本臣民对天皇“义勇奉公”。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基督教尊重生命的主张原则,那么日本臣民皈依上帝之后,即使可以“尊皇”也不可能再为国捐躯了。内村鉴三就是现实中的例子,不能想象拒绝对天皇和《教育敕语》礼拜者,会为天皇“义勇奉公”。因而,从确保天皇政治、精神权威的角度看,基督教的上帝崇拜无异于釜底抽薪,当然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总之,近代日本基督教生来就是明治政府的“天敌”。那么,一边是专制国家权力,一边是宗教信仰,二者又不可调和,孰胜孰负,不言而喻。
看来,内村鉴三“两个J”的思想是无法实现的,日本基督教会只有两条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像德川初期的日本天主教那样为坚守信仰抗争到底而遭严厉镇压,要么在顺从并配合政府行动的前提下,保留最微弱的信仰。结果,日本基督教会选择了后者。
其实,这种选择也有日本基督徒们自身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入教之初的先天信仰不足。与其说日本基督徒们出于纯粹的信仰而皈依上帝,不如说是在文明开化社会氛围的感召下,因为憧憬西洋而拥抱上帝的,因而对基督教的教义也并非了然于心。内村鉴三就是16岁时,在学长们诱骗威逼之下于“信耶稣者之誓约”上署名的:“我是在被强制违背自己的意志情况下,向基督教迈出了第一步的。”[42]田村直臣也回忆过当初皈依上帝时的心理:“我成为基督教徒,并非因为对基督教教义本身深信不疑,而更多的则是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的。应该说,对于精神层面的基督教,我还基本理解不了。我只是觉得基督教是文明国家的宗教……如果没有基督教,就不能像欧美那样成为文明社会。我觉得当时和我一起受洗的筑地大学校的教友们,都是我这样的信徒。”[43]还有日本基督徒是因为基督教的“泛爱”理念符合儒家“仁爱”思想而皈依上帝的。曾任日本组合基督教会会长的小崎弘道就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他后来在提及自己入教动机时说:“不是弃儒信耶,而是为了实现儒家精神才接受了基督教。”[44]日本基督徒的这些特殊性,为他们在信仰领域对政府妥协埋下了伏笔,使他们在政府和社会媒体的强大压力下很难坚持基督教教义,甚而与基督教的“泛爱”背道而驰,转而支持政府发动的对外战争。
结 语
基督教重返日本半个世纪后的1909年,信徒达7.5万人,[45]对照17世纪初期,天主教传教半个世纪的成绩是信徒75万人,以至于被称为“天主教时代”。扼要解读这十倍之差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知明治日本基督教会坎坷命运的社会政治机理,还可为深刻把握明治专制天皇制政治提供一条清晰的线索,甚而可以帮助我们宏观上了解日本应对外来文化的习性。
天主教初传日本的16世纪中叶,正值群龙无首、大名混战、国家权力陷于真空状态的战国时代,这对传教士说来可谓天赐良机。其一,日本国家权力的真空状态,意味着传教士传教阻力的弱化。其二,西南地区的大名们历来注重对外贸易,而葡萄牙商人可以提供火枪和作为弹药原料的硝石,又因为葡萄牙是当时天主教传教的保教国,因而对日本采取了商教一体的策略。[46]于是,诸多大名无法抵抗贸易利益的诱惑,纷纷对传教士表现出言不由衷的好感,甚至出现“大村、有马、天草等地区全体领民入教的局面”。[47]此外,对于生活在战国混战时代的普通百姓说来,天主教宣倡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博爱精神和教会慈善事业等,无异于黑暗时代的“救世主”,因而“归其宗者如麻粟”。[48]
与天主教初传日本的社会状况相比,幕末和明治时代来日传教士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对手是仇视西教的统一政权。尤其是明治时代专制天皇制国家把对天皇的绝对崇拜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核心,并强行灌输给全体日本臣民,于是天皇与上帝一样被视为必须绝对信仰的“唯一神”。如此一来,便形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与天皇之间不可调和的对决局面。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又不能无视西方列强的屡屡施压,因为近代西洋绝难像当年葡萄牙那样被驱逐,因此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日本的存在。明治政府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决定了明治基督教不可能享受“天主教时代”那样自由传教的惬意,另一方面也不至于遭受德川幕府初期那样的残暴镇压。这种宿命引导着日本基督教会步履蹒跚,最终在背离信仰而自愿匍匐在政府体制内的条件下,才使得基督教的躯壳得以勉强保存下来,内村鉴三“我爱两个J”的信仰包容终成两律背反。明治政府通过对基督教半个世纪的“考验”,相信基督教已经变得有益无害。1911年,神道、佛教、基督教三教聚集,召开宗教会议,显示了基督教正式与政府合作,成为与神道和佛教并列的“国家翼赞宗教”。
基督教紧随西洋殖民者向全球强势扩张以来,世界各地对基督教或接受或抵制,不过,一旦融入传教地,便较少受到来自国家意志的干预。但是,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的命运却几经反转命运多舛,反而在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屡遭打压,虽保留了基督教形式上的躯壳,但却沦为点缀专制天皇制国家政治及其民间民族主义的花瓶。这种戏剧性的结局或可视为非基督教国家“接纳”基督教的“特殊标本”,或可称一种模式。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展现的是日本基督教会通过拥抱天皇绝对崇拜而抛弃了基督教上帝信仰和仁爱精神等内核,这种“存壳去核”的作业,正可谓“买椟还珠”。这即是所谓日本基督教本土化、日本化的过程。明治日本基督教引人瞩目的尴尬境遇提示人们,在探讨明治时期诸多历史文化现象时,不可忽略在皇国观念支配下的专制天皇制的存在,因为它是抵消“文明开化”时代近代精神的渊薮。
一般认为日本人具有热衷吸收外来文化的天性,然而综观明治西教史不难发现,这种所谓“天性”却是大打折扣。其实明治西教史可视为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上的典型模式,因为这段历史又一次展示了历史上外来文化日本化的过程。外来的异质文化尽可以进驻日本,但需要经过排异的调试,哪怕外来文化异化为自身的对立面,也要使之符合日本人的需求。当然,大多情况下这个调试过程反映的是国家意志,而在战前的日本,目标就是要符合专制天皇制国家的需求。
作者简介:赵德宇,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史。
[1]大濱徹也:『明治キリスト教会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79年、前言、1頁。
[2]张永广:《基督教教育与日本明治初期的武士阶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教育敕语”、国家主义与近代日本的反基督教运动》,《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同志社风波”与近代日本基督教学校的本土化》,《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2期;《近代日本基督教学校与政府关系述略》,《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0期。
[3]在当时大部分日本人看来,天主教与基督教都是西方传来的“洋教”,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4]福尾猛市郎:『日本史史料集成』、第一学習社1980年、149頁。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个数字似有夸张,但最保守估算也在30万人以上。
[5]松山崎校注:『切支丹鮮血遺書』、改造社、1926年、186-257頁。
[6] アルマンド·マルティンス·ジャネイラ(Armando Martins Janeira):『南蛮文化渡来記』、松尾多希子訳、サイマル出版会、1971年、50頁。
[7]如需稍详细了解这段传教史,可参阅赵德宇:《日本“南蛮时代”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2期。
[8]松平惟太郎:『日本聖公会百年史』、日本聖公会教務院文書局、1959年、5頁。
[9]收入日英词条20 722个、英日词条10 030个,词典中使用的罗马字拼写法(类似于汉语拼音)一直沿用至今。
[10]佐波亘編著:『植村正久と其の時代』第一巻、教文館、1937年、371頁。
[11] “切支丹”即天主教、天主教徒,为葡萄牙语的音译,因16世纪中叶天主教是经由天主教的保教国葡萄牙传入日本的。“隐切支丹”即地下教徒之意。
[12]所谓“檀家制度”,是德川幕府严禁天主教政策的一环,所有家庭必须要归属于特定的寺院而成为固定的檀家(施主),并承担维持该寺院的经济费用,而寺院则为檀家发放其不是天主教徒或已经放弃天主教信仰的证明,并主持一些礼仪活动。佛教寺院俨然成为幕府的行政管理单位。
[13]笹山晴生等編:『詳説日本史資料集』改定版、山川出版社、1994年、242頁。
[14] [日]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744页。
[15]参阅開国百年記念文化事業会:『明治文化史』6、洋洋社、1954年、272頁。
[16]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史史料』4(近代)、岩波書店、1997年、87頁。
[17]開国百年記念文化事業会:『明治文化史』1、洋洋社、1955年、187頁。
[18]田村直臣:『信仰五十年史』、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3年複製、24頁。
[19]開国百年記念文化事業会:『明治文化史』1、359-360頁。日本一致教会1890年改称日本基督教会,并在东京设立一致神学校。
[20]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編:『宗教史』、山川出版社、1985年、384頁。
[21]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编:『宗教史』、348頁。
[22]井上哲次郎:「教育と宗教の衝突」、瀬沼茂樹編:『明治文学全集·80·明治哲学思想集』、筑摩書房、1974年、125頁。
[23]内村鉴三:「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君に呈する公開状」、『内村鉴三全集』2、岩波書店、1980年、128頁。
[24]植村正久:「不敬罪とキリスト教」、『植村正久著作集』1、新教出版社、1966年、290頁。
[25]杉井六郎:「小沢三郎编日本プロテスタント史史料·六·田村直臣の“日本の花嫁事件”(一)」、『キリスト教社会問題研究』 25号、同志社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
[26]杉井六郎:「小沢三郎编日本プロテスタント史史料·六·田村直臣の“日本の花嫁事件”(一)」、『キリスト教社会問題研究』 25号。
[27]杉井六郎:「小沢三郎编日本プロテスタント史史料·八·田村直臣の“日本の花嫁事件”(三)」、『キリスト教社会問題研究』 27号、同志社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
[28]井上哲次郎:「教育と宗教の衝突」、『明治文学全集·80·明治哲学思想集』、131頁。
[29]井上哲次郎:「教育と宗教の衝突」、『明治文学全集·80·明治哲学思想集』、145頁。
[30]開国百年記念文化事業会:『明治文化史』6、第356頁。
[31][日]古屋安雄等著,陆若水等译:《日本神学史》,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19页。
[32]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編:『宗教史』、390頁。
[33]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史史料』4(近代)、81頁。
[34][日]村上重良著,聂长振译:《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9页。
[35]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日本の心と形』、東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255頁。
[36]初为1月29日,1873年改为2月11日。
[37]张永广:《“教育敕语”、国家主义与近代日本的反基督教运动》,《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
[38]久山康編:『近代日本とキリスト教ーー明治篇』、創文社、1956年、182頁。
[39]大久保利謙編:『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館、1965年、425頁。
[40]井上哲次郎明确地将“义勇奉公”解释为“为国捐躯”。
[41]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史史料』4(近代)、87頁。
[42]内村鉴三:「余はいかにしてキリスト信徒となりしか」、内田芳明編:『近代日本思想大系』6、筑摩書房、1975年、13頁。
[43]田村直臣:『信仰五十年史』、24頁。
[44]小崎弘道:『小崎全集』第3巻、小崎全集刊行会1938年、27-28頁。
[45]川崎庸之、笠原一男編:『宗教史』、388頁。
[46]详见赵德宇:《日本“南蛮时代”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2期。
[47] フロイス(佐久間正訳):「1596年耶稣会年报」、キリシタン文化研究会編:『キリシタン研究』第二十輯、吉川弘文館、1980年、267頁。
[48]雪窓宗崔:「対治邪執論」、海老沢有道ほか校注:『日本思想大系』25、岩波書店、1980年、4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