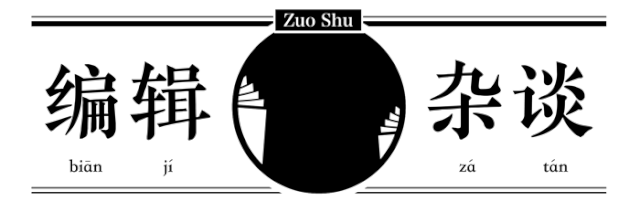 (一)
(一)
身高一米八几的北方汉子老钱儿,往那一站,气势十足。然而一张嘴却柔声慢语,气势立马锐减三十公分,一米六的我好像也可以俯视他。
他有着长年从事印制这个行业坐下的职业病——唠叨和强迫症。
每本经他手的书,印前都要和编辑确认三遍起。
一遍聊天工具,两遍电话,是标配。
“阿铁,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你这书……”
他打来电话总是这样的开场白。语速节奏每次高度相似,一度让人怀疑老钱儿是不是“进化”成了人工智能。
其实我也特别理解。
毕竟印制这活儿,环节多、又琐碎,每本书的装帧都不一样,材料和工艺也不断升级,拉页、模切、不规则内页、烫印,各种手工活儿......想要满足编辑日新月异的玩法,协调印厂、纸厂、装订厂各路人马,保证各环节顺畅高效无误,会算账、会砍价、会和稀泥、会亡羊补牢,特别考验印制的能力(神经)。
久经考验的老钱儿于是变成了今天的模样。而慢语速、唠叨,大概也是他在长期磨炼(折磨)中避免出错和缓解焦虑,以不变应万变的良方。
据我敏锐的观察,当老钱儿“人工智能”时,往往说明一切安好。而当他语气起了波澜,通常意味着有事发生。

比如那天电话里,他以两倍速惊慌地说道:“阿铁,封面出问题了!”
我一惊,手里的保温杯差点打翻,问他怎么了。
他一股脑地说:“就你那本卡书脊的书,我看装歪了,你那红色的书脊跑到封面上来了一条!我平时就跟你们编辑说,少卡书脊、少卡书脊,你看看,几千册全都装完了,哎...”
在他的唠叨中,我想起是有一本白色封面、红色书脊的书,他说的装歪了,应该封面装的时候整体往右移了。

我努力喝下一口枸杞压惊,让他拍个照片来看看。
看到他发来的照片,我那差点跳出来的小心脏,又妥妥地落了回去。
白色的封面上,露出了一条宽也就一毫米不到的红线,一般人其实不一定注意到,而且我觉得勇攀科学高峰的学子们应该不会太介意这条红色发丝,而且,也许会以为这是一种特别的设计…
我一边心里感慨这工作都把人逼成啥样了,一边安慰着受惊(大惊小怪)的老钱儿,直到他又捡回了人工智能的理智和淡定,去通知入库了。
而那一次,他突然出现在我们屋,用一种令人不安的坚若磐石、中气十足的声音说:
“阿铁,你那本书的内文印得有个小小的问题。”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怕是要杯具。
怎么了。我坚若磐石地反问。
“你那本书不是双色书里有一部分四色页吗,然后书眉那儿应该是统一的蓝色,但是双色追四色的蓝追的有点不准。”他继续坚若磐石地说,一边缓缓的从背后拿出一本印好的毛书。
这颜色追得有多不准呢?
从书上可以看出,大概也就是深蓝和草绿的区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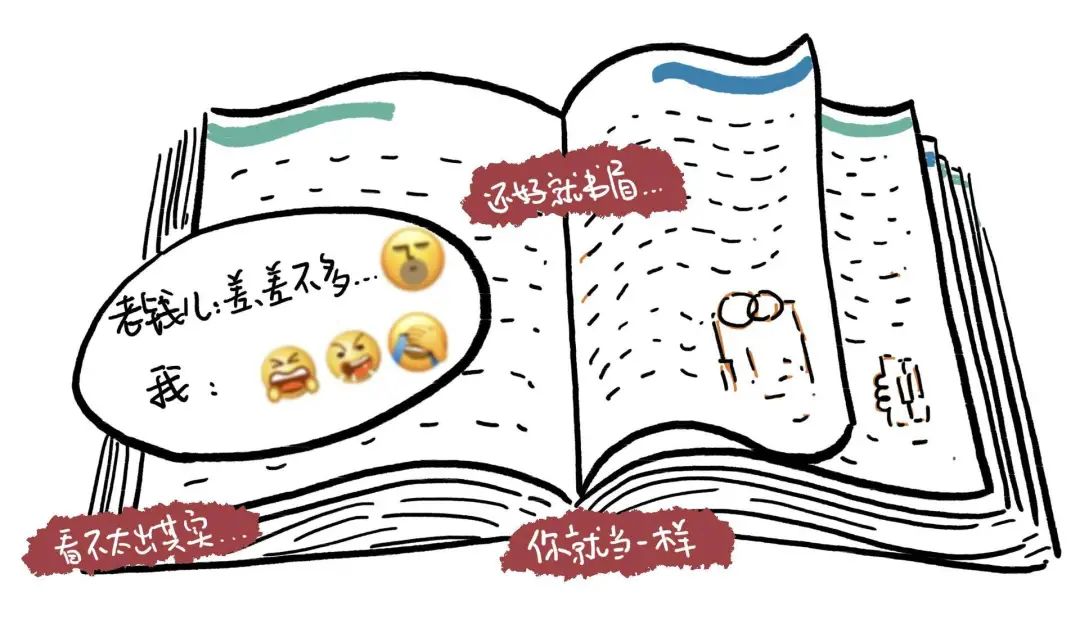
夸张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孔雀蓝与蓝的区别吧……
我的沉默和眼神化作一把利刃,刺穿了他“坚若磐石”的外壳,壳瞬间土崩瓦解碎成渣渣,他的气势缩回一米五,语速变成快进模式解释道:
“这颜色细看确实是有点差别,但也不难看不是……
这家印厂相对便宜,我不想着给你省点钱吗,这手艺,一会我得好好说说他们……
这四千册都印完了,重新印的话,这价格啊,这工期啊……”
本着女人何苦为难男人。
本着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
本着我还有一堆书在他手里。
本着上次我弄错了一本书的封面署名,他补救得还挺干净利索。
我叹了口气。
老钱儿松了口气。
我承认老钱儿最后说的“这价格啊,这工期啊”戳中了我。为了书眉,让印厂全部承担重新印的成本,也是有点不落忍。更何况,本来就是为了节约成本才用的部分双色部分四色,纸张本身都因为材质不同而有细微的色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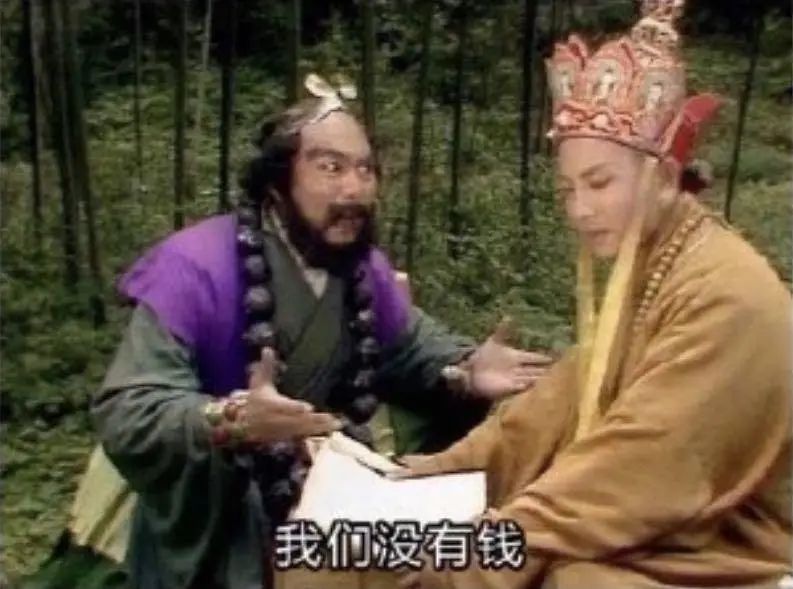
这么一想,我便(故作)大气地安慰他:“没事儿,这次就这样吧,下次换个稳妥点的厂吧,您继续往下走装订吧。”
老钱儿如释重负地恢复成人工智能走了。
现在只能希望,
读者看到这忧郁的深蓝和草绿两种书眉,不要忧郁,
这其实是我们又一个特别的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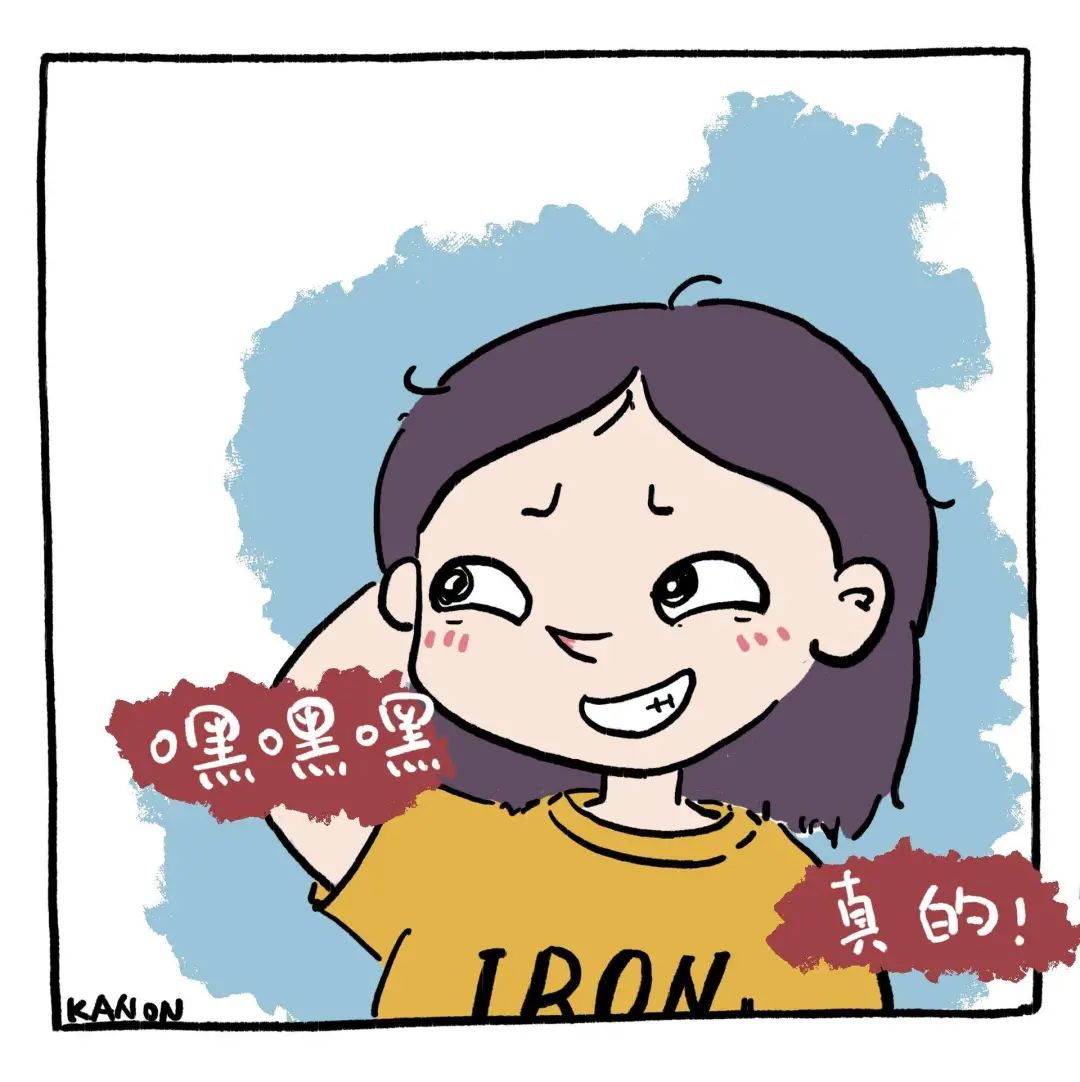
(二)
印制南哥曾经是个美编。
社里的印制不够用了,好几个老印制要退二线,新来的还在代培,人已中年的美编南哥于是被调来救场(赶鸭子上架)。
美编南哥就这样变成了印制南哥。
满脸花白的胡子茬,不羁、沧桑,是美术科班出身的南哥身上,残留的一丝艺术家梦。
深度近视加提前老花,让镜片后南哥的目光总处于失焦状态,好像永远游离于当前之外。
而成为印制之后,那一丝残梦更是飘去了远方,南哥的目光也越发茫然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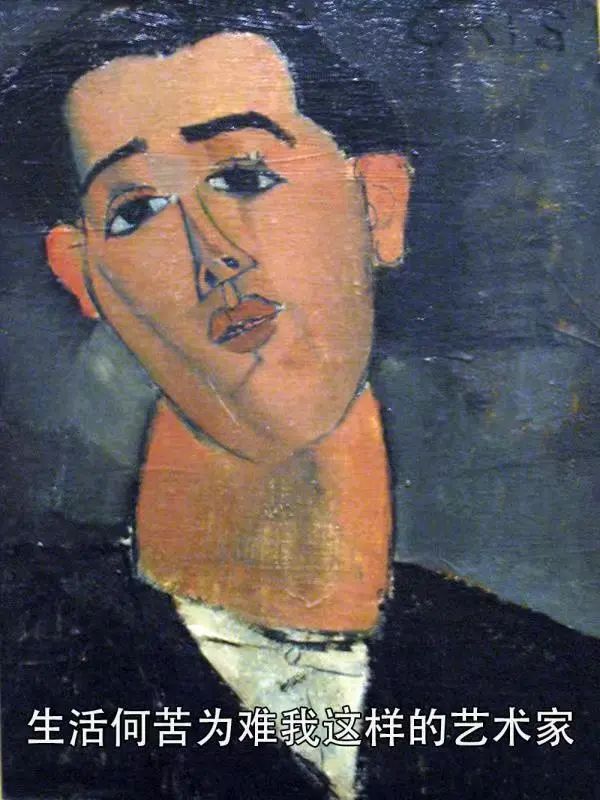
那些每天早晨哼着小曲打开iMac,端着茶走到窗前,从深秋的柿子树上汲取设计灵感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曾经认为并不需要看色卡,自诩脑中就有一本色卡可随意调用的人,这回真的不必再看色卡了。
工位虽然只是搬到了对门的办公室里,印制南哥却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人生,而这个人生里没有惊喜,只有惊吓。
每日惊吓从打破清晨薄雾的电话铃声开始……
“南哥,我那本书怎么还没给蓝纸呢?已经两周了啊。”
“南哥,前天跟你说的假书做好了吗?怎么还没给我送呢?”
“南哥,昨天那本书的版权页和封底的定价怎么不一样啊!”
“南哥,我的点校样你昨天回厂了吗?怎么排版厂还没传文件?”
“南哥,昨天那本着急入库的书怎么还没入?营销跟我说还是没有货发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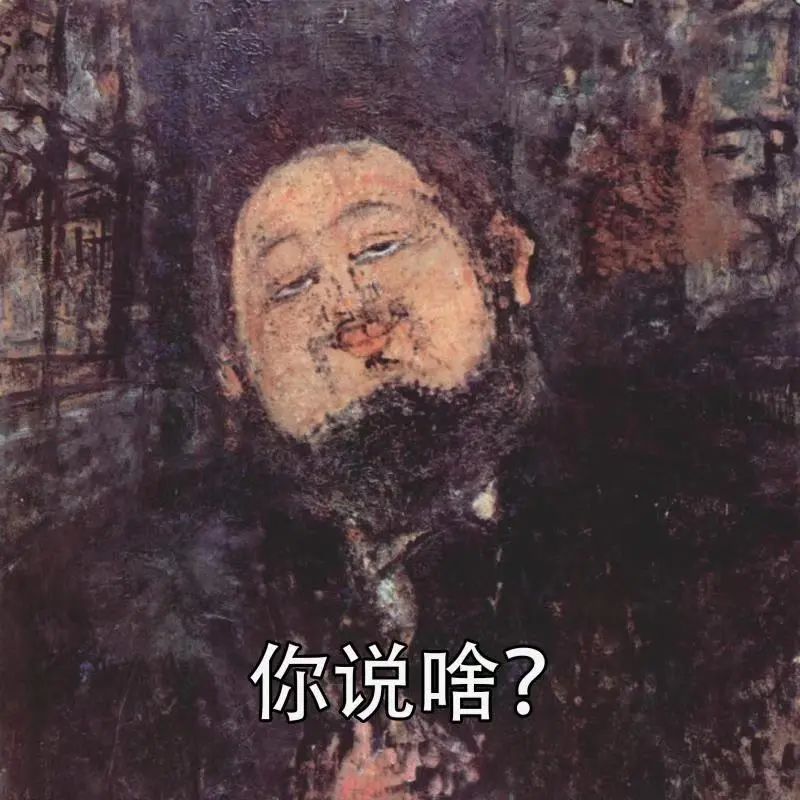
面对所有的质疑和挑战,南哥统统用一句简短有力、百试不爽、一招制敌、直击要害的话,把来电的编辑们挡回去:
“哪本书?”
电话另一头无一例外一阵沉默。
然后南哥立刻熟练地把电话移到耳膜十厘米远,任由那头的疾风暴雨化为冷冷冰雨打在脸上。
打开电脑里老印制老钱儿发给他的表,一溜书名后面,记录寥寥。大片的空白就像他的脑子,干净得如被扫过的地面。
南哥拍拍脑袋,希望能把那些遗散在角落的记忆碎片拍回原位。
做美编的时候,他打开电脑看一眼photoshop的图层,就能回忆起昨天未完成的各种细节。而印制的表里,总有太多要填的进度和细节。一转身忘填了,这根记忆的线索就断了,然后待印的书们就如断线的风筝,飞上高空无迹可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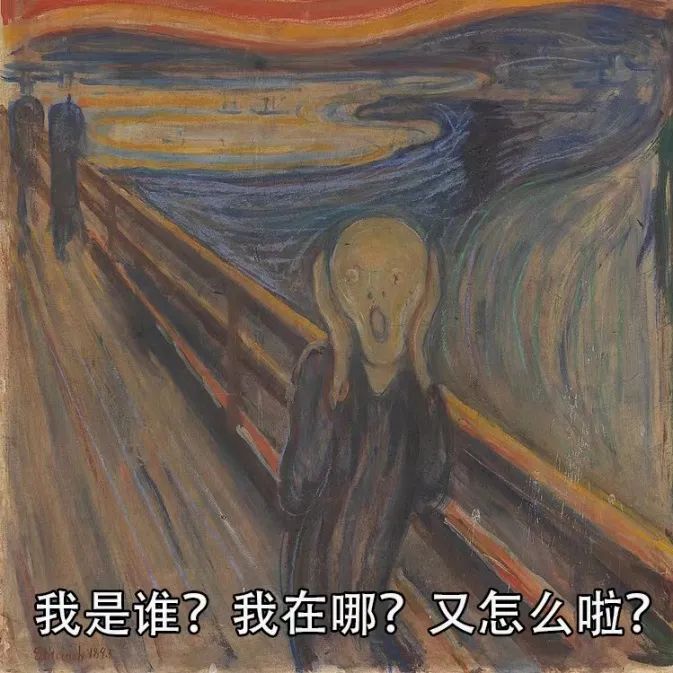
印制老钱儿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这张表了。
老钱儿的整个职业生涯仿佛都浓缩在这张表里。
每本书从收点校样开始,到传文件,开单,开机印,入库,每一步都有迹可循,环环相扣,老钱儿眼前仿佛有条无形的流水线在各部门间流畅运转,而他正精心操控和指挥着整条流水线,掌握一本本新书诞生的面貌和体态。
老钱儿觉得说书是编辑生的,有失偏颇,没有他们,书只是浮在脑海中的一个影子。
书明明是他们生的。
南哥还无法拥有老钱儿的这种情感。
南哥目前想的就是怎样尽快把脑子里的空白填上,以及把那些飞上天的书的线索都抓回来,握在手里。然后跟编辑们一一回电话,对她们说:
“别急,你再把书名跟我说一遍。”

编辑们都替南哥着急。
其实也不是替南哥着急,大家是替自己的书着急。
毕竟编辑做书一路走来,战战兢兢,波折坎坷,打怪升级,好不容易站到印前这个最后环节了,又被南哥绊了一跤掉进个错误百出的大坑,能不能爬上来凭运气。
书做砸了,受损最大的还是编辑。心血努力成泡影,卖不出去成炮灰。
“你怎么不记录呢?”王编辑说,“你上次传完文件,要是及时记,后面也不会忘开印制单,这一放就是半个月,说好的十月初入库呢?我还要赶双十一呢!”
“封面是用亮膜还是亚膜,你当时要记下来,就不会错了。这封面风格都是按亚膜设计的啊!”铁编辑说。
“前天我做了假书,厂家忘送了,你也忘了问了,作者今天催我要呢!”张编辑说。
“我报给你的定价,你当时没记,现在erp里和版权页都错了,只有封面是对的。怎么办啊?撕版权页重做吧?”刘编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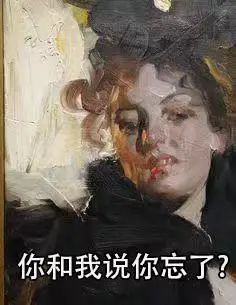
其实编辑们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及时填表。”老钱儿掷地有声的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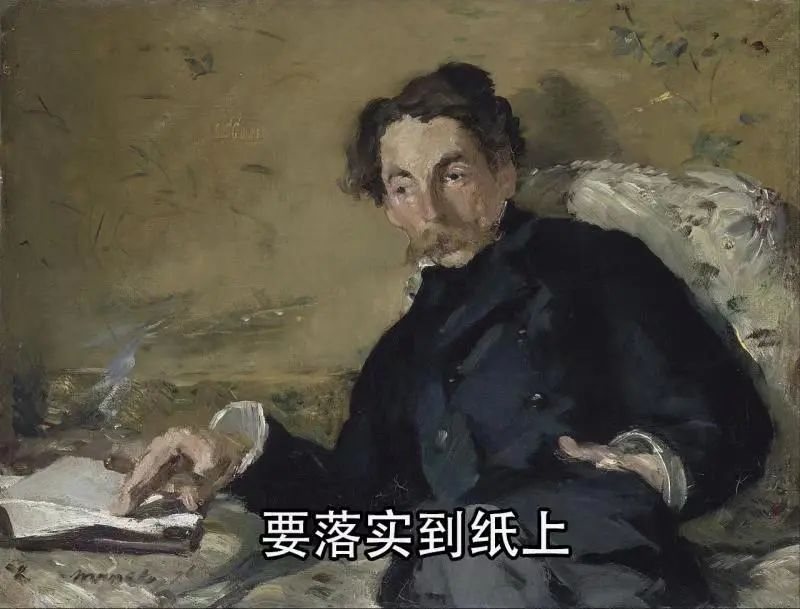
南哥不是不知道及时填表的道理,只是他的脑细胞们自由散漫惯了,它们抓得住瞬间即逝的灵感,能把各种色彩、形状、线条进行排列组合,却无法有序地组织起来,合成一张“生书”分解流程图。
印制的每个环节无序的堆积在他脑海中,好像一座坍塌的废墟。
眼前,老钱儿还在跟他阐述“电脑里有表,手机里有表,心中有表,人表合一,人在表在,人不在表也在”的道理。
南哥的心却早已飘向了不知何方,他呆呆地看着老钱儿还在一张一合的嘴唇,想起的却是那些过去的时光。
那时他还是个肆意挥洒鼠标的高级美编,喝着浓茶,发红的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一边满网找灵感一边薅着头发。
那样的日子,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