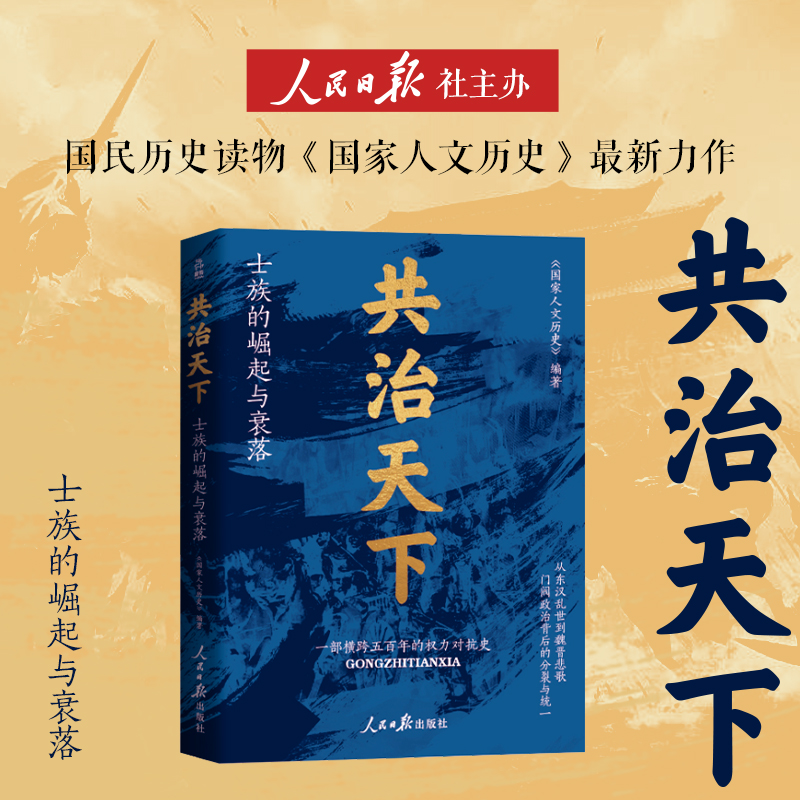古代变法,从来是阻力多多。
主要是因为变法是否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很难说。
具体就商鞅变法而言,商鞅鼓吹说他的新政令能使秦国强大,秦孝公一听就开心了,但是秦国的普通人,也就是秦国的国人会怎么想?
秦国强大,太好了!但是强大之后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根据后人对秦灭六国斩首人数的记载,可知一共杀了186万人。假设双方的战损失比例是五比一,那么秦国就死掉了近四十万人,而当时秦国全部人口,即男人女人小孩老人加起来一共才780万人,可想而知这是多少家族男丁的消耗
(以至于秦末刘邦西进时秦国几乎没有足够的男人组成军队来抵挡)
。
和壮年男劳力的大量消耗相比,得一点田地金帛上的赏赐,其实是不能成正比的
(这也是后来起义军进攻咸阳而关中父老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
。如果商鞅告诉秦孝公及全体国人,变法确实能使秦国强大,但秦国将有四十万男丁死在战场之上,而秦国王室血统更将彻底灭绝,请问你们的选择是什么?
当然这个选择题超纲了,我们还是回到商鞅变法现场,当时的秦国国人,不知道这场变法会让自己的国家变得那么强,更不知道在未来的战争中会死那么多人。国人只知道,打东方来了一个叫鞅的男人,他要把秦国原有的一套法令都改掉,他们会怎么想?
胡闹!忽悠!大概率是吹吹牛,显摆自己多么聪明而已。吹完牛,一切照旧!
而商鞅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他的对策也非常简单粗暴:
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五十金就解决了老百姓的信任问题,你说商鞅厉害不厉害?但是,变法的最大反对者,不是老百姓,而是权力阶层。
秦国的权力阶层,除了国君之外,就是卿大夫。
打个比方,如果秦国是一尊三足鼎,那么国人是一足,国君是一足,卿大夫就是第三足。

从当时来看,卿大夫也是变法的受害者。在秦大一统之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君归君,臣归臣,民归民,大家各有自己的权利,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若是贪婪到想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入自己之手,那么众人都会反对你、推翻你。三者中,国人地位最低,和平时期提供粮饷,战争时期提供兵源。国君地位最高,但主要权力其实是在祭祀和对外交往。卿大夫地位居中,却掌握着这个国家实际治理的权力,对下号令国民,对上则向国君定期汇报成果即可。
秦国的国君,要作出一项决策,必须召开廷议,即听取卿大夫的意见。而早期的秦国卿大夫几乎全是秦国的“公族”,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族长
(秦王)
和族中长老
(卿大夫)
的议事会。这是一种早期的分权政治,与秦始皇才开始的君主集权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如秦始皇“一人独裁定国是”的做法,在他之前的秦国,其实从来没有实行过。所以,商鞅要变法,最大的阻碍,就是公族。因为他要改变、瓦解、摧毁的,就是秦国公族说了算、秦君只是拱拱手的传统体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商鞅和秦孝公彻夜长谈,秦孝公“语数日不厌”。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秦国的创业史。秦国,并非周武王分封诸侯的第一批入选者,它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秦国的祖先是蜚廉,看过《封神演义》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司马迁告诉我们:
“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在商纣王最后的战斗中,恶来被杀,而蜚廉却幸免于难,隐居到霍太山
(今山西太岳山)
。蜚廉是商朝的驾车好手,他的子孙延续了这个优势,所以到周穆王时期,蜚廉的后裔造父成为周天子的车夫,并立功受封,得了一座城叫作赵。所以秦国的皇族,是嬴姓赵氏,嬴姓代表祖先的根源,即舜时期的伯益
(一般情况下姓是指母系起源一致,史书上有大量案例)
;赵氏则代表宗族系统
(氏是父系源头一致,汉以后姓氏合并,其实是用氏完全取代了姓)
。秦国和赵国,是一棵大树上的两个分支。


周孝王时期,秦人的直系祖先非子,被安排到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养马,稍后给了他一个“附庸”的身份,而这,一般就被视为秦人立国的开始。所以,秦国的“公族”,就是当年跟随非子,从山西来到陕西的第一批秦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嬴姓赵氏”一族,只不过在秦国自己的史书上,一般提到他们的名,都没有姓氏,享受和国君相似的待遇,就好像“秦王政”,史书几乎不提“赵政”,更不用说“嬴政”这个只有后世才有的奇怪称谓
。
也就是说,秦国是嬴姓赵氏的族人一同打造而成的。大家都是嬴姓后裔,一起来到长林丰草的西部养马,一起与野蛮的犬戎厮杀,一起建起这秦国的城池与边疆,凭啥你秦王一人说了算?按照分权时代的规则,从秦国初封,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统治权,其实都牢牢掌握在这批人手中。具体来讲,则是王室享有“统”的权益,公族则负责“治”。大家都是嬴姓一族,利益共沾、分工合作,很合理啊!但是如果出现不合格到离谱的某些王,公族会做什么事呢?

《史记》记录的秦国第一个重大国内事件,就是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末的“秦国大庶长弑君事件”。大庶长,这个名词大家初听比较陌生。商鞅变法之后施行的军功爵中,第十级为左庶长,第十一级为右庶长,第十七级为驷车庶长,第十八级为大庶长。也就是说,大庶长是秦国政治体系中,仅逊色于彻侯、关内侯的爵位。
商鞅变法之后,大庶长是高级爵位,而在变法之前,大庶长就是秦国的上卿,即后世的宰相。商鞅变法之前,大庶长这个职位基本为公族所垄断。即便是百里奚、蹇叔这样深得国君器重的外来人,也仅能担任左、右庶长之职。
那么,公元前8世纪,秦国的大庶长
(宰相)
做了什么呢?《史记》告诉我们:
“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
这里必须说的是,《史记》全书最靠谱的部分,就是秦国史,因为秦始皇焚书不焚秦国国史;也因为《史记》作者司马迁的先祖,本身就是秦国人——秦国伐蜀的名将司马错,就是他的祖先。而这段史料,虽然描述得很简略,但是基本事实很清楚。那就是秦国此时的三个大庶长,他们的名分别是“弗忌、威垒、三父”,如果按照现代表述就是:“秦国宰相赵弗忌、赵威垒、赵三父,废除了太子,立五岁的弟弟为国君
(即秦出子)
。六年之后,赵三父等人又杀死秦出子,重新拥戴昔日的太子做国君
(即秦武公)
。”当然,秦武公心里还记着仇,所以三年之后,他又以“杀死秦出子”的罪名,将赵三父等几个人的三族全部夷灭。


这场权力争斗,说到底就是赵家的家族内斗。虽然最终以国君的胜利告终,却给后人
(其实是秦王室的后人)
一个历史教训,那就是:“公族其实并不可靠。”
正是借鉴这样的历史教训,到秦穆公就开始引进第三股势力,即外来人才。理由有两个,明面上就是为了秦国的强大,此时已经是春秋之世,秦国为了能与周边强国
(春秋时期主要是晋国)
竞争,需要采用一种类似后世“人才引进”的政策,吸引若干外部人才,来担任秦国的卿
(稍后有一个专门称呼,叫作客卿)
。由此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原来的“世卿世禄”出现了新元素,在家族世袭的公族之外,多了几个外来户,且这些外来户因为功绩,能够享受与原本公族类似的待遇
(包括世袭)
。而这就是不可细说的另一个理由,即在秦王和强大的公族之间,引进一股第三势力
(外来人才)
,而这个第三者,在秦国并无根基,他的权力地位完全取决于秦王对其的信任,换句话说,他就是秦王用来压制公族的武器。
史书可查秦国引进的第一个外来人才,叫作百里奚。百里奚是虞国人,姜姓,百里氏,名奚,此时流亡到楚国养牛,秦穆公用五张黑色公羊皮将他赎回,委任他做大夫,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五羖
(gǔ)
大夫”。秦国之后能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他的功劳是最大的,所以奚家也就成了此时秦国的宦族。百里奚的儿子,在史书上叫作“孟明视”,很容易让人误解他姓孟名明视,但其实他也是姜姓、百里氏,名视、字孟明,他曾经在崤山之战中惨败给晋国,之后报仇雪恨,赢得了王官之战的胜利。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蹇叔,这是秦国引进的第二个外来人才。后来在秦国做到上大夫,再升为右庶长。蹇叔有两个儿子,担任了孟明视东征的副将,即白乙丙和西乞术,丙和术,是他们的名;白乙和西乞,是他们的字。
秦穆公时期引进的第三个外来人才,是由余。由余是姬姓,周朝王室的后人
(直接来源可能是周幽王的弟弟周携王)
,在西周末年二王并立的争斗中,周携王战败,他的族人便逃往西戎。由余,便是这些族人的后裔。秦穆公将由余引进到秦国,委任他做上卿。随后正是在由余的主持之下,秦国放弃向东与晋国硬碰硬的念头,转而向西,征服西戎十二国,于是称霸西方。那么问题就来了,百里奚、蹇叔、由余三个外来家族的融入,是否改变了秦国公族势力强大,甚至在某些时期凌驾在秦王之上的面貌呢?答案是否定的。
秦穆公是秦国第九任国君,等到第十九任国君秦怀公时期已经是战国初期,中原的韩赵魏正强盛,而秦国,又一次发生了公族与国君的冲突,而这一次,依旧是国君败:
“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领头的庶长赵晁
(鼂)
,甚至直接带着一帮大臣把国君秦怀公围了起来,逼迫他自杀以谢国人。
完了吗?还没呢。
公元前385年,庶长赵改发动政变,又杀死了第二十三任国君秦出公,史书描述是“沈
(沉)
之渊旁”,即丢进沼泽看他慢慢沉没
(
不得不说够无情)
。也正因为上述案例,记录历史的秦国史官才沉痛地说:
“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这里的晋指三分晋的韩赵魏)复强,夺秦河西地。”
不过,在这里也要说一句。说秦国的公族有多嚣张,这个“嚣张”在很多时间段其实并不是贬义,因为公族也是嬴姓赵氏,所以他们废立国君,并非没有理由的胡作非为,通常是因为这个国君不称职。
如果把秦国看作一个股份公司,国君就是总经理,而公族就是股东大会,通过股东会议表决,是可以罢免董事长的,而反过来,董事长却没有权力开除股东。所以,公族废黜君王,并非乱臣贼子的行为。
秦出公死后,公族迎接公子赵师隰
(xí)
回国,即秦国第二十四任国君秦献公。秦献公推行废除人殉、迁都栎阳、建立商市、编制户籍、推广县制等改革措施,对外则挫败了三晋的进一步入侵,公族对他的作为很满意,于是最终给他的谥号是“献公”,按照谥法,只有聪明叡哲的君王才有资格享有这个“献”字——当然汉献帝那个就另说了。
秦献公之后,便是秦孝公登场了。秦孝公初继位的时候,年纪不过二十出头,虽然他老爹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秦国的危局,但三晋依旧占据着黄河以西的大块土地,必须说,秦国并未改变不利的大局。而公族,在秦孝公看来,显然是拿不出一个救国的方案。他需要借助外力,才能拯救秦国的危亡
(不可明说的隐含目的,是借外力压制公族,实现国君权威的提升
)
。
于是秦孝公发布了著名的求贤令: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个名为“鞅”的男人,这便来到了秦国。
前359年,一场关于“要不要变法”的廷争,便在卫鞅和秦国的大臣们之间展开。司马迁说:“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请注意,这里的甘龙、杜挚,严格说起来并不属于秦国公族,他们是旧贵族,但不是嬴姓赵氏这个核心部分。可以这么理解,鉴于秦孝公对变法的支持,公族不便于直接反对,所以他们让相对外围的非嬴姓赵氏贵族甘龙、杜挚,出来表示表示。
甘龙,来自甘氏家族,完整的表达是姬姓甘氏,源自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国甘国,在现在陕西省的鄠县西南一带,后代以国为氏。杜挚,来自杜氏家族,完整的表达是祁姓杜氏,杜国在今陕西西安的东南部,被秦吞并之后,可能一部分贵族也加入了秦国,并以国为氏。

这就好像打牌一样,在尚未明确对手的实力之前,你不会直接打出自己的王牌,更常见的选择是丢几张杂牌试试水。结果一番辩论,甘龙、杜挚完败。那么秦国公族呢?自然没有就此认输的道理。
之后,甘龙、杜挚背后的人亮相,便是公子虔、公孙贾,他们都是嬴姓赵氏的公族,按照今天的叫法,其实应该是赵虔、赵贾。公子虔、公孙贾的办法,一是发动老百姓,在各处说新法如何如何不好,造成舆论渲染;二是利用太子老师的身份,推动太子赵驷
(即
后来的秦惠文王)
触犯新法。在公子虔、公孙贾看来,卫鞅你胆子再大,也不敢动太子吧?而只要你不动太子,这新法自然而然也就流产了。这一招,真的很厉害。
对于卫鞅而言,如果放过太子,变法还变不变?不放太子,未来又该怎么保全自己?于是卫鞅,采用了一个在他看来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揪出幕后指使者公子虔、公孙贾,将他们施以刑罚,公子虔本该监督太子行为良好,结果失职,处以劓刑;公孙贾本该传授给太子足够的知识,也没做到,处以墨刑。这样一来,既打击了反对派,又没有直接伤害太子的本身,是不是很得体?只能说,卫鞅还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一死,公子虔等“公族”便发动了对商鞅的围攻,最终罗织的罪名是“谋反”,这就不是割鼻子能解决的事了,于是商鞅逃亡不成,潜回封邑商於,发动邑兵。此时已经是秦惠文王的赵驷发兵征讨,双方在彤地
(今陕西华州西南)
交手,商鞅在以少对多的不利情势下并无变天的手段,战败身死,最终尸体遭车裂示众。


秦惠文王即位之后,虽然没有改变既成事实的新法,但在一定程度上,既任用外人
(如张仪、公孙衍等)
,也重用嬴姓本宗
(如樗里疾、公子华等)
和秦国本国人
(如司马迁祖先司马错)
,这就很好地安抚了公族和国人的情绪。变法之后秦国的强大,也让反对者难以发声。

值得一提的是,最终导致秦朝灭亡的罪臣赵高,其实亦是秦公族的一分子
(但是非常疏远)
。这也正是赵高在杀害胡亥之后,试图自立为帝的理由,只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无奈之下,这才选择了子婴
(即琅琊刻石上出现的赵婴,秦二世的堂哥)
。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进击的士族
旁落的皇权
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
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
最新力作
展现士族潮起潮落的史诗级历史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