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

作者:
段
德敏(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
)
1
民主的胜利?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的许多举动,特别是其带有宗教歧视色彩的移民禁令,都被人认为与民主的价值相违背。因此当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们阻击了其总统的行政命令时,很多特朗普的批评者都欢呼这是民主价值的胜利。虽然这听上去好像没错,尤其是当我们把特朗普想象成类似希特勒这样的专制独裁者时。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特朗普是民选的总统;法官不是民选的,而是由总统提名就任的,同时也不需要回应民意。由非民选的法官制约民选总统的权力,如何能说这是民主的胜利?

叫停川普移民禁令的联邦法官罗巴特(James Robart)
类似的例子是在今天的德国,德国《基本法》
(也就是其宪法)
明确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有取缔政党的权力,其中第21条第2款写道:“凡由于政党的宗旨或党员的行为,企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或企图危及德意志联邦民共和国的存在的政党,都是属违反宪法的,联邦宪法法院对是否违宪的问题做出裁决。”这里的关键词是“企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什么才是其构成要件?起码宪法文本并没有规定清楚。仅就“民主”而言,假如有一群人积聚起足够的“民意”支持,从而组建了一个政党,但这个政党对德国的纳粹历史持“较宽容”的立场,甚或直接支持纳粹意识形态,那么这够不够成对自由民主秩序的损害?如果说是,那该政党难道不是对
(起码一部分)
民意的反映?如果说不是,则该政党确实是危险的,纳粹党上台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基本法》最初确立这一条款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此类政党的再次出现,因而赋予了联邦宪法法院以不一般的权力,它在认为有充足理由的时候可以强行解散一个政党。同美国最高法院类似,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并不是一个民选机构,它通常由数名联邦参议院议员组成的“法官任命委员会”来任命,长期、独立地行使职权。虽然在实际行使“取缔政党”权力时,同时又要维护言论和结社自由,因而他们通常极为谨慎保守地使用这一权力,但这一权力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构成对“民意”的防范功能。尤其是在当下,外来移民涌入和恐怖主义威胁之下,德国右翼势力崛起,已然有突破“反纳粹”这一政治正确的迹象,可以想见,宪法法院的“非民主”权力恰恰能够起到防波堤的作用。

在1924年选举时的纳粹党海报上,纳粹党被描绘成鼓舞“德意志之鹰”挣脱锁链的太阳。
通常情况下,司法机构要对“民意”起到限制作用,需尽可能地使自身脱离民意的束缚。原因无他,主要在于民意是多变的,其内部也经常是分裂和矛盾的。司法机构——尤其是具备违宪审查功能的司法机构——则应该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否则其公信力便会大打折扣,最起码在人们的观感中会是如此。从而,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虽然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但他们一旦上任便终身任职,除非自行退休或有重大行为不端而遭国会弹劾。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确实带有很强的党派色彩,这也是总统大选中的关键要素之一,很多共和党关键人物最后选择支持他们并不喜欢的特朗普,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想看到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一个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法官,打破最高法院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平衡,进而在一系敏感问题——如同性恋、堕胎、医保法案等——上做出不利于保守价值观的判决。然而,另一方面因为司法系统
(包括最高法院)
的法官们并不需要向任何其他机构负责,他们通常能保持其独立性。特朗普政府立即恢复移民禁令的要求在联邦上诉法院被驳回,做出一致判决的三名法官之一就是共和党总统小布什任命的理查德·克利夫顿。从原则上来说,最高法院法官们服从的是宪法,他们将自己看作美国立国之时所做承诺的守卫者、建国之父们的精神的传承人,独立于一时一刻的民意或民选机构的意见,并对后者构成制约。因此,称最高法院为一个权威机构不仅毫不夸张,而且切中要旨,它拥有巨大的权力,极其独立,同时人们对其公正性有极大的期待,犹如古代人民对公正仁慈的国王的期待一样。

2
民主与贵族
美国最高法院的性质和重要性使得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题:美国政治体制到底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阿伦特在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时指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政治体都需要一定的权威结构,它不能在无休止的革命中存在,美国的政治权威所在地就是其最高法院,它是其整个政治体系中不变的、自上而下发出命令
(裁决)
的部分。这一权威虽然在性质上和古代国王的权威相通,但也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例如其角色是“消极的”,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同时也不能干涉其他政府部门——行政和立法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实际上,美国建国之初就将“民主和非民主”的问题作为重点辩论的对象,而“民主”在当时而言远构不成一个褒义词。作为美国宪法思想基础的《联邦党人文集》中,麦迪逊等人明确地将其构想的美利坚合众国看作一个“非民主”的共和制国家。民主政体
(democracy)
和共和政体
(republic)
的两大区别是:“第一,后者的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第二,后者所能管辖的公民人数较多,国土范围也较大。”简单地说,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代议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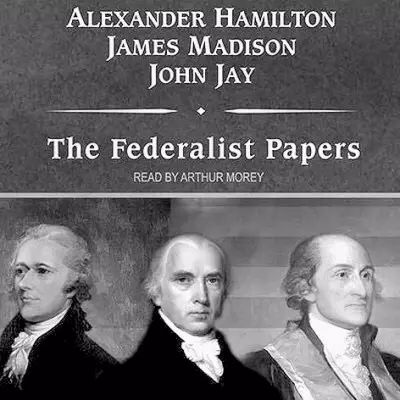
《联邦党人文集》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麦迪逊在这里所强调的代议制以及其中包含的政治代表和我们今天的理解可能很不一样。我们今天经常将政治代表理解为民众向其“代表”发出指令、代表尽可能忠实地执行指令的过程,类似于银行客户和其理财经理之间的关系,后者作为“代表”在投资理财过程中尽可能最大化前者的利益。这听上去很“民主”。然而,在“联邦党人”那里,情况却几乎相反,当麦迪逊等人在强调“代表”的重要性时,他们不是在说对选民唯唯诺诺、一切行动听指挥式的代表,他们十分清楚是在说一种新的“贵族”制度。这种贵族不是欧洲封建社会中那种以出身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传统贵族,而是建立在才智和德行基础上的所谓“自然贵族”
(natural aristocracy)
。联邦党人认为民主最大的问题是“党争”
(factions)
,即人们为了各自的观点和利益争论不休、内耗不断,以至于忘记或看不到那个“大局”
(the bigger picture)
,比如他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以及需要有人去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事实。联邦党人在这么说的时候,批评的主是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之前各州之间的龃龉,从而为联邦政府的权力确立正当性基础。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古代,国王通常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代表着联合、团结和理性,在今天有些地方仍是如此,尤其内部纷争比较严重的地方——例如比利时——更为明显。但这在美国显然不可能,毕竟其独立战争以及革命本身就是为了推翻压在他们身上的英国王权的压迫。

一幅描绘1787年美国宪法签字仪式场面的画作被悬挂在美国国会大厦
如何产生“自然贵族”?联邦党人将目光投向了选举,联邦政府由选举产生的长官构成,如总统和参议院议员,他们应该就是新的贵族。再一次地,联邦党人在用一种我们今天不那么熟悉的方式理解“选举”这一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更接近古希腊时期流行的观念,亚里士多德等人在讨论城邦政治时就将选举看作一种贵族体制,而典型的民主政体是用抽签的方式产生长官,从而体现公民之间的完全平等。选举的过程必然产生不平等,它必须有某种方式将那些被选出来的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否则选举就不可能产生结果。在古代,将人与人区分开来并使得一些人具有统治资格的,无非就是财富、智慧、德行等要素,因此这自动意味着那些更富有、受过更好教育、更能打仗的人才能做长官。因此,在古希腊时期,选举制和贵族制基本上是等同的。这一观点一直流传到近代,在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那里都清晰可见。美国联邦党人则将此作为确立一个自然贵族的统治、同时又跟身份平等的大原则不相冲突的方法,他们希望全国范围的选举能产生优秀的、更加独立于地方民意的长官,由他们来议决整个联邦的大事。这一选定的公民团体能“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因为代表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
英国在近代民主化的过程中逐渐扩大选举权,但早期选举出来的议员中几乎都是贵族,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从身份贵族到自然贵族的转变过程。美国建国之父们同样希望达到类似的效果,在王制政府不可行、民主又不可取的情况下,要统治如此大疆域的国家,这在当时来说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明。可与此进行比较的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曾经历了痛苦的民主与贵族两种价值、两种势力之间的长期较量,但不幸的是其结果基本都呈现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态势,从而暴力革命和专制复辟交替出现的局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870年以后才有实质性改善。这其中的关键正在于:能否既接受现代社会的社会境况,即身份的普遍平等,同时又以某种形式接受一些“贵族”要素,或起码同这种贵族要素达成有效的、开诚布公的谅解。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建国历程相较于法国革命后状况大为“优越”的原因,正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意地同“民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巧妙地保持了“贵族”制成份。这并不是说美国就真的是一个贵族制国家,即便在其建国之初,这也离事实很远。选举确实会产生“自然贵族”,但到底什么才构成自然贵族却不完全由政治代表们说了算,他们也需要积极地向其选民回馈其政治行动、听取选民的意见等等。如此,再加上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分权,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分权,立法机构本身内部的分权,基本上可以确保权力的运行处于一种较为平衡和理性的状态,既不失民众的参与,又确保了有更高、更理性的智慧在照顾国家整体利益。可以说,这是联邦党人最初的设想,同时也是美国延续至今的宪制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