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膜
节选自《风景的诱惑》(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房伟 著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本文由「阅读培文」授权发表。
第一次知道赵本山,是1990年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一边吃饺子,一边看春节联欢晚会。突然,一个着装怪异的农村中年男人走上了舞台,接着他仿佛变魔术一般看了看表,说了一句:「哎呀妈呀,才4点60呀。」我们全家都笑得放不下筷子。从此,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赵本山」。

许多年过去了,一个快乐的赵本山一直在伴随我们的成长,他从「徐老蔫」变成「老乐」、「老香水」,后来,又变成「妇女主任」、「村长」、「农民企业家刘老根」,一直到「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人陪聊的快乐农民」和「靠卖拐、卖车坑人致富的刁民」。

《相亲》(2011)
在现实生活中,赵本山也从一个「受大家喜爱的小品演员」成为「农民艺术家」、「东北文化代言人」、「辽宁税务宣传大使」、「人大代表」、「电视导演」一直到近来媒体大谈的「世界艺术大师」、「东方笑神」、「东方卓别林」。
一个朴实可爱的农民离我们远去了,一个人格高尚伟大、富有庄严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大儒赵本山,一个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热爱民间的艺术家赵本山,同时又是「包飞机回家过年」的富豪赵本山,一个「被外星人劫持」、「状告模仿者」、「抢注刘老根商标」、「和香港艳星传出绯闻」的文化明星赵本山,却浮出了充斥文化泡沫的海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赵氏喜剧不断走向恶俗和炒作,对赵本山的小品艺术,也有越来越大的争议性,甚至是尖锐的对立。可以说,赵本山的小品,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症候」。
赵本山是谁?我们似乎只能得到一些模糊古怪且矛盾的印象:他头上戴着一顶深色的帽子,虽然不合城里人的规范,但在乡下还是很常见;身穿一件中山装,脚上是一双布鞋。
但是,他有时会有一双套袖,表明了这个乡下人可能正在城市的底层混一口粗浅的技术工作(比如木匠)。有时,他的中山装上会插一支钢笔,以显示村干部的身份和好学上进的努力。当然,他也可能换下中山装,穿一件西装或脚蹬一双廉价旅游鞋,以表示他是一个已小小致富的农民,或新鲜消费潮流的拥护者。

《不差钱》(2009)
再让我们来看看长相。他前期作品最大特点就是性别不清、年龄不清。他弯腰弓背,走路一走一忽悠,说话声音尖利、高亢,透着一点玩世不恭,随时可以引人发笑,却又有女性细腻的敏锐,可以随时引发人们同情。
用本山自己的话说:「有点像老太太。」男性的女性化,使之取得了边缘优势,他长着一张饱经沧桑的脸,额头皱纹密布,显示着农民艰难的生存,两腮却十分饱满,眼角眉梢带着笑意,显示着积极乐观的天性,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在35-65这个年龄阶段游动。
由此判断,我们可认为他是农村中喜欢说个怪话、有一定批判意识、对主流官方意识形态起解构作用的边缘农民形象。他头脑较灵活,有一定艺术才能,如徐老蔫。

他对自身处境有清醒意识,他将自己在稳定有序且等级森严的世界里自我放逐,成为这个世界不合时宜的局外人,他会经常闯入这个正统世界,揭示这个世界假正经和伪善的一面,他的笑声是双重的,既笑别人又笑自己。
但是,这个形象在他后期作品中却不断发生改变。「阳刚之气」越来越足,他又似乎是一个主流农民形象,是帮助大家脱贫致富的农民企业家。他对城市文明有天然警惕和反感,极力通过宣传农村思维方式获得压倒性地位。

《红高粱模特队》(1997)
但《卖拐》后他又成了一个刁钻恶毒的城市游民,显示不择手段的恶意强悍。他的目的是利用人们对习惯思维的迷信,来惩处和捉弄他们,从中捞取好处。他的看家本领就是吹嘘,他在高姿态和低姿态中来回地高攀低就,通过吹嘘将「崇高」和「神圣」引入到无拘无束的把戏中去,使之获得反讽意味。
关于赵本山的喜剧形象,我们似乎可分成几种简单原型:A. 善良幽默的落后农民;B. 拥护党的领导的致富农民;C. 巧言令色的骗子。
这几个形象差别很大,这不仅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显性规则硬性规范的结果,也是媒体、市场、民间多重作用力共同对农民形象改造的综合结果,它也暗含中国现实中利益冲突和妥协的潜性规则。

《刘老根》(2002)
同时,这也体现为一种文化身份定位的错位和杂糅。在城市/农村,市民/农民,雅/俗的双重身份对峙中,赵本山不断摇摆和游动,始终处在文化和商业利益的最佳结合点。
喜剧起源于对不同身份人物的反讽性模仿。然而,在赵的喜剧中出现了正剧色彩,使这种反讽自身日渐陷入尴尬境地。显然,本山并不是一个传统农民形象,他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象征性寓言,正如卓别林的流浪汉形象,已成为20世纪西方大萧条时期代言人,赵本山的身体形象,也已成为政治学意义的符号。
也许,我们可以从斯图亚特·霍尔的一段话中理解赵本山艺术形象千变万化的秘密:「文化身份不是发现,而是一种生产,它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部稳定的点……它不是本质而是定位。」
赵本山系列人物的多次文化定位,正契合了目前看似多元,实际上一元权力结构在转型期的碎片化表现。同样,我们也可解释现实生活中,赵本山身兼为民娱乐、为民请命、艺术精英、道德楷模、文化明星多重身份的秘密。

中国人对权威身份的认可,来源于对话语权威的无条件认可的敬畏感和恐惧感。一个人一旦取得权威身份,其他权威身份就会成为附加物。比如人们习惯于把艺人看为「艺德双馨」,从而使其成为道德权威。
这种心理学「晕轮」效应,在中国由于权力控制的紧密而成为权力泛化的土壤。中国转型期隐性权力运作的层级上的碎片化文化生态,使赵本山的文化身份进一步发生变异。
对农民形象的嘲讽,早在中国北宋的喜剧艺术中就出现了,例如「杂班」表演中就有针对当时京东(山东)人进汴梁城时种种表现的嘲弄,舞戏中也有农民搞笑式的「舞鲍老」,这也是在城乡雅俗对峙格局中的重要文化表现之一。
这种具边缘气质的农民题材表演,一般具不确定性,并借助一系列广场人物的即兴表演得到强化,赵本山小品就有很强的即兴化的广场表演特征,比如他并不严格遵守剧本和主题,而会根据观众反应,及时加入新东西,一方面调动观众情绪,另一方面也显示广场文化拉近距离的需要。

赵本山封箱之作《中奖了》(2013)
同时,在赵本山的后期表演中,这种边缘性不断减弱,对权威的脱冕仪式,变成了维护秩序的加冕仪式。赵本山初期喜剧特色是游走在意识形态边缘,他利用边缘文化身份,不断消解秩序的权威。
然而,由于文化语境的强大整合和吸纳功能,这种挑逗和消解,又不断被「反消解」,他的边缘身份,反而成了秩序加强「维模」功能的证明,刺激并激活了秩序潜力,造成边缘性的不断丧失。
同时,狂欢的喜剧形式通过反讽叙事来解构权威,也通过反讽拉近和权威的距离,从而产生亲近和顺从。这也就是说,赵式喜剧具双重性,它本身也蕴涵着和秩序妥协的力量。

《捐助》(2010)
秩序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不但可以让人哭,且可以让人笑;可以剥夺人思考的权力,也可以剥夺人不思考的权力。只不过,当来自底层的狂欢完全变成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图解和空洞的恶作剧,笑声也就变成了勉为其难的捧场和无趣的自恋。
我现在仅以《相亲》、《红高粱模特队》、《三鞭子》、《昨天 今天 明天》、《卖拐》等几个赵本山十几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例子,来展示赵本山喜剧创作由边缘民间而被整合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轨迹及在这个过程中,赵本山表现出的尴尬「喜剧性」。

《相亲》(1990)
《相亲》是赵本山的成名作。他以「老年人的幸福」为主题,其移风易俗的社会功利目的,反封建的明朗风格,颇似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现实的矛盾尚没有显示其尖锐性和沉重的一面,除了「小琴他妈差点扒了火车道」一个短暂介绍外,人们来不及思索,就湮没在赵本山那来自民间的原汁原味的生存智慧和乐观积极的幽默中。
小品的内在矛盾以误会开始,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告终。思维方式和情节矛盾的编织,都来自民间,老年人婚姻以儿女的理解掩盖了经济和伦理情感问题,所以在主题思想上显得较单薄。

这时候的赵本山和主流意识形态基本是疏离的,而非反抗或迎合,赵本山扮演的「徐老蔫」,对世态炎凉有一定认识,勇于追求幸福,同时又顾全大局,有传统农民吃苦耐劳和宽容善良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小品中最引人发笑的,主要是赵清醒的「自嘲」。
一个善良幽默的农民使我们倍感新鲜与亲切。这个追求「幸福」的主题在之后的《我想有个家》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挥。这一次,本山的成功试图被导演迅速整合入官方语言,于是就出现了「致富」后的农村三级木匠电视征婚的喜剧。这个小品总体是不成功的,主题没有突破,赵本山的表演由于形象设计的突然改变,有一些举止失措,表情过分夸张更使人感到困惑。

《我想有个家》(1992)
于是,赵本山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磨合,在《红高粱模特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以至于引发了人们对小品主题的质疑。这个小品的内在矛盾是:代表都市精英意识的模特文化和代表农民意识的秧歌文化的冲突。

《红高粱模特队》(1997)
但如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所谓农民意识的秧歌文化,只不过是都市大众传播的猎奇方式,民间歌舞的粗犷和俚俗的性意味不见了,民间歌舞突破秩序束缚的叛逆精神不见了,剩下的只是精致的、符合城市欣赏口味的伪民俗风味。它所宣扬的是什么呢?一群具绝对专业水平的所谓「业余」牤牛屯模特队表现的是什么?名模=劳模的公式好笑吗?「土地是妈,劳动是爹」的口号,多大程度上是正确可行的?
民间经过权力意志改造后,便使愚昧和顺从被赋予了神圣光环。农民的狭隘经验一经放大为主流教条,就会成为可怕的东西,这已是几十年来最深刻的教训。谁又能说这种思维方式消失了?
《三鞭子》和《拜年》是赵本山最好的喜剧小品。这是他挣脱羁绊,进行喜剧在题材、思想和艺术性上独立探索的努力。然而,他依旧是农民,他表达了一个农民对越来越尖锐的农村问题的朴素义愤:
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所以我最了解农民的生活。每年我都要回老家好几次,可是每次回去,乡亲们都围着我,排着队等着向我借钱,有些老乡辛苦干一年,到头来还是穷得揭不开锅,他们见到我,就抱着我的腿哭啊………比方我的家乡,据我所知,教师的工资也发不出来,农民一辈一辈都生活在没文化状态,这让人痛心呀!
小品表达了对「金钱至上」观念的嘲讽和抗议。同时,对官僚主义、城乡差距也表示了愤怒,但是,他表达的目的呢?他不过是在「今不如昔」的感慨中,期望「像当年八路一样好」的清官。

《三鞭子》(1996)
一旦基层民主失去必要而畅通的渠道,对制度的依靠就必然化为对个人的依靠。《拜年》中赵老蔫对官员罢免的态度变化,令人深思。《三鞭子》结束时,本山那一跪,跪出了千百万农民的辛酸和无奈,也跪出了沉重的启蒙的必要。喜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

《昨天今天明天》(1999)
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赵本山的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又回归了「富裕农民感谢党的领导」的路子上来。「实话实说」的民间威信加上赵本山的大众形象,成了这个节目引人注目的因素。古今中外的对比中,「改革春风吹满地,齐心协力跨世纪」、「总揽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的主题呼之欲出。
这个小品中,赵本山改进了原有的语言特色,杂糅农村土语、方言、城市时髦用语、歌词、文化精英语言,取得了语言运用上较突出的喜剧效果。喜剧的讽喻味道减轻了,喜庆节日气氛被弘扬,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宣传政策的「寓教于乐」、「安定团结」的改造民间艺术的基本出发点。

《卖拐》(2001)
2001年的《卖拐》对「东北赵式喜剧小品」的意义很重大。它一方面是赵本山在体制内挣扎后的被迫转型,另一方面表现为赵本山对范伟的改造。虽然赵本山还穿着一身农民服装,但他已不是一个农民了,而完全像古罗马帝国熙熙攘攘都市里尖酸刻薄的俳优。
他丧失了农民的善良和质朴的「自嘲」,并转而成为这种思维方式的「魔鬼终结者」。赵本山的小品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市民喜剧的特点,而抛弃了农村情节喜剧固定模式。
然而,他需要一个不值得让人可怜,并让观众找到优越感的角色。于是,范伟应运而生,范伟从早先的知识者和城市市民形象,被改造成新一代游民形象。他的顽固和愚蠢,破坏了弱者引发同情感的道德基础,从而消解了人性关爱的价值,他是秩序受害者,却不思进取,真诚地维护秩序对他个人的伤害,并使之合理化。

《卖拐》、《卖车》中,范伟完全是一个不值得人同情的「愚民」,他的悲剧性命运,只不过是为大家增加一点恶意笑声而已。本来一个可以揭示出人类在权力关系中无法摆脱的命运的素材,却在赵本山的手中成了一场都市闹剧,这也不能不成为中国文化现状的一种隐喻。
尽管,《功夫》中,小品又对「好人好报」的朴素伦理有所反拨,但是,赵氏小品从喜剧走上恶俗已不可避免。

《不差钱》(2009)
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赵本山又借助他的徒弟小沈阳,将东北二人转文化中「恶俗」部分,进行了极致性的夸张。很多二人转的策略,比如「男扮女装」、「性俚语」等以往属于夜总会、村头草台班子的招数,也堂而皇之地登上春晚。
观众在「喜剧变爆笑剧」的心理中,满足的仅是「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人死了,钱没花完」这类消费畸语,而没有了任何道德底线和人性反思。这也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待娱乐的矛盾心态:既要求老百姓受教育,又要讨好观众;既要娱乐消费性,又要在娱乐中遗忘现实。
于是,当受教育的道德动机和意识形态规训发生冲突时,主流意识形态选择的是,以恶俗消费娱乐,装扮成民间文化合法代言人,进而让观众在恶俗中以「欲望」遗忘「批判」。

自此,喜剧内在的解构意味被破坏殆尽,一个政治农民脱贫致富的神话闪现在通往收视率的金光大道上。在这一点上,《不差钱》后的赵本山小品,和古罗马角斗士场中嗜血杀戮前的「俳优表演」异曲同工。
基于以上分析,赵本山系列小品形象,正是一个边缘化农民走入体制内的过程。这个淳朴憨厚的农民在主流召唤下,很快成为一个政治农民,并飞速成长为一面「脱贫致富」的旗帜。
同时,成立于新世纪赵本山旗下的「本山传媒」集团,曾于2008年初,被文化部授予除事业单位外的「中国文化经济实体30强」,以其固定资产30亿元的雄厚实力,横跨演出业、影视制作业、电视栏目业和艺术教育业四大领域。赵本山,这个政治农民,致富的好农民,狡猾的刁民,终于在新世纪成为披着「低俗外衣」的超级富豪。

赵氏小品,也就取代赵丽蓉小品、陈佩斯小品、山西「王木墩」式小品等多种小品类型,成为娱乐界唯一合法性的「娱乐主流宏大叙事」的小品帝国。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赵氏喜剧的接受史。「赵本山」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一边倒的文化现象。否认赵本山,就等于否认中国黑土地文化,否认民间二人转,否认中国喜剧艺术。
官方称之为「人民艺术家」,学界的余秋雨先生则认为:「赵本山作为当代杰出的喜剧表演艺术家,是受到全中国数亿观众评判的」;商家不断利用赵本山形象作商机,从北极太空棉到刘老根商标抢注事件,而赵本山的小品和电视剧也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官、产、学、民间各方对赵本山的一致欢呼,这说明了什么?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大众文化工业的特点。它是一种快感、意义和文化身份的选择,无论文化统治阶级还是文化从属阶级,都可利用意义和快感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
福柯说:「权力并不是自上而下的一股单力,而是一种双向力,权力结构应该是在对立中运作的双向、多元的权力层面。」然而,在这种权力对抗中,统治阶级努力把一种超阶级的、外在的性质强加于意识形态,平息或内驱这个符号发生的社会价值判断的斗争,把符号变成单声,从而使快感和意义在超阶级面纱下获得统一稳定合法性。
如赵本山小品,「劳动人民情怀」、「追求幸福」已成为超越阶级符号,所有农村尖锐的矛盾纠葛都在这一符号中不断被遮蔽和覆盖,从而使大团圆的伪喜剧成为超越人类荒谬的真喜剧的「劣币驱逐良币」,这在当代消费文化中有很大号召力、诱惑力和欺骗性。

《同桌的你》(2011)
其次,从接受学角度考虑,赵本山的小品隐喻着农民与市民、官方、知识分子等诸多阶层的错综复杂关系。农民的趣味表面上受到赞赏和怂恿,实际上,知识分子热衷于小品中机智的俏皮话解构主流权力话语;市民们有了嘲笑捉弄的对象;中产阶级和官方则看到了稳定和谐的秩序。
赵本山式小品却在这种「想象」的「一致喝彩」中不知不觉地延续了传统思维方式和等级观念。就民间而言,赵本山的意义首先在于快感。快感属于身体,是民间用来抵抗和颠覆权威的重要工具。农村大众看到赵本山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朴实的「土地精神」的内模仿,以弱势姿态形成对城市生活方式和金钱至上观念的价值抵抗。
就市民而言,重要的则是承认快感,并承认快感是个人的事情。市民阶层通过对滑稽的狂欢化人物形象的欣赏,获得对主流意识形态严肃说教的解构,并获取自身优越感。就官方而言,试图利用赵本山的出现形成新大众意识形态,借以平衡和缓和各个阶层情绪,并进一步将之纳入可控制的范围内。

赵本山小品强烈的图解政策的表现,可看作是一个需要/迎合的艺术政治化个案。2002年赵本山「辽宁税务宣传大使」的任命,可以窥见一斑。同时,我们还要看到,90年代后,商人成为权力阶层吸纳的重要部分,改革开放的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对大众意识形态具有很强影响力。也正是在商人们的运作和包装下,赵本山迅速成为商业品牌,并成为商业利润体系的一部分。
当然由于官方形象的原因,商业追求还没成为控制赵的唯一力量,这也表现在商人们对《刘老根》的巨额利润分配的抱怨上。中国知识界对赵本山的欢呼,是90年代后中国文化圈最令人寻味的文化选择之一。这可归纳为民粹保守主义的心态和犬儒的混世哲学。
一部分学者出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充分肯定赵本山小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时代是「欢乐的时代」吗?是余秋雨、赵本山们的欢乐时代,还是赵本山所说的「辛苦一年不够吃喝」的农民们的欢乐时代?

「几亿人民对欢笑的选择」是一个大得压人的帽子,在强势媒体和强势权力联合的年代,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农民们又有多少可选择的文化权力?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站在赵本山身后喝彩的文化人的动机是什么。
再次,我们还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这个较小的语境来分析赵氏喜剧现象。春节本是按中国农业社会农事特点安排的,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与西方节日狂欢化的倾向不同,中国的节日更注重家族伦理感情的凝聚。
春节晚会是笑的世界,是喜庆和吉祥的象征,它不能容忍沉重的出现,不能容忍无节制的狂欢,更不能容忍现实的矛盾破坏喜庆的和谐氛围,这一节日特点,也就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年复一年将春节晚会办下去,且将其当作强有力宣传工具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世界电视技术已飞速发展,中国中央电视台可在两岸三地,甚至在全世界直播或通过卫星光缆同时主持晚会。当官方将这一民间节日政治仪式化,它也就日渐丧失了其本源的快感和意义。
通过全世界范围内的电视直播,春节加上家庭的政治符号意味便被不断地放大并强化,使公众对此符号下隐藏的潜性原则丧失了应有警惕,从而形成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盲从。这也是赵氏喜剧遭遇一致欢呼的重要文化因素。
然而,一个广场仪式成为泛政治化的放大镜,最终会使民间的狂欢走向了伪民间的无趣。在近年的读者调查中,对春节联欢晚会不满,对赵氏小品不满的呼声日渐升温,甚至不断有官员、学者和普通观众对赵氏小品提出尖锐批评,如前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其博客上指出,赵本山小品《捐助》反映出节目编导者对我国当下教育制度的空前无知。

《捐助》(2010)
而赵本山喜剧在美国遭到非议,则进一步说明赵氏喜剧中存在封建低俗、不适合现代文明的腐烂因子,已在新世纪主流意识形态纵容下,成了「合法的低俗」。这无疑令人悲哀。艺术的个性化,艺术对人的精神境界的熏染,艺术对人思想能力的提升,都因「话语消费性」和「意识形态的规训性」两个原因,被放纵为「恶性癌变」。
因此,赵氏喜剧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解读新世纪文化语境的一把钥匙。激进的启蒙主义退潮,保守主义与商业利益逐渐合流,并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原始积累阶段权力寻租的天然屏障。
然而,面对着转型期原有伦理体系的分崩离析,我们不得不悲哀地看到,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在中国还是一个远没有达到的目标。王朔为代表的痞子小说和赵本山的农民喜剧小品,成为中国诞生的向现代和传统双向呼应的「怪味果」。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文化研究者必须承认,我们时至今日还在依赖启蒙运动以来「科学革命」为我们的自我认识造就的思想模式中展开我们的思考。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讨论什么「后现代」,而是要面对一个8亿农民的半工业社会的现实,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赵树理留影
也由此想到了一位重要农民作家——赵树理。《刘老根》剧本统筹何庆魁曾自豪地说:「我们想做赵树理第二。」但是,当写真实的艺术操守和现实政策发生冲突时,赵树理和赵本山的不同选择不证自明。赵树理无论是写落后的农民,还是新思想农民,其现代性思想诉求,即以此展示真实矛盾,追求现代化的人的自由、民主精神的目的都十分强烈。
他建立了一种清新、朴实、自然、俭省的民间语言,他的特征是农民的,也具农民气质和可贵品格,这种品格自始至终表现为艺术「诚实」态度。他的诚实甚至也是农民式的,有一些农民式的天真和固执。
对农民题材和自身的局限性,赵树理并没有刻意掩盖和回避。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赵树理也抱有天生警惕性,这也是赵树理小说在接受史的评价屡经变迁的重要原因。
而赵本山则无论前期「移风易俗」系列小品,还是后期「致富农民感谢党的领导」、「致富农民的爱情闹剧」,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内在缺陷十分明显。他从农民向政治农民和小市民的转变,值得我们深思,他显然对此缺乏足够警惕。

《中奖了》(2013)
追求自我的解放和个人的发展,仍然是中国现在文化的第一要义,也是中国启蒙未竟之事业。然而,面对这个精英主体性死亡的过程,也是犬儒主义的欢乐时代来临的过程,当最后的「英雄」也已成为中产阶级宏大叙事牺牲品,你又能让「徐老蔫」一个农民怎样呢?
赵本山小品,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社会转型期农民复杂心态和一定社会现实,但它更多展示的是一个有天赋的农民艺术家迷失在商业和权力神话中的心路历程。他的成功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农民神话,这到底是赵本山的成功,还是中国式喜剧的伟大胜利?
节选自《风景的诱惑》(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房伟 著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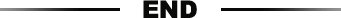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精彩内容
忘掉猴年春晚!来看看他是如何成为「春晚历史第一人」
这样有趣到极点的喜剧科幻片,现在真的没有了
黄宏为什么要在春晚小品里歌颂马俊仁?
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做了一件可能每个影迷都会喜欢的妙物——Le Cinéma帆布包。
这份妙物专门设计给热爱电影的你,原始定价为248元,首发促销价为199元,目前只在虹膜微店预售,此时下单,年后发货。
长按下图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进入购买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