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张千一为这部歌剧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历时6年潜心创作。
虽然这部歌剧的内容灵感起源于一首民歌,但它绝不是民歌的移植改编。
张千一并非把民歌原样搬到歌剧中,也没有刻意地让民歌多次出现,每次出现都是恰如其分地融入戏剧情境里,而不是孤立存在。

民歌《兰花花》在全剧中共出现了两次,其他时候则被打碎作为核心动机材料,在歌剧里发挥独特作用。
两次《兰花花》都是以合唱的形式出现。一幕中,兰花花第一次勇敢面对兰家河的乡亲们,说:“别打他,要打就连我一起打吧”,这时,众乡亲望着兰花花,唱出“一十三省的女娃子,唯有兰花花好”,既从侧面交代了人物性格,也具有很美的意境;第二次出现是在尾声合唱,兰花花跳黄河自尽之后,蓝家河全体村民歌唱出一曲宏大的赞美诗。
旋律在保持原民歌旋法的基础上
“换音不换魂”
,给人十分熟悉但又耳目一新的感觉。两次升调也推动了全剧情感的升华,令人回味无穷。
张千一对这部歌剧的定位是:“运用歌剧的
交响性
与
史诗性
,力求将兰花花这一典型的中国题材,打造成具有国际化艺术水准的中国歌剧。”
“兰花花”是典型的中国本土题材,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甚至更具有传统的
乡土气息
和
民族意蕴
。在旋律的写作上,张千一吸收了陕北民间音乐元素,
运用了“苦音”和“哭音”等陕北特色音程
,让观众感受到浓郁的陕北风味。
而在乐队中,张千一加入了板胡、管子、大笛、铙钹等民族乐器,形成了丰富的音响场
,处处体现着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和浓墨重彩的中国风貌。

在面临中国语言与音乐之间如何协调的困难的问题时,作曲家在歌剧《兰花花》的创作中
特别注意语言与音乐、节拍与律动的关系等凸显中国原创歌剧的母体元素。
比如周老爷二幕五唱段“有救,有救,有救,只要你听我的”,先是五度,后是八度,然后再接近于说白,语气越来越重,调门越来越高,把周老爷胸有成竹的这种自信状态表现出来。再比如语气式的宣叙风格以及对白的适度间插,对人物心理描绘和性格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语音方面,采用强化儿化音的方法,强调周老爷作为一族之长“温和、亲切”的一面。这些创作手段让旋律具有了中国意蕴,让宣叙调也好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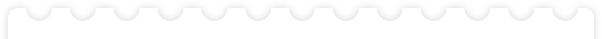
“《兰花花》以浓郁中国特色的民间故事、典型的意大利歌剧艺术表现手法、新颖别致的艺术效果,展现了中国歌剧在近百年历史探索中的新思考,展现了戏剧舞台艺术在当下发展语境中中西融合的新样态。”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王安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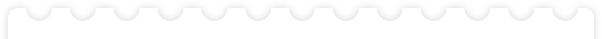
“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歌剧《兰花花》将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作曲家 朱嘉禾
歌剧《兰花花》不但具有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准,还兼具了
旋律性、可听性
,作曲家在剧中创作了大量唯美浪漫的旋律,让普通观众也享受其中。

例如被作曲家称之为
“核心唱段式咏叹调”
的兰花花与骆驼子的二重唱“圆圆的月亮挂在天上”,是兰花花与骆驼子这对儿恋人重要的爱情表达唱段。其旋律优美动听,情感质朴单纯。尤其唱中“天上”“心上”同音落音的一高一低,支声复调与心境表达的一分一合,以及“苦(花)音”飘然而至的清新效果,无不从听觉上展示出这个唱段的唯美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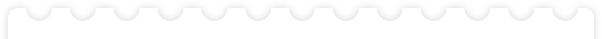
“作为一部中国歌剧,《兰花花》是少有的具有很强旋律性的作品,这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音乐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作曲家们的创作开始往回走,主要表现就是抛开先锋派的不协和转而注重旋律性——或可称为一种新浪漫主义,这股潮流一直延续至今。由此观之,国家大剧院的这部歌剧是紧随时代精神的,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
——《三联爱乐》编辑 李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