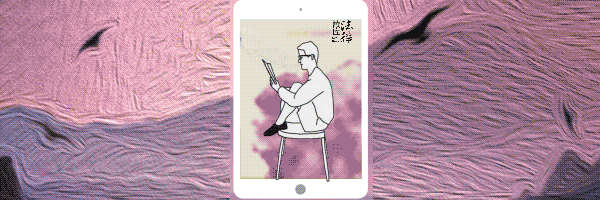
作者: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庞良程
中央领导批示关注的王某等人骗取贷款、违法发放贷款案,是建国以来数额特别巨大的金融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达72.71亿元。
本案因为财政部对交通银行某分行信贷资产质量进行例行检查、交通银行总行内部审计后移送处理函给公安部而案发。
王某经与交通银行某分行原行长刘某明合谋,规避交通银行贷款审查和监控规定,指使张某文等人以购买空壳公司或者借用他人公司作为贷款主体和保证单位,编造虚假的贷款理由等,先后以40多家公司名义向交通银行某分行及下属支行申请贷款;
将骗取的大部分贷款利用复杂的转账流程,通过地下钱庄非法转账和境外公司实施资本运作等进行掩饰隐瞒后,分别以王某实际控制的中国轨道、正顺集团、新源置业公司的名义,收购天源公司、金东源公司和三诚公司全部股权,控制开发经营广州动漫星城、名城广场、珠江新城地块等地产项目,同时经营运作广东置地公司到英国上市。
此案涉及骗取贷款、违法发放贷款、贷款诈骗等多个复杂罪名,省市相关部门七次召开案件分析会,我参与指导越秀区院打好时间争夺战、证据攻坚战、庭审技术战和国有资金保卫战,一审判决生效后,通过拍卖、变卖上述公司被查封的股权,退还交通银行被骗贷款及法定利息,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化解国家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2011年12月6日,交通银行总行专程在广州召开答谢广东省政法系统总结座谈会,此案办理受到上级领导机关肯定和被害单位致谢。案件从侦查到审判环节也存在一些诉讼争点,值得总结研究。
(一)如何评价王某的行为责任
庭审中,王某及其辩护人认为证明王某授意张某文等人购买空壳公司或者借用他人公司骗取贷款的证据不足,只是对公司行为负责,没有直接参与行为。
检察机关认为,在案相关证人证言证实天源公司、金东源公司、三诚公司都是王某负责经营管理,三个公司的股权取得都是王某向银行贷款再从其他企业转账所得购买;张某文指证王某授意其购买空壳公司向交通银行借款,并对每次向银行借款的金额及涉案借款如何走账、调配、最终流向等作出指示。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骗取的大部分贷款都是经过关联公司的账户多次转账等方式掩饰后交由王某使用或者购买三家公司的股权。文检鉴定书证实王某具体参与部分骗取贷款行为。王某作为天源公司、金东源公司、三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此庞大款项的融资情况,其只负领导责任的辩解有违常理常情。
(二)骗取贷款罪的数额认定
骗取贷款罪是2006年6月29日施行的刑法修正(六)新增加的罪名,而涉案骗取贷款行为发生在2005年11月至2007年12月之间,交通银行报案和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起诉意见书所认定的骗贷事实也是根据上述时间段计算,辩护人认为不应当将2006年6月29日之前发生的骗贷行为作为犯罪事实认定。另外,应当扣除“以新还旧”的贷款数额。
检察机关认同辩护人的部分意见,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对行为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义,也体现国民的法感情和对自由安全的可预测性,故应当对2005年11月至2007年12月间发生在2006年6月29日之前的骗取贷款事实仅作为民事法律事实评价,不作为骗取贷款的犯罪事实认定。值得注意的是,涉案犯罪数额的认定还存在以新还旧情况,对于还后再贷的行为,因是以新贷款还旧贷款,借款人虽然未实际取得贷款,但该贷款是通过重新签订借贷合同的方式形成的,行为人使用虚假资料再骗取的贷款,是另一个骗取贷款行为,对还后再贷的数额应作为涉案数额认定。法院判决也支持上述观点。当然通过持续“借新还旧”方式偿还贷款在现实中广泛存在,不能简单认定骗取贷款罪的“其他严重情节”。
(三)骗取贷款单位犯罪的认定
庭审中,辩护律师提出,本案融资主观意图为了投资项目的发展,谋取单位利益,应当认定单位犯罪。
检察机关认为,本案涉及天源公司、金东源公司、三诚公司等多家公司,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公司有集体意志决定进行骗取贷款行为,也不是以天源公司、金东源公司、三诚公司的名义实施骗取贷款行为,是王某、张某文为筹集资金以购买的40多家空壳公司或者借用其他公司的名义实施的,利益不归属于名义上的贷款主体,涉案公司都是被王某、张某文等人用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本案不属于单位集体意志决定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并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不符合单位犯罪的主要特征,不应当以单位犯罪论处。
(四)违法发放贷款罪的认定
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在庭审中存在三个诉讼争点:
一是交通银行某分行授信管理部原高级经理张某辩称不知道也不负责审查王某、张某文递交申贷材料的真实性。检察机关认为,黄某某、刘某喜等证人证言证实张某有参与王某、刘某明借用他们公司名义向交通银行借款的经过;同案人交通银行某分行番禺支行原行长麦某某在庭审中明确指证张某是分行授信管理部高级经理,负责初审贷款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后才能将贷款申请安排贷审会审查;交通银行授信档案材料中也有张某对涉案贷款签发同意的签名;张某也供认明知王某、张某文的贷款违规,但仍按照交通银行某分行原行长刘某明授意对申请签发同意,故张某的辩解不能成立。
二是辩护人认为案发后已用三个经营项目向银行抵押贷款来还款,银行不会因为本案遭受任何损失,故不构成“造成重大损失”。经查,本案于2008年7月24日立案侦查后,王某于2008年10月8日向交通银行某分行黄埔支行提供抵押再借款人民币45亿余元,偿还了本案涉及的贷款余额。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在事实表达部分,只认定“至2008年9月,仍有共计人民币46亿多元贷款未能归还,造成交通银行某分行巨额资金的损失”,未客观认定上述情节,检察机关起诉书认定了上述情节。问题的关键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文书理由部分,对行为人骗取贷款和违法发放贷款的法律评价均进行了模糊表达,只认定骗取贷款和违法发放贷款行为,但对“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和“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等重要事项均没有进行明确评价,即便出于诉讼策略、不怀恶意,也体现出重定罪、轻量刑和重意见、轻说理的司法短视和保守倾向,难免给辩方带来辩护知情权和防御权的困扰;司法裁判作为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在行使定罪量刑裁量权时,无法回避辩方提出的意见,但在判决书中出现了说理和判项的矛盾,如说理时认为本案的两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重大损失”,该“损失”应是指立案时造成没有归还或者没有全部归还的贷款数额巨大,案发后,被害单位采取措施保证金融资产不致流失,避免扩大损失,不能认为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没有造成损失,不影响对行为人定罪。另外,王某、张某文用虚假资料骗取被害单位贷款数额巨大,使银行巨额资金陷入巨大风险,符合骗取贷款罪“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判项中认为王某、张某文骗取贷款“情节特别严重”,没有认定“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认为张某、麦某某违法发放贷款“数额特别巨大”,也没有认定“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我认为,法院判决不认定“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说理部分值得商榷,参照渎职犯罪相关司法解释,造成损失一般是指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立案后挽回的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所造成的损失,不宜简单以立案时未归还的贷款数额作为损失认定。2009年6月24日最高法刑二庭《关于针对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立案追诉标准的意见》和2009年6月30日最高检公诉厅《关于对骗取贷款等犯罪立案追诉标准有关问题的回复意见》的基本精神一致,认为根据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实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制,商业银行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称为不良贷款,不宜一概以金融机构出具“形成不良贷款”的结论来认定“造成重大损失”,如达到“次级”的贷款,虽然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经营收入已无法保证足额偿还本息,但若有他人为之提供担保的,银行仍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实现债权。因此,不良贷款尽管“不良”,但不一定形成既成的损失,不宜把形成不良贷款数额等同于“重大经济损失数额”。本案中王某通过抵押贷款偿还贷款余额,不能像判决书以立案时未归还贷款推定为贷款损失。
三是辩护人认为张某负责的分行部门收到支行交付的资料后,再交给由分行9人组成的贷款审查委员会实施“一票否决制”决定性审查,整个过程中只起到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麦某某所参与的违法发放贷款都是在分行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指令督促、安排下进行的,并不是麦某某的主动行为,起到辅助作用,处于次要地位,只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院判决采纳了辩护意见,认为交通银行贷款审查委员会在审批贷款时实行一票否决,从本案的有关证据及所贷出的资金数额如此庞大的情况分析看,以张某、麦某某的职权是不可能决定的,二人辩解称根据原分行行长刘某明的指令发放贷款是可信的,本案放贷应该是根据刘某明的指使和授意进行,而非张某、麦某某的主动行为,据此可以认定二人在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属于从犯。经查,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和检察机关以违法发放贷款罪批准逮捕刘某明前,刘某明已潜逃海外至今未归,国际刑警组织已发布红色通缉令引渡在逃犯,早在2015年4月22日中纪委网站公布的百名外逃人员名单中,刘某明以涉案金额最高的银行人员赫然在列。我认为,本案不宜认定二人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从犯,在同案人刘某明未归案的情况下,即便推定是刘某明指使和授意,但根据贷款审批流程,麦某某作为支行行长,负责受理、审核、递送申贷资料给负责授信管理工作的张某审批,张某提出合规性审查意见后审批报送给贷审会,二人具体参与实施发放贷款的重要环节,也是贷审会决策的前置条件和审查关口,不宜以贷审会享有一票否决权减轻二人的罪责,因为贷审会的工作质量与二人职责效能密切相关,二人在贷款审批发放中不属于次要、辅助地位,不应当认定从犯。实际上关于辩护人提出张某文是从犯的意见时,法院判决书分析认为张某文具体负责操作本案融资工作,在整个贷款过程中,向银行提供申请贷款虚假材料及购买空壳公司等一系列行为,都是张某文受王某指挥进行的,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不宜认定从犯,其分析思路和理由与此相同。判决书不宜对类似问题,以不同的认定理由作出相互矛盾的处理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