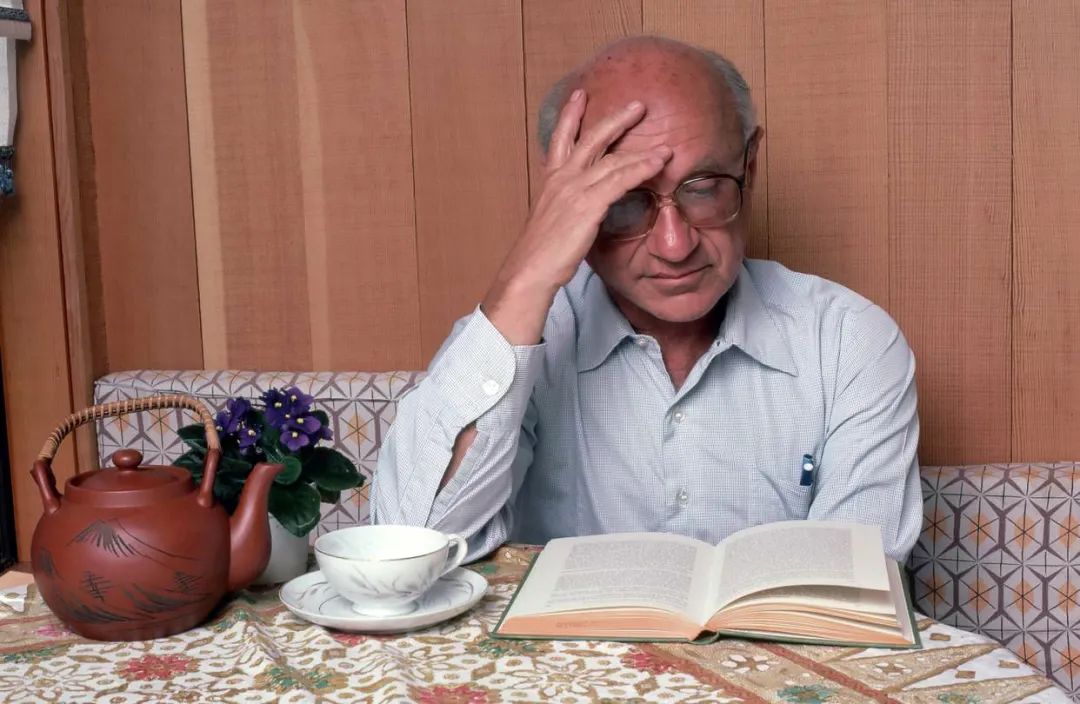
张五常前言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在会见赵紫阳的同一天,佛利民在北京科学会堂作了一次关于市场运作的演讲。赴会者二百余人,座无虚设,高朋满座(站着听的多的是)。因为预料慕名而来的听众必定多,主办机构就只能有选择地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以王羲之所说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形容那次盛会,是很适当的。
佛利民讲话时没有讲稿在手,是很随便的演讲了。实时翻译的人是香港的周安桥——周兄见义勇为,从老远专程而来拔刀相助,我与佛利民要在此表示谢忱。演讲后,听众踊跃发问,但因时间所限,我只好代为「终止」了。
五十年代,佛利民是最出色的价格理论家,对市场运作的认识无出其右。但由五十年代末期至今天,他的学术兴趣却放在货币理论那方面。不少经济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他这份兴趣的转移,是经济学上的一大损失。价格理论比货币理论更重要,而像佛利民那样百年仅见的天才,怎可以让他放弃价格理论的研究呢?当然,货币理论是关乎通货膨胀及失业等众所关心的问题,对佛氏声望的普及是大有帮助的。声望的普及,增加了他对执政者的影响力。这是世界之幸。但从学术那方面看,佛氏不继续在价格理论上多下功夫,经济学整体的解释能力就得不偿失了。
也许这是我个人之见吧。但在这里我特别提及这些,是因为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产权理论的崛起使价格理论发扬光大。到今天,我们对产权及市场的认识,与五十年代时不可同日而言。在这个重要的发展中,佛利民忙于货币量的辩论,对产权理论是很少触及的。这不是说他对产权毫无认识:产权理论中最重要的是高斯定律;当年(一九六○)在戴维德家里,一天饭后,多个高手反对高斯而将这定律迫出来的一剎那,佛利民是一个重要的功臣!高斯在十多年后对我说,如果没有当时在场的佛利民——从反对到同意而至协助——他自己不会把问题想得那样清楚、透彻。
我旧事重提,是因为在这次北京讲话中,佛氏所指出的「自由、私有、市场」的繁荣三大因素,在比较新的产权理论的概念里,只不过是一个合并的因素而已;那就是:私有产权。自由的定义不简单,而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有不同的自由。这一点,我在其它文章内是解释过的。在私有产权下的自由,是指在个人权利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因为有了保障而不会受到其它的「自由」侵犯或侵占。至于「市场」,则高斯定律解释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个人在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
在六、七十年代时我曾在几篇文章内详细解释过,私有产权一定要有私人的使用权(包括决定使用的权利)、自由的转让权,与私人收入的享受权。这三项权利若缺少一样,私有产权的定义就不容易成立了。左管右管的政策,削弱了私产的收入享受权与转让权,真正的私产制就谈不上了。可以说,只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的界定与保障,「自由」与「市场」是不用再提的。
佛利民在北京的讲话,显然是用上比较旧的「私有」概念。话虽如此,我仍认为佛氏将「私有」分为「自由、私有、市场」是比较通俗而令人容易明白的。他和我的观点不同,只不过是表面而并非实质上的事。他的不够严谨的「私有」概念,一分为「三」的申述,为了要使一般听众明白,是高明之着。
佛氏的北京演讲有录音,本文是由朱茜斌根据录音带整理出初稿,经王深泉修改,最后由我修订的。
——
张五常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
繁荣三大要素
米尔顿·弗里德曼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 北京
最近在上海所作的报告里,我承接了一九八○年到中国访问时所谈过的有关市场运作的问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讨论。我的报告特别强调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容许下,广泛地使用自由私有的市场。
「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开放的市场。单单使用「市场」并不足够:任何国家,不论富庶或贫穷的,都在使用它。只有「私有市场」也是不足够的,例如:印度虽然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私有市场,但人民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同样地,一般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也使用私有市场,但它们非常落后贫穷。
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自由竞争的私有市场。在历史上,我找不到任何例子、任何国家或任何地方,在没有「自由竞争的私有市场」的环境下,能够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市场而言,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混合着政府与私人的活动,而那些在经济上有卓越成就的国家,竞争性的私有活动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这里,让我讨论一下对中国目前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通货膨胀和双轨价格制度。无论从历史或个人的经验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胀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控制通胀似乎是当务之急。但我们必须弄清楚,怎样才能控制通胀。很多国家以为控制通胀就要控制某些价格。这个方法用了一次又一次,但从未成功过。一千六百年前的罗马帝国,以及近代的巴西、阿根廷等,都先后采用过这方法,但都难逃失败的厄运。通过控制某些价格来控制通胀就等于夹着气球的某一边,这只能迫使空气走向另一边罢了。同样地,压低某些商品的价格只能迫使其它商品的价格承受更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分辨整体的价格与相对的个别价格。
在任何地方,通货膨胀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这通常是由过多货币流通量所造成的。对中国的情况来说,通胀是因为钞票过多。由于中国的经济不断地发展,银行存款与支票使用已逐渐通行。因此,在中国「货币」这个概念将来会有所改变;但在目前,货币一般还是指钞票。然而,指出通胀是印制钞票过多的后果,仅仅是这个问题答案的序幕。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钞票发行?而又应该怎样控制钞票的流通量?据我所了解,目前中国钞票过多,是由下述两个因素造成的:用印制钞票去填补大部分的赤字;人民银行和属下分行贷放过多的款项给国营企业。为了控制通胀,首先要限制用印制钞票来填补赤字,以及限制给国营企业的贷款。问题不在于过多的投资而在于过多的货币。
如果中国的利率能容许在市场里自由浮动,使之高于通胀率,这对解决问题会有莫大的帮助。据我所知,现在付给储蓄者的利率是远低于通胀率的,那就是实际上人民要倒贴才能享有存款的权利。这当然会阻碍储蓄的意向。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够在低于通胀的利率下借钱,这就会鼓励浪费投资的资源。
放宽价格本身并不会引起通胀的问题。由于放宽而导致个别价格的上升并非通胀;正相反,它却能帮助控制通胀。我们必须分辨统计学家所制造的数字和真正的事实。如果某些价格是人为的偏低,而有关的物品我们又不能买得到的话,这不是真正的便宜;如果某些价格是过于偏低,但要排上五个小时「队」才能买得到的话,这也不是真正的便宜。另一方面,如果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格而我又能买得到的,这才算是真价——即使价格比统计出来的报告为高。
我有两个外国的例子,对今天的中国特别有启发性。其一,是日本在七十年代早期的经验。通胀率和货币增长率同是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三年,政府决定大幅度削减货币增长率,但并没有控制物价和工资。不出几年,通胀率不但大大下降,也为日本过去十五年的超卓发展打好了基础。
另一个反面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一九四七年,德国由英、美、法盟军统治;物价和工资因管制而偏低。结果是店铺的货品被人抢购一空,求过于供,这样,发行过多的钞票就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钞票变得不值钱,烟酒便成了钞票的代替品。一九四八年的一个星期日,当放宽价格和工资的宣布从收音机传出后,这消息果然生效,为德国带来奇迹般的转变。商店再度照常营业,人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通胀也因货币管制而销声匿了。
这些例子同时带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双轨价格。众所周知,在中国,同一商品往往会有不同的价格。在我来看,这个问题与外汇有莫大的关系。双轨价格对贪污舞弊和低效率,似乎是一份公开的「邀请」(或诱惑)。我这种想法是始于三十多年前我当印度财政部长的顾问。在那段日子里,我深深体会到:给意见往往比接受意见来得容易。当时,我向印度的财政部长提议放宽外汇管制并容许汇率在公开的外汇市场浮动。但很可惜,他们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实施外汇管制和多重汇率制度,是导致印度普遍的贪污,和民生四十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因素。
在任何一个有外汇管制的国家,无论是印度、阿根廷,还是巴西、墨西哥,最快捷的致富办法,莫过于从政府那里拿到外汇许可证。这是很有效的途径——它使财富集中于一小撮人身上而令大多数人捱穷。外汇管制往往导致灰市、黑市、黄市的涌现。除此之外,外汇管制更会剥削了国家对外的竞争力。有些商品的汇率过高而有些商品的汇率过低。这对什么应该生产,什么不应该生产,什么应该进口,什么不应该进口都造成了错误的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