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以下的谈话看来,我以为苏格拉底是劝勉那些和他交游的人在饱食、性欲、睡眠、耐冷、耐热和劳动等方面都要实践自制的。
当他看到有一个和他交游的人在这些方面没有节制的时候,他就对他说道:“请告诉我,阿里斯提普斯,如果要求你负责教育我们中间的两个青年人,使一个成为有资格统治人的人,另一个则成为决不愿意统治人的人,你将会怎样教育每一个人呢?就让我们从最基本的食物问题谈起,好不好?”
“的确”,阿里斯提普斯回答道,“我认为食物是个很基本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进食物他就活不下去”。
“那末,他们两人就都会在一定时间有进食的要求了?”
“是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阿里斯提普斯回答说。
“那末,这两个人中哪一个人我们应该训练他,使他把处理紧急事务看得比进食更要紧呢?”
“毫无疑问,是那个被训练来统治人的人”,阿里斯提普斯回答说,“否则的话,国家大事就会因他的玩忽而受到影响”。“当两个人都口渴的时候”,苏格拉底继续说道,“我们岂不是也要训练这同一个人要有耐渴的能力吗?”
“当然”,阿里斯提普斯回答道。
“这两个人中哪一个我们应当使他有限制睡眠的能力,使得他能够晚睡早起,而且如果需要的话,就不睡眠呢?”
“毫无疑问”,阿里斯提普斯回答道,“也是同一个人”。“这两个人中,我们应该要求哪一个人有控制性欲的能力,使他不致因性欲的影响而妨碍执行必要的任务呢?”
“也是同一个人”,阿里斯提普斯回答。
“这两个人当中,我们应该训练哪一个人,使他不致躲避劳动,而是很愉快地从事劳动呢?”
“这也应该是那个受训练准备统治人的人”,阿里斯提普斯回答。
“这两个人当中,哪一个需要有制胜敌人的知识呢?”
“毫无疑问,当然也是那个受训练治理人的人非常需要这种知识,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其他一切资格都将毫无用处”,阿里斯提普斯回答。
“那末,在你看来,一个受了这样训练的人,不会像其他动物那样容易出其不意地被敌人所制胜了?我们知道有些这样的动物,由于贪婪而被捕;另一些,尽管很机灵,也由于贪图吞饵而受诱;还有一些,由于滥饮而陷入罗网。”
“这也是无可争辩的”,阿里斯提普斯回答。
“岂不是还有一些,就如鹌鹑和鹧鸪,由于它们的性欲,当它们听到雌鸟叫唤的声音时,因为贪图享乐就放松警惕,终至于落入陷阱之中吗?”
阿里斯提普斯对这也表示了同意。
“那末,你想,一个人像那些最无知的禽兽那样,也陷于同样的情况,岂不是很可耻吗?就如一个奸夫虽然明知一个犯奸淫的人有受法律所要施加的刑罚和中人埋伏、被捉、受痛打的危险,却仍然进入妇女的闺房中去;尽管有如此多的痛苦和耻辱在等待着登徒子之流,但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方法可以使他避免肉欲的危险,而他竟甘心自投罗网,你想这岂不是有如恶鬼附身吗?”
“我想是这样”,阿里斯提普斯回答道。
“考虑到人生当中极大部分重大的实践、战争、农业和许多的其他事情都是在露天中进行的,你想,竟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受过忍耐寒冷和炎热的训练,岂不是重大的疏忽吗?”阿里斯提普斯对这也表示了同意。
“你想我们岂不是应当把那准备统治人的人训练得能够轻而易举地忍受这些不方便吗?”
“当然应该如此”,阿里斯提普斯回答。
“如果我们把那些能够忍受这些事的人列为‘适于统治’的一类,那我们就岂不是应当把那些不能忍受这些事的人列为甚至连要求统治的资格也没有的一类了吗?”
阿里斯提普斯对这也表示了同意。
“既然你知道这两类人各属于哪一类,那末,你是不是考虑过应当把自己放在哪一类里呢?”
“我的确已经考虑过了”,阿里斯提普斯说:“我从来也不想把自己放在那些想要统治人的人一类;因为在我看来,为自己准备必需品已经是件很大的难事,如果不以此为满足,还想肩负起为全国人民提供一切必需品的重担,那真是太荒唐了。自己所想要得到的许多东西尚且弄不到手,竟还要把自己列于一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从而使自己如果不能为全国人民提供必需品就要受到谴责,岂不是愚不可及吗?因为人民认为他们有权处理他们的领袖,就像我认为有权处理我的奴仆一样,我要求我的仆人给我提供丰盛的必需品,但却不许他们染指;人民也认为国家的领导人应该为他们尽量提供各种享受,却不愿领导人自己有任何享受,因此,任何愿意为自己惹许多麻烦而同时又为别人找许多麻烦的人,我就这样训练他们,把他们列于‘适于统治’的一类;但我把自己列于那些愿尽量享受安逸和幸福的一类人之中”。
于是苏格拉底问道:“让我们考虑一下是统治人的人生活得更幸福还是被统治的人生活得更幸福,好吗?”
“当然可以”,阿里斯提普斯回答道。
“首先从我们所知道的民族说起。在亚洲的统治者是波斯人;叙利亚人,弗吕吉亚人和吕底亚人,都是被统治者。在欧洲的统治者是斯库泰人,被统治者是马俄太人;在非洲,统治者是迦太基人,被统治者是利比亚人。你想这些人中哪些人生活得更幸福呢?或者就拿以你自己为一分子的希腊人来说,你想是统治集团的人生活更幸福呢,还是被统治的人生活得更幸福呢?”
“不过,我并不是一个拥护奴隶制的人”,阿里斯提督斯回答道,“但我以为有一条我愿意走在其中的中庸大道,这条道路既不通过统治,也不通过奴役,而是通过自由,这乃是一条通向幸福的光明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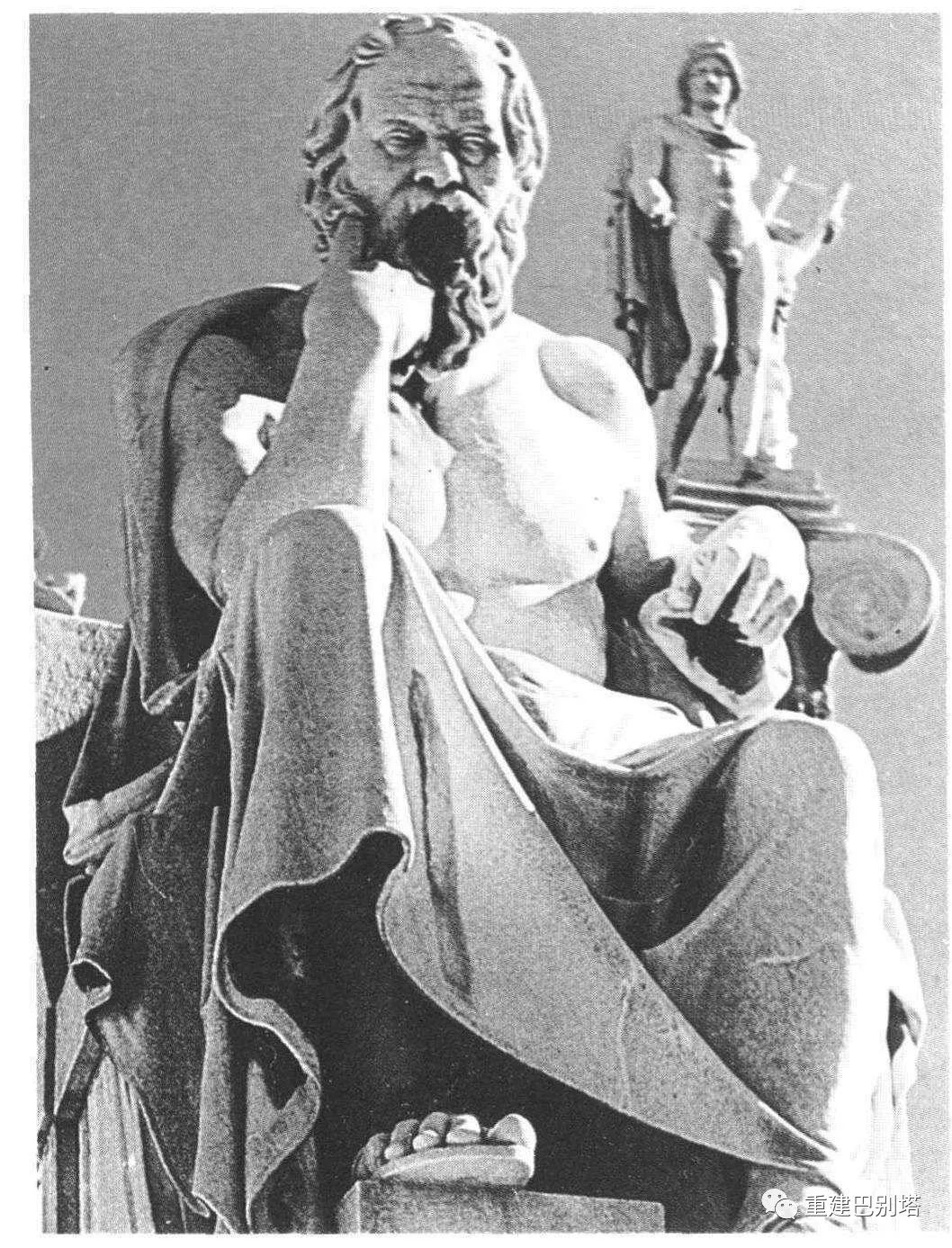
“不过”,苏格拉底说道,“如果你所说的既不通过统治也不通过奴役的道路,也是不通过人间的道路的话,那末,你所说的也许就值得考虑了。但是,你既然是生活在人间,而你竟认为统治人和被统治都不适当,而且还不甘心尊敬掌权的人,我想你一定会看到,强有力的人是有办法把弱者当着奴隶来对待,叫他们无论在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中都自叹命苦的。难道你能够不知道,有些人把别人所栽种和培植起来的庄稼和树木砍伐下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扰害那些不肯向他们屈服的弱者,直到他们为了避免和强者的战争而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奴役?就是在私人生活中,难道你也没有看到,勇而强者总是奴役那些怯而弱者并享受他们劳动的果实吗?”
“但是,对我来说”,阿里斯提普斯回答道,“为了不遭受这样的待遇,我并不打算把自己关闭起来做一个国家的公民,而是要到处周游作客”。
“现在你所说的倒的确是一个绝妙的计策”,苏格拉底说道,“因为自从西尼斯、斯凯伦和帕拉克鲁斯推斯被杀以来,是没有人会加害于旅客的!但是各国的执政者,现在都颁布了保护他们自己不受损害的律法,除了那些必须听他们呼唤的人以外,他们还结交了一些朋友,环绕他们的城市建筑堡垒,配备武器防止敌人袭击,除了这一切以外,他们还在外国寻求同盟者;但是,尽管采取了这些防御措施,他们还是遭到了损害;而你,既没有这许多有利条件,花费许多时间奔走在很多人遇害的公路上;当你进入一个城市的时候,你的力量总是没有那个城市的居民那么强大,很容易成为歹徒们注意而加以袭击的对象,难道你会认为由于自己是个客旅,就可以避免受害了吗?有什么事使你这样自信呢?难道是这些城市已经颁布了保护来往客旅的法令吗?还是你以为没有一个奴隶主会把你当作是一个值得一顾的奴隶?因为谁愿意把一个不爱劳动而只是一味贪图享受最优厚待遇的人留在家中呢?”
“但是,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奴隶主是怎样对待这类奴隶的呢!难道他们不是用叫他们挨饿的办法来抑制他们的贪食吗?用使他们无从接近的办法使他们没法下手偷窃吗?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他们岂不是用锁链把他们锁起来吗?岂不是用鞭挞的方法来赶走他们的懒惰吗?你自己是怎样做法来除掉你的家奴的这一类的缺点的呢?”
“我用各种方法惩罚他们”,阿里斯提普斯回答道,“一直到使他们不得不服从我。但是,苏格拉底,你好像认为是幸福的那些受了统治术的训练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和这些被强迫受苦的人有什么不同,既然他们也得甘愿忍受同样的饥饿、寒冷、不眠和其他许多苦楚?因为同一皮肤,不管是自愿或非自愿,反正是受了鞭挞,或者简单地说,同一身体,不管是自愿或非自愿,反正是受了这些苦楚,在我看来,除了自愿受苦的人的愚不可及外,并没有任何区别。”
“怎么,阿里斯提普斯”,苏格拉底问道,“难道你看不出自愿受苦的人和非自愿受苦的人之间有这样的区别,即自愿挨饿的人由于他挨饿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当他愿意的时候他可以随意进食,自愿受渴的人由于他受渴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当他愿意的时候就可以随意进饮,其他自愿受苦的事也是有同样的情形,而被强迫受苦的人就没有随意终止受苦的自由?此外,自愿的人在忍受苦楚的时候,受到美好希望的鼓舞,就如打猎的人能欢欣愉快地忍受劳累,因为他有猎获野兽的希望。的确,这类劳苦的报酬,其价值是很小的;至于那些为了获得宝贵朋友而辛苦的人,或者是为了制胜仇敌而辛苦的人,或者为了有健全的身体和充沛的精神可以把自己的家务治理妥善,能够对朋友有好处,对国家有贡献而辛苦的人,难道你能够不认为,他们是欢欣愉快地为这一切目标而辛劳,或者他们是生活得很幸福,不仅自己心安理得,而且还受到别人的赞扬和羡慕吗?况且,怠惰和眼前的享受,正如健康运动训练员所告诉我们的,既不能使身体有健全的体质,也不能使心灵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知识,但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会使人建立起美好和高尚的业绩来,这是好人们所告诉我们的,赫西阿德斯在某处也说过:
‘恶行充斥各处,俯拾即是:通向它的道路是平坦的,它也离我们很近。但不朽的神明却把劳力流汗安放在德行的宫殿之前:通向它的道路是漫长而险阻的,而且在起头还很崎岖不平;但当你攀登到顶峰的时候,它就会终于容易起来,尽管在起头它是难的。’艾皮哈莫斯在下列诗句里也给我们作了见证:
‘神明要求我们把劳动作为获得一切美好事物的代价’。
在另一处他还说道:
‘无赖们,不要留恋轻松的事情,免得你得到的反而是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