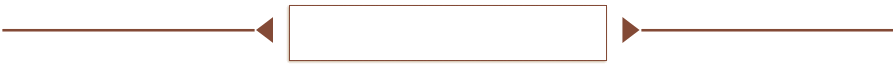
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年。
这不平凡的二十年,同时也不平静。1997年,香港GDP一度占到全国的近四分之一;到了2016年,只占全国GDP的2.77%。1997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七,大约是排名第一的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了2016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二,接近排名第一的美国的三分之二。在这个巨大的变局中,如何适应变化、找准定位,成为香港需要面对的一个巨大课题,甚至是难题。
回望香港回归的二十年,既有骄傲与成就,也有反思与忧虑。如今往前看,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香港和内地之间更深度的大融合。站到高处,放宽心态,突破政治壁垒和信任障碍,实现两岸三地乃至四地间的优势互补,让彼此间产生积极的化学反应,这是符合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乃至造福全球的正确选项。
今天起,陆续为您推送纪念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封面报道
《二十年 爱与忧
——香港回归二十周年
》
★ 香港回归20年:“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变迁
★ 梁锦松:对香港的爱与忧
★ 粤港澳大湾区:探索香港“再融入”
★ 范恒山:开放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在品质
★ 我们都是“湾区人”
★ 马化腾:粤港澳大湾区抓了几副好牌
★ 方舟:面对新变化,香港要调整好自己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闵杰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30日总第810期《中国新闻周刊》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位于香港中环地标性建筑——中银大厦的61层,从窗口望出去,拥有俯瞰维多利亚港的绝佳视野。
从身份上看,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是专门研究香港公共政策的民间机构,缘起于香港回归之前。1985年,为迎接香港回归,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另一个则是在香港成立的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咨委会”)。设立咨委会的目的,是为了香港回归以后的制度安排,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保留了咨委会的部分功能,将研究重点转移至香港内部运作面对的社会和经济等重大问题,以及香港与内地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及合作关系上,继续充当特区政府重要的公共政策智囊。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深度参与了深圳前海、河套地区开发等粤港合作项目的联络和研究。他在香港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谈到,回归20年来,香港最需要总结的问题是,面对新变化准备得不够充分,转型也很辛苦,未来如何做出新的调整来适应新变化,是香港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
你怎么理解中央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方舟:
之所以搞大湾区规划,是因为香港的市场和空间有很大的局限性,希望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共同规划,
帮助香港解决两方面矛盾:
一方面是经济结构太窄,香港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经济结构太窄就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今天粤港合作和二十几年前的粤港合作模式是不一样的,二十几年前是前店后厂,但是今天珠三角深圳已经有很强的高科技产业基础,实际上是希望香港和广东合作能丰富香港的产业结构,改善香港经济的空间。
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希望通过粤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香港作为自由港,还是有很独特的优势,能够和广东的产业基础结合起来,也为国家在更高层面上创建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
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很多人担心大湾区会出现广州、深圳、香港等几个城市的“龙头之争”,你怎么看?
方舟:
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个多中心的模式,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特点。举一个例子,比如国际金融方面,香港的优势毫无争议。如果讲高科技,湾区的龙头肯定是深圳,而广州是传统商贸中心,澳门是全球博彩业的老大,
这几个城市没有必要去争所谓的名分,大家都有自己的行业优势和特点,关键是把优势协调起来。
如果能够协调得好,整个区域竞争力就能有更高的提升。
这种协同效应,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深港边界的河套地区,经过了非常艰苦的谈判,在今年签订了协议,
共建“港深科技创新园”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价值呢?深圳很多科技企业已经比香港更国际化,从国际招揽大量人才,包括华为、腾讯、比亚迪等。对于它们来说,很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把人才招到深圳,各方面的配套条件不够理想,包括税收环境、子女教育,如果是非华人,还存在语言环境问题。如果放在香港,以香港为基地,为这些企业服务,对人才吸引力也更大。
因为这个地区贴在边境上,既可以为内地市场、为珠三角企业服务,又能够利用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特殊优势,利用税制、法律各方面特殊优势,达到一个协同的效果,双方都得利。
中国新闻周刊:
因为“两制”的差别,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香港推进效率比内地低。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否会碰到类似问题?
方舟:
香港很多事情需要经过程序,不光是立法程序,在走到立法会之前,前端就有一大堆程序。
香港所有重大工程都要做三轮可行性研究,每一轮做完后要做公众咨询,每一次公众咨询短则3个月,长则6个月。
什么都还没做呢,就写个研究报告出来,两年多就过去了。立法会上又有可能遇到阻力,发生冗长辩论,让大量的审批积压,拖的时间就更长了。
从广东的角度看,香港的效率一定是太慢。这是需要互相理解的问题,因为香港确实有很多法定程序,有些环节快也快不起来,有些环节比如在立法会是故意被反对派拖着,导致整个政府运作比较慢。这是体制不同导致的差异。而且这几年,内地一些官员和民众对香港有看法,觉得国家对你这么好,你还搞了那么多事情。
其中也有一些误解,因为香港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双方需要多理解。
中国新闻周刊:
香港过去一直充当国家对外开放的“超级联系人”角色,未来这种角色是否会受到影响?
方舟:
过去香港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但从香港本身角度看,还是有很多功能,而且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会有很多新的机会。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香港有几个特别突出的优势:
首先
,在融资方面,国家加大“走出去”步伐,这个过程中会有大量投资,更需要大量融资。香港可以借鉴亚投行的运作模式,利用比较好的主权评级,在市场上发债券融资,然后再去借给第三方。香港在这方面有很多空间。
第二
,香港有很多商业服务,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国家现在“走出去”,需要大量的配套服务,包括签合约的时候,各方面的法律、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香港比较有优势。
第三
,香港在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上也有比较好的经验,一方面可以帮助内地提升水平;另一方面,在国家“走出去”的过程中,提供配套服务,尤其是和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的配套服务。比如香港机场的管理、地铁的管理,可以算是全球最好的。伦敦新建的一条贯穿东西的地铁,也是交给香港地铁公司来管理。在软实力上,香港有很大的优势,如果能和国家在基建方面配合,软实力和硬件配套,会产生很强的互补性。
过去五十多年里,香港的角色一般都是“超级联系人”,但实质一直在变化。
刚开始,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内地还没有开放,香港的角色是做转口贸易。上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就开始做前店后厂,珠三角也变成世界工厂。2000年以后,内地企业转制,需要到海外上市,有大量企业到香港上市,巩固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下一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新的功能又出来,香港的角色也会不断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
从特区政府施政的角度,香港回归20年来最值得总结的经验和问题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