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因其父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便手刃杀父仇人并投案自首。《登幽州台歌》的作者陈子昂(初唐诗人,公元661-702年)时任谏官,他向武后提议处死徐元庆以禁止“血亲复仇”,然后在徐的家乡表彰其孝义,并请朝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以作将来处置“礼法冲突”案件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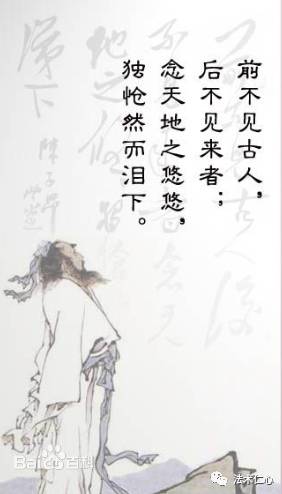
杀人偿命乃法之明令,而为报父仇亦出于孝道,陈子昂提议“诛其人”而“旌其闾”,似乎做到了“法”与“礼”之间泾渭分明,且其有拟定疑难案件“判例法”以指导将来司法实践的意识也难能可贵 。但柳宗元(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公元773-819年)却认为陈子昂的观点错误,专门写下一篇驳论性的奏议《驳复仇议》,批驳初唐陈子昂提出的“既诛且旌”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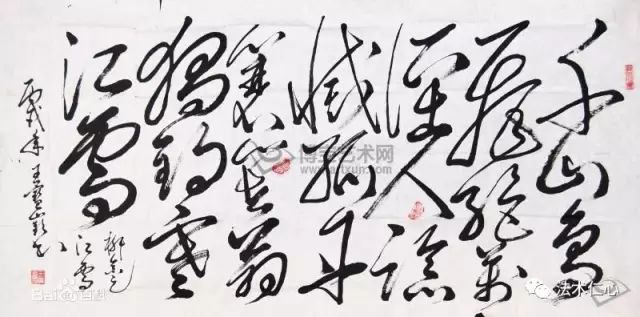
其主要论点有三:
一是礼法应当协调统一。礼与法“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并焉”,据此提出一个“二难推理”:
——如果诛杀应受到表彰的人,则是滥用刑罚;如果表彰应该诛杀的人,则是僭越礼义。
若朝廷真以陈子昂“礼法”分隔的建议昭告天下,就会使意欲尊崇礼教和规避刑罚的人都无所适从。

二是礼法应通过探究事情缘由得于统一。“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最终都不过是为了使礼法归于一致罢了。只有弄清真伪、明察是非,才能确定如何适用法与礼,据此提出一个“证据问题”:
——本案先应查清复仇的缘由再行决断。如果赵师韫是因私怨杀死徐元庆的父亲,而其他官吏又纵容包庇使得徐元庆求告无门,徐元庆被逼才亲手报父仇,这便是“守礼而行义”的行为;那司法官首先应当自责对赵师韫迫害徐父的恶行失察,更不应该将徐元庆处死(柳宗元在此仅是主张不杀,而并未主张赦为无罪)。
如果赵师韫杀死徐元庆之父并非出于私怨,而是恪尽职守、秉公执法,则“法其可仇乎?”如此便是公然抗法、犯上作乱的死罪,更不应该褒奖他。

三是礼法应通过正确解释得于统一。 陈子昂主张“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故应诛杀徐元庆以止“血亲复仇”之风。
柳宗元认为,这是陈子昂“惑于礼”。“礼”所指之报仇,应是处于“冤抑沉痛而号无告”的有冤难申之境地、不得已而为之,而非恣意“抵罪触法”、当处极刑的情形。
陈子昂只知主张“彼杀之,我乃杀之”,以杀戮止复仇,却不论是非曲直,仅是“暴寡胁弱”而已,陈之观点违背经义甚远。《周礼》主张“凡杀人而义者”,就要告诫他们的子弟不要再报仇,如报仇则是死罪;有反过来再去杀人的,全国都将其视为仇人。如果这样,又怎会“亲亲相仇”无可禁止呢?《春秋公羊传》指出父亲不该被杀,儿子可以复仇;父亲有罪当诛,儿子报仇便是复私仇,此种复仇不能消除祸害。
因此,柳宗元认为按照上述原理来理解“礼”,便能决断好“两下相杀”的案件。他还认为,徐元庆为亲报仇、孝也,不惜一死、义也,其应该是一“达理闻道之人”,不会“以王法为敌仇”。如果将其处死,便是滥用刑罚、破坏礼义,明显不应作为“定法”交后世效仿。可见,欧阳修应是极其同情徐元庆。
基于上述原因,柳宗元也向朝廷提出,将他的建议附在法令后面,作为今后裁判的指导,不知这种形式的法律解读是属于“司法解释”还是“学理解释”?

经由陈子昂与柳宗元二人的分析可见,陈子昂类似于一位法实证主义者,对于法的理解仅依赖于“什么已经被制定”和“什么具有社会实效”,认为法律的有效性和道德无关。
法律既然已经规定杀人者偿命,又要防止“血亲复仇”无休无止、祸乱法纪,便应该坚决诛杀徐元庆。至于其为尽孝而复仇的问题,便留待道德层面考量,强调即使是道德所褒奖的行为也不能逾越现行法律的界线。
而柳宗元更像是一位自然法学派的“拥趸”,认为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关联性,制定法必须以内容的正确性作为基础,主张“礼法相统一”。不过,他的推理判断方式明显带有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的影子,除适用法律外,还用《周礼》、《春秋公羊传》等儒家经义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且特别强调作案的动机与缘由。

对于这两位文坛“大腕”在这起“礼法冲突”案件上的交锋,现在读来依然启迪智慧。笔者更倾向于柳宗元的观点——不能机械地将法律与道德相互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而应先查清“复仇”的原委:
徐元庆为父报仇而杀死一个公职人员、应当定罪,至于刑罚轻重或者应否适用死刑,需查证其父死于“私怨”还是死于“公法”,以此判定其主观恶性之大小,并结合自首情节等综合考量。
但是,陈子昂的观点便毫无道理嘛?恐怕未必!至少千年之后,其主张的法律观念依然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否则,就不会有无休止的实证法学与自然法学之争,也不会有现实生活中那么多“情与法”难以厘清的疑难案件。

笔者由《驳复仇议》联想到近两天正在热炒的“辱母杀人案”——“孝子”与“罪犯”的冲突案件。有的主张应该给“孝子”手刃辱母者的权利,有的提出被辱一方同样是巨额非法集资未还的违法者;有的认为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甚至适用无限防卫条款,有的倾向不认定为正当防卫也不无道理......

其实,笔者作为只瞟了一眼判决书而没有看案卷的“普通群众”,自问没有太多发言权。只是强烈感觉到,该案首先是事实证据之争,即凶案发生时是否存在现实的紧迫危险?包括警察当时是否在场?又有何作为?这是评判正当防卫是否成立的关键。而在这一事实前提的确定,至少笔者自认为在没有详细审查证据之前,实难做出准确判断。至于事实确定之后的法律评价,也许仅是一个对照法条“照本宣科”的问题。
当然, “辱母杀人案”与千年以前“为父报仇案”案情不同、法律关系不同、适用的裁判标准也不同,但同样应以查明的事实证据为前提。
即使是沿袭“春秋决狱”思维的柳宗元,也知道要衡平“礼法冲突”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首先应查明徐元庆之父是死于“私怨”还是死于“公法”,再决定刑罚的裁量!单从这一份审慎的态度来看,今人就未必强于古人!

我们身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更应该具备静待全面客观掌握事实真相之后,再依法评判是非对错的定力!特别是职业法律人更应有这份坚守!社会舆论场中无需承担责任后果的“口诛笔伐”,终究不能成为公平正义的基石!
许多众说纷纭的事情,或许本就应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应由司法裁断的纷争,何不多给司法留一些空间和时间!《驳复仇议》中的陈、柳双方观点,即使历经千年不也是难以分出绝对的对错,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往往也只能在具体案件中具体裁量!
(本文图片来自互联网,著作权由原作者享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