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图|视觉中国
2017年,有三个诺贝尔奖是关于人性的——生理学奖(霍尔、罗斯巴殊和扬关于生物节律的研究)、文学奖(石黑一雄直指人性渊深处的浪漫小说)、经济学奖(塞勒将认知与行为科学融入经济学的研究)。诺贝尔奖没有“哲学奖”,但今年的授奖颇有哲学意味。对“人性”的研究和思考,如此广泛地进入了评奖委员会的视野,在这人工智能化的、追求工巧机智的后现代,在这人性沉沦而物化的当下,在这充满悲剧与困惑的“后9·11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在拉斯维加斯夺去数十人生命的非理性、反人性的枪声尚未消散之时,这样的授奖风格,恰如荣格所说的“共时性事件”——既像是巧合,又绝非巧合,隐隐然透露出学风与世风的转机。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授奖,是为表彰其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塞勒1945年出生于新泽西州,曾先后执教于罗彻斯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行为科学与经济学讲座教授。他是行为经济学最为重要的一位创始人。在宣布这一奖项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成员Peter Grdenfors接受采访时说,“他使经济学更为人性化”(he made economics more human),这是对塞勒终生成就的一个有力概括。这位眼神天真灵动、大圆脸、谈笑风生、喜作讽喻之言的白发老教授,这位终生喜爱美酒、美食和高尔夫球,也曾客串过电影的“生活家”,终于实至名归。
在塞勒之前,当代学院派的主流经济学里面是没有“人”的。它假设人的行为遵循一套精密的公理体系,例如,偏好的自反性、传递性、完备性、局部非厌足性、凸性等等一系列的公理,由此推导出性状良好的效用函数,并且在最优约束下计算理性选择——所有人都在极其精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没有学过主流经济学的读者,会怀疑这到底是否描述了真实的人性,但经济学家会认为,进化过程可以淘汰掉那些不理性的个体,大浪淘沙的竞争之后,剩下的人都变成了“天生”的数学家。他们头脑冷静,善于谋划,步步为营,精心算计,用塞勒揶揄的话来说,“他们尽管自私自利,却像甘地一样自制”。然而,恰恰是这种过度简单化的本质主义描述,让“人”的鲜活面目在经济学中逐渐消失——如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所说,“人被抹去,如同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塞勒的大量研究,都指向了现实中的人类决策与完全理性化的、似人非人的经济动物(塞勒讽刺性地称之为Econs)的偏离,而让“活生生的人”在经济学中得以复现。事实上,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这样一种有着七情六欲、既非绝对利他亦非极端理性的真实的普通人。塞勒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人学”的一面,又把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规范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之中。
读塞勒的书和论文是一种享受,数学少,引例多,妙语连珠,智慧丰富而润泽。他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性是如何偏离理性的”。比如,关于心理账户的研究:你要去听票价200元的音乐会,忽然发现丢了200元电话卡,此时多数人还会去买票;但如果你是买票之后又弄丢了门票,同样是200元的损失,多数人却会选择不再买票。学院派的正统经济学无法解释这种差异,塞勒则认为很好解释——你在内心,给自己的各项收支分门别类地设立了不同的账户,丢电话卡的损失只被记录在通信费用的账簿里,不会影响对音乐会的决策;而丢了门票之后,音乐会的账户上明显亏损,自然不会再花冤枉钱。塞勒本人对此也有生活经验,他第一次去瑞士讲课,收入颇丰,塞勒用此收入在瑞士旅行,觉得十分舒心;第二次去英国讲课,收入同样不低,此番他重游瑞士,却发现价格昂贵得难以忍受——这是因为在瑞士工作所得,得自瑞士,失于瑞士,被归入了同一个心理账户,自然觉得舒畅;而从英国挣钱再到瑞士消费,间隔了一段时间后,心理上已不再将之视为同一账户。在股市上,人们会长期持有下跌的股票,期望有朝一日能咸鱼翻身,而非将这些股票卖出再购买利好的股票,也是因为他们给不同的股票设定了不同的心理账户。
塞勒在行为金融学上的建树深广,他提出的诸如禀赋效应、锚定效应、输者赢者效应、即时偏好效应等,都已经成为当代金融学上的经典。塞勒自己也与人合作成立了一家基金公司,运用行为金融学而获利丰厚。
在法经济学方面,塞勒也有着开创性的贡献。目前在法经济学中方兴未艾的“行为法律经济学”,就是塞勒和卡思·桑斯坦(Cass Sunstein)共同创建的。塞勒在法律经济学中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助推”(Nudge)这一概念,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标志,2008年他和桑斯坦合著的《助推》一书,全球畅销、长销,以致BBC在报道塞勒获诺奖时,直接称他为“助推经济学家”(nudging econom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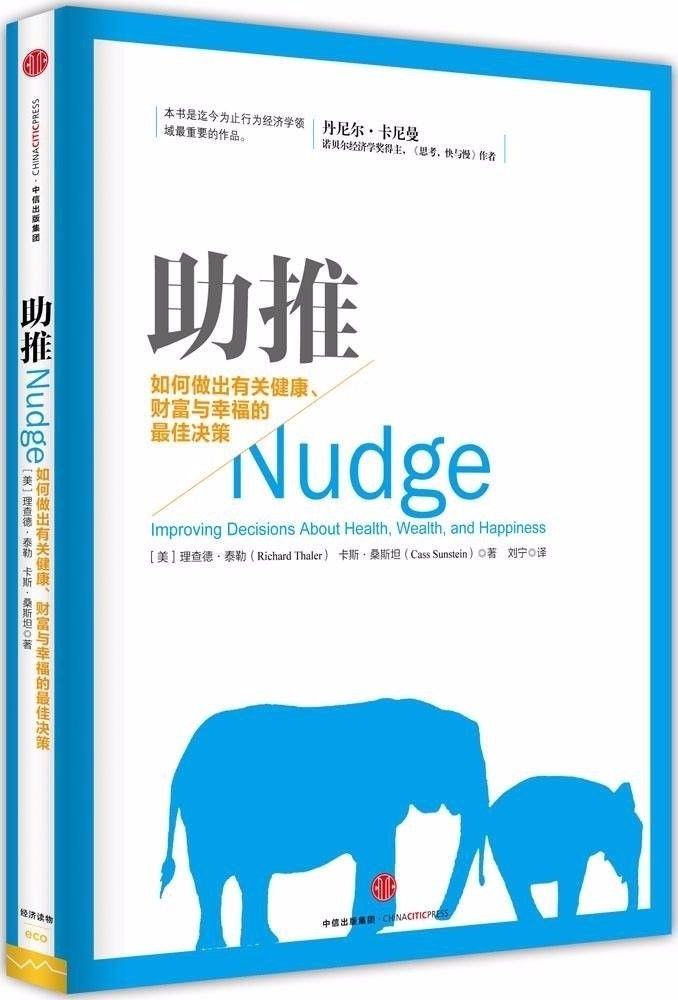
《助推》中文版
所谓“助推”,是指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充分了解人们固有的心理倾向之后,采用尽可能巧妙的规则,使法律和政策工具取得最佳效果——不影响人们的选择自由,却增加社会福祉。比如,把健康食品放在学校食堂中最容易取到的位置,就增加了孩子们的饮食健康;用亮橙色的纸贴违法停车罚单,会让乱停车现象减少;在机场男厕小便池中心蚀刻一个逼真的苍蝇,让男士在“方便”时有个瞄准对象,“溅出”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五分之四;公共场所如果有一串绿色的引导脚印通向垃圾桶,就会减少46%的乱扔垃圾行为……如是巧妙的制度设计,不同于采用严肃刻板的法令去“强推”(push),而是洞悉人性之后“轻轻一推”,如庖丁解牛,切中肯綮,又如太极推手之“四两拨千斤”,顺势而为,借力打力,用力极小而功效甚大。
塞勒将“助推”称之为“温和专制主义”或者“自由家长主义”,它尊重了人们的选择自由——没有改变人们的选择目录,也没有强行为自由选择设置障碍;但它却让法律和政策的“阻力”小了很多。比如,如果把养老金缴纳的方式从“默认不缴纳,申报之后方可缴纳”改为“默认缴纳,自由退出”,并没有增加政策的强迫性,却会让更多的人缴纳养老金。目前,英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助推”机构,而塞勒本人也担任过奥巴马的重要智囊,全球已经有51个国家采纳了助推方法来指导公共政策制订。
助推的理论基础,仍然是“非理性的人性”,由于理性有限,人的大多数行为实在是不经意而为之,绝非深思熟虑的结果。比如不断买买买、随手扔垃圾、匆忙下判断等等。即使深思熟虑制订了详细计划,人的意志力和执行力也往往捉襟见肘,例如人们很容易沉溺于富含盐糖脂的食品,或者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此时,需要一系列明智的公共政策,来指引人们从惰性的泥潭中脱身而出。塞勒本人说,助推就像是给人的头脑里装上一个GPS导航,帮助你规划最优路线。你随时可以关掉这个导航,也可以不按照它的指引来走。但有了这个导航,默认路线变得更合理,长期来看,会大大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然而,很显然,这种“自由家长主义”的取向,这种对“有为政府”的期待,与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然将社会调整至最优状态的想法大相径庭。非主流的经济学派,例如奥地利学派,也未必能欣赏这样的论调,在这些人看来,政策的功用有限,而政府总是值得警惕的对象。然而如上文所述,“助推”并非是对社会和市场的整体设计,它更接近一种边际上的制度改进和创新,在这个层面上,塞勒不具有哈耶克所批评的“致命的自负”。事实上,假如我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制度是由演化而来,也就承认了社会不是一成不变之局,人类的理性设计必然会在规则创新中起作用,即所谓的“有意识演化”(volitional evolution)。由此观之,哈耶克的著作本身就是有意识演化的一个尝试。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也表示,要达到现代文明的扩展秩序,人们必须调整自己,斩断从原始部落带来的偏狭习气,从小群体的裙带关系,转而遵循通用的一般性规则。这不也是一种对自身的克制和改变吗?
塞勒所做的海量研究,揭示出人性中包含着的广泛的非理性,并给出了解决之道。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徒,需要借此反思自己的理论预设,至少需要承认人类的“动物精神”,而那些“助推”的信奉者也切莫忘记,芸芸众生固然可能常犯错误,政策制订者也绝不是完美的决策者,否则,现代文明的发展也就不至于经历如此之多的曲折与磨难。塞勒对于非理性的强调,也并非要替代理性分析的框架。事实上,理性和非理性同时存在于人心之中。理性如同骨架,非理性如同血肉,两者相融互补,相依相承,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性。之所以有“助推”策略,之所以人们会读塞勒和其他行为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的书,恰恰因为人类有着“高阶理性”,也就是说,人类能反思自己的非理性,并将这些涌动着的、千奇百怪的非理性纳入一个合理的范围。恰如汪丁丁教授在塞勒得奖时所预测的,或许,风水轮流转,行为经济学获奖之后,公理经济学也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新时期,当然,这意味着对经典理论的扬弃和再造。从这一角度来看,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奖颁发给塞勒,又何尝不是对经济学这一古老学科的一次“助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