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图:来自 Jim Connolly 2012。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1149篇原创文章。欢迎转发分享,未经作者授权不欢迎其它公众号转载。
作者:Lisa,在37层办公室里俯瞰过莱茵河,在非洲贫民窟见识过会飞的厕所。人生不在于经历最好,而是体验更多。
四年前,25位欧洲沙发主用各自普通却迥异的生活让我
爱上了世界的多样性,从此无法自拔
。他们是我人生转变的触发器。回国后我和父母住在一起,老人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让外国友人睡沙发,死活要把自己的卧室让出来,我只得在沙发客网站上把状态改成了 “wants to meet up”。有时和这些还没倒过时差的背包客在咖啡厅喝点饮料,有时让他们来家里尝尝家常菜究竟是什么味儿。
虽然我们在各自生命中只驻足了几个小时,但是有时改变观念就是一句话的刹那。
Tara — 伊
朗的虎妈猫爸一家
Tara 是波斯语老师,趁着暑假带两个女儿和老公来中国旅行。
“我的老公不会英语,但是他会西班牙语和日语,我的两个女儿也说一点法语。”这个多语种的家庭几乎能毫不费力地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旅行了。
这一家来中国时正赶上穆斯林的斋月。“我老公是穆斯林,但是为了避开斋月不能吃东西这个规定,我们经常在这期间去国外旅行。”你看,伊朗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忍不住问了一个特别俗的问题:
“你们怎么看美国?”
“我们每一届的政府都必须对美国强硬,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是如果我有机会,我很想去美国看看,但是签证太难了。除非你在美国有亲戚。” Tara 有点遗憾。
“你知道北京的宜家在哪儿吗?” Tara 的问题让我一愣,很少有游客会逛家具店,行李应该已经被“秀水”塞满了吧。
“因为在德黑兰没有宜家,所以我每次到国外,都想去宜家看看。” Tara 将失望和渴望混合在一起,让我陷入沉默。
这一家子除了对宜家感兴趣,对“苹果”更着迷。临走,家里的每个成员都轮流和我在购物中心前合影。事后我收到照片,越看越觉得有趣。五六张照片,每个都被“打上”了苹果的 logo,有些甚至能看出特意的痕迹。

Tara 一定为了这个构图费了不少心思
我不禁想到 Tara
说过:“
在伊朗她们(两个女儿)必须带头巾,但是她们不喜欢,所以上飞机就摘了。”
政府再对美国强硬,也难以改变民众的态度。宗教再约束人的外表,也难以锁住那已经自由的灵魂。
German — 厄瓜
多尔的养虾天才
一开始看到 German 的名字,我好奇这家伙到底对德国有多热爱。
“哈哈,很多外国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但真正的读音应该是 Her Man。”这么浪漫的解释,也只有拉美人能想得出来。
German 兴奋地问我吃不吃蝎子,还给我看了他拍的蝎子烤串儿的照片。
“我们都听说中国人吃虫子啊,狗肉啊,所以我妈妈之前还担心我在中国吃饭的问题。” German 在美国学了四年农业,“我回国后找了四份工作,都要求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七点,一周六天,但是一个月只有 600 美元。”就算放在经济不景气的拉美,600 美金对于一个海归来说也确实有点少。
于是 German 父业子承,开了一家养虾厂。
“中国是我最大的出口客户!”
可别以为这就是一个来自厄瓜多尔的农民。German
年轻时是厄瓜多尔全国象棋冠军、奥数冠军、电脑游戏冠军,顶着这些头衔代表国家去世界各地参加国际比赛,几乎周游了世界。“
我就是觉得这是游戏,而我很享受征服的过程。
”所以当
German 成为冠军后,他基本上就没有再继续这些让他免费旅游的项目。
“你有测过智商吗?说不定你比爱因斯坦
还高呢哈哈。”本来我只是一句玩笑,谁知 German 回答:“我没测过,不过你知道门萨俱乐部吗,我在里面。” IQ 达到148以上是门萨的要求。都说吃鱼
虾能让人变得聪明,作为虾农的儿子,German 真是力证!
“我在国内上了两年大学,后来转去美国继续读。
我特别不喜欢我们那儿的教育制度。
”我心想谈到教育制度,还有人敢在中国人面前抱怨?“我们的大学为了证明自己制度严格,都变成存心折磨学生,不让他们毕业。有一次数学考试,我基本上就是在脑子里算算就得出了正确答案,但是老师非得让我写出计算过程,结果我没写,就得了0分。”我头一回了解了超常儿童的无奈。
除此之外,German 对于自己两个侄子的爱简直让我无法理解。
“我当时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我的两个侄子。”
每个周末他都会和侄子们待上一天。
“你这样你哥哥不会嫉妒吗,你爱他的孩子快比上亲爹了!”我笑他。
“真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哥哥同时下车,我的侄子从家里跑出来迎接我们,他先扑到我身上。
”我挺好奇,如果
German
自己有了孩子怎么办,他是不是已经把父爱提前预支了?“我也担心过,还问过我妈妈,不过她说不会,哈哈。”可惜没有一个爱侄子大赛,不然
German 也一定会是冠军。

厄瓜多尔的炫侄狂人
Jesslene — 新加坡的第六代华人
来自新加坡的 Jess
正在北大读暑期学校,于是我有机会回母校一日游。毕业生们站在图书馆前合照,在未名湖旁留下倩影,学校还是一样的学校,只是我手中的校园卡变成了校友卡。刚刚结束大一的
Jess就已经在首尔大学、香港大学短暂学习过。“我计划利用寒暑假,在东亚几个国家体验下。下个学期我会去复旦大学交换,然后再去日本看看。”
Jess 是家中的老末,“我姐姐是学建筑的,我哥哥是电脑设计,好像只有我的专业(政治学)比较切实际哈哈。
我其实更想从事社会工作,但是赚不了很多钱,我觉得自己欠爸爸妈妈的,因此以后毕业不论什么工作,只要薪水不错我就先做着。”
Jess 的妈妈为了照顾三个孩子,很多年前就辞职做家庭主妇了。而现在三个孩子都已经上学,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的她只能自己在家。“我有时候会下了课会回去陪她,怕妈妈一个人孤单。”
Jess 以为中国三口之家成员的关系不如她这样的多兄妹家庭亲密。可在我家看到的正好相反。“我挺羡慕你和父母的关系。我和爸爸交流很少,他基本上天天都在工作。”
和政治系的人在一起总免不了被问到 — 中国现在强大了,你们觉得这几年有什么变化?中国会不会把自己的模式移植到非洲?……
然而我更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有西红柿味道的西红柿,失去了夏天搬着小板凳坐在四合院里聊天的惬意,失去了排队买东西就能攀谈起来的热络,失去了宁静的什刹海和南锣鼓巷,失去了蓝天和白云……
我带 Jess
来到了西四北
7
条,寻找四合院的记忆和胡同的味道。
430米的胡同,慢慢深入其中,耳边不再是车水马龙,仿佛时光倒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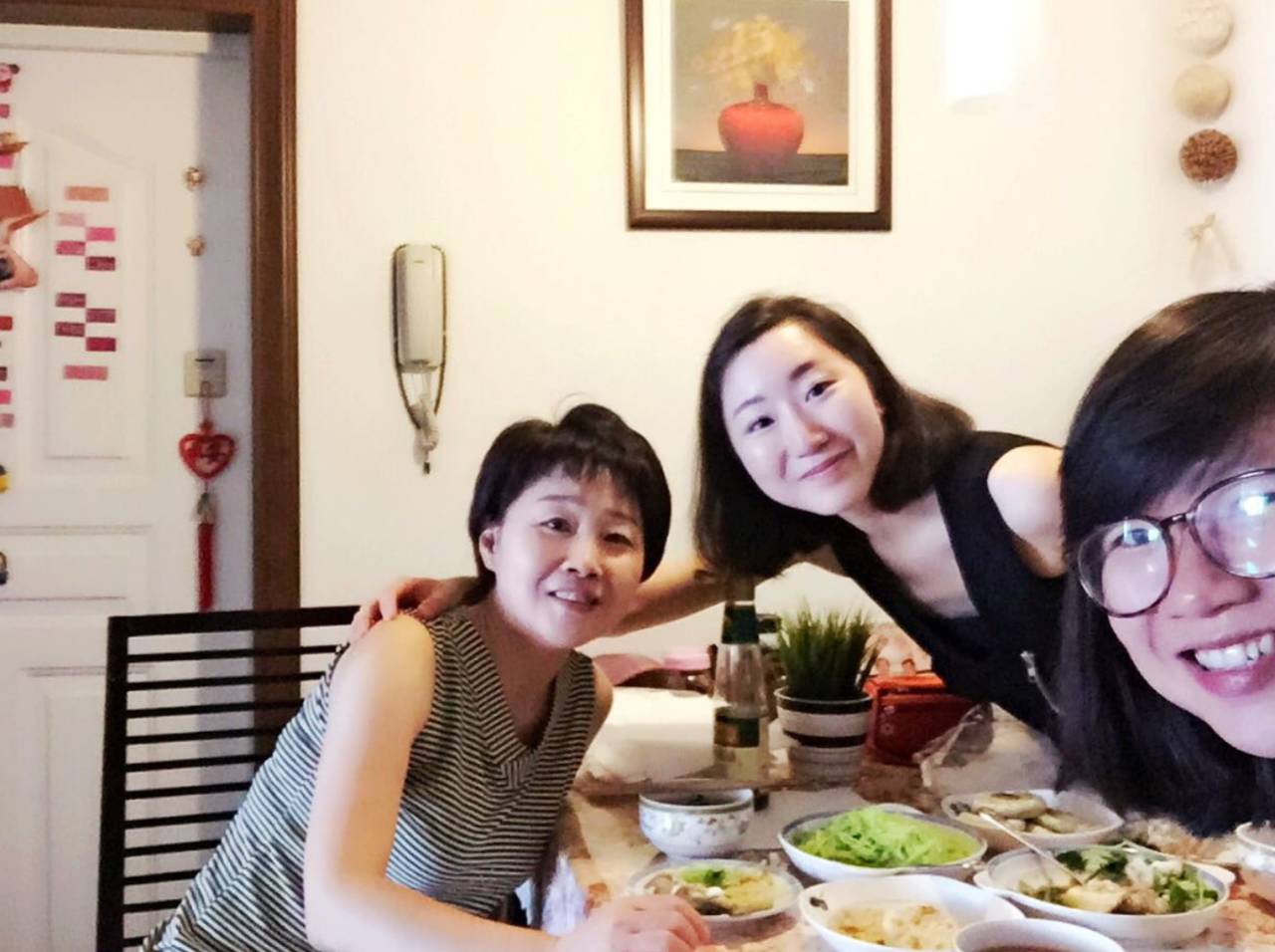
带 Jess 回家吃饭,赶上一个会说中文的,把我妈乐坏了
Alay —
美国的女生联合会趣事多
Alay 是众多沙发客中和我旅行经历最为相似的 — 在巴黎交换,她游遍欧洲,来中国前又去了缅甸,之后还要前往印度和肯尼亚。这个墨西哥和美国的混血女孩,入乡随俗,一顿“陷老满”过后,
她非要抢着买单
。服务员接过她的毛爷爷,问有没有一块钱零钱,我递过去,可
Alay 不知道缘由也听不懂中文,坚决不让服务员收,搞得我哭笑不得。
见面前我刚好读完了奥斯卡·刘易斯的书《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虽然描写的是60年代的墨西哥社会家庭情况,但里面家庭成员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生活的窘迫和社会的动荡,都让我好奇现在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里面是不是写女孩们都不上学?” Alay 问我。在得到肯定答案后她说:“
墨西哥女孩十几岁就结婚,然后就留在家里做家务,所以根本无法完成学业。
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美国。”
“我住在圣地亚哥,开车20
分钟就能到墨西哥,所以很多墨西哥人从边境偷渡过来”。提到近来美国共和党候选人
Donald Trump
对墨西哥移民出言不逊,说其是“强奸犯和罪犯”,
Alay
忿忿不平“
我很多墨西哥朋友,父母一天打
5
份工作,工作非常辛苦。本来墨西哥裔一般不参加投票,但是这回我们一定得给
Trump
点颜色看看。”(我们的见面是2015年夏天,看来 Alay 的“颜色”还有点单薄。)
我向她求证美国大学 Sorority house
里的
drama
是不是特别多,因为最近看的一部电影《
The Longest Ride
》的女主角就住在
Sorority house。
“哈哈,我大学时也在 Sorority里面!”
美国大学的 Sorority
(女生联合会)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有钱人进的,交钱就行,第二种是偏学术的,第三种是根据种族分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Alay 自己就属于这类。
“我的那个 S
orority
规定在考察期间,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每天穿同样的衣服!
我们就去商店一起买,全是黑色,这样方便哈。” 这些规定是各自的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