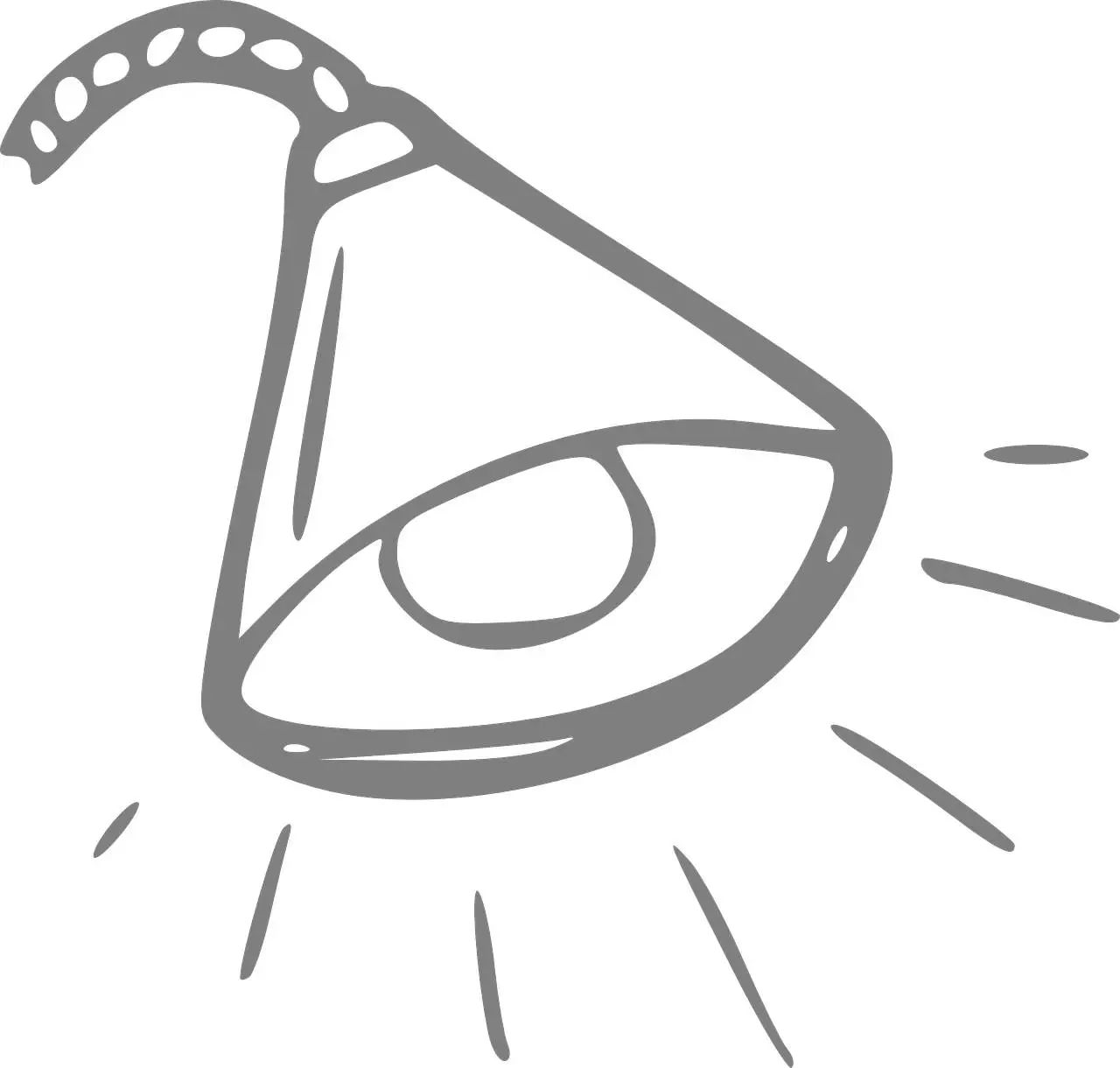![]()
把崔健的歌词当做独立的文本解读,这是一个冒险,崔健自己也许会反对这种做法。在他看来,歌词是从音乐中生成的,音乐是源,歌词只是流,不能脱离他的音乐来谈他的歌词。但是,我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而把完善的评论留待行家们去做。我这样做也不无收获,结果我的发现是,这些在狂热的演唱中呼啸而过的句子有着丰富的思想含量,它们是值得在安静中仔细玩味的。
九十年代初,在《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中,崔健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病人的故事。这个病人光着膀子,迎着风雪,跑在逃出医院的道路上。他痛苦地叫喊着: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
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
给我点儿爱情,我的护士小姐
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歌中反复吟唱的句子是: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什么样的人会因为麻木而感到如此痛楚呢?一个人把没有感觉感受为一种尖锐的病痛,岂不正因为他的感觉过于敏锐?所以,问题出在这个世界不能让人痛快地哭痛快地笑。最使一颗优秀的灵魂感到压抑的当然不是挑战,而是普遍的平庸和麻木。于是,在众人宁愿躲在医院的暖被窝里养病或装病的时候,他独自跑到风雪中发出了尖利的呼叫。
在同期作品《像是一把刀子》中,作者就直接向社会的麻木宣战了。手中的吉他被譬做一把刀子,用它割下自己的脸皮(也许他恨脸皮是人体最容易装假的部位),只剩下一张嘴(对于崔健来说,嘴只是用来唱歌的,而唱歌必是真实的,不真实就不是唱歌),目的却是--
不管你是谁,我的宝贝
我要用我的血换你的泪
不管你是老头子还是姑娘
我要剥下你的虚伪看看真的
那种普遍的麻木已经令作者透不过气来了,他无论如何要把它捅破。其实世界上发生过某些重大事情,人们却装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人们面带微笑和往常一样仍在这周围慢慢地走着”;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我面带着微笑,和人们一样,仍在这世上活着。我做好了准备,真话、假话、废话都他妈得说着。”(《北京故事》)一切都可以原谅,不可原谅的是灵魂的萎缩,麻木的病症由表及里,虚伪下面不再有真诚的核心。“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可是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宽容》)在接下来的“呵呵”的怪声中,压缩着多少无法说清的痛苦。
![]()
《飞了》的歌词比较费解,我相信它表达的也是灵魂被粘滞在平庸的现实之中的痛苦。面对周围的现实,包括过于紧密和琐屑的人际关系(“一股人肉的味儿”,“它只能让人琢磨人之间的事儿”),人们的像是烟雾的眼神(“它们四周乱转但不让人在乎”,反映了内心的空虚和软弱),以及缺乏力量的发牢骚(“在无奈和愤怒之间含糊地烧着”的无名火),我觉得“浑身没劲儿”。这种晕的感觉驱使我“孤独地飞了”。但是,我终究不能生活在空中,只好又回到现实中,再飞不起来了。(崔健注:《飞了》是一个反对吸毒的作品,我经常在音乐会上唱这首歌之前这样说:“我们用不着毒品,只要我们有音乐我们就能飞起来。”)
在较晚创作的《缓冲》中,作者对这种被粘滞的感受有更加生动细致的描写。我也是“从天上飞了下来”,不过那大约是一次旅行归来,回到了熟悉的环境中。这环境化做一片叫人腻味的声音,副歌反复唱道--
周围到处传出的声音真叫人腻味
让我感到一种亲切和无奈
周围到处传出的声音真叫人腻味
软绵绵酸溜溜却实实在在
我首先产生的反应是格格不入,不想看见朋友,不想再说废话,要跟所有的人保持距离。我发现我挺喜欢这种有脾气的伤感,因为它使我“还能看见我的生活的态度,还能感到我的灵魂似乎还活着”。在作者看来,灵魂活着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浑身骚动的热血与这环境的对比令我疯狂,我愿把这种疯狂永远保持下去。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洗完了脸,疯狂不见了,我像以前一样无所谓地走出了家门,和所有我的熟人打着同一样的招呼。我不由自主地开始装糊涂,这使我感到一种比疯狂更加强硬的恐惧。
这些描述真正具有一种令人震惊的深刻。普遍的平庸之可怕就在于它让人感到一种亲切,这种亲切具有死亡的气息,这种死亡又仿佛是有灵魂的一样,它对那些不甘让灵魂死去的人发生着强大的威慑作用。
我把以上几首歌放到一起评述,是因为它们使我清楚地看到,崔健的确是一个灵魂的歌者。他在这个时代里真实地生活着,既没有逃避,也没有沉沦,他的灵魂始终清醒地在场,经历了最具体的磨难和危险。他对灵魂的关注决非空洞的,他不是居高临下地要拯救众生,他关于灵魂所说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灵魂中所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的歌才会在别人的心灵中引起震撼。
![]()
《自由风格》
周国平对话崔健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1
配图:摄影师Craig McDean
注:由于小编在微信后台的音乐素材中无法找到崔健的原唱,
所以配乐为他人翻唱歌曲
带来视听不便,还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