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本积累与价值生产机制的传播媒介既是“经济型生产工具”也是“社会型生产工具”( Hebblewhite,2015)。传播媒介直接作为经济生产工具参与到资本增值的流通领域。传播的商品化就是促成传播工具经济生产的过程,媒介内容商品、媒介受众商品、以及传媒业内劳动都是传播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要素。商品化是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而剩余价值在市场出售的交换价值实现过程中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仅限于维持生计的需要,还延伸到社会建构的范畴”(莫斯可,2000:137),媒介内容意识形态的生产性则体现在对使用价值的社会建构上。不仅如此,传媒在资本原始积累与剥夺性积累中亦发挥作用。传媒能够在“结构性”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上参与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剥夺性积累( Ekman,2012)。传媒体制与传播在开拓资本积累的新途径,实现资本扩大再生产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媒介生产场域中的“积极受众”
在作为生产机制的媒介系统中,受众的角色与地位至关重要。“剩余价值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劳动者、消费者、资本市场等众多因素”(莫斯可,2000:142),在传媒经济生产过程中,传媒从业者的内容生产、受众的免费劳动参与、以及受众
市场变化都将影响着总体剩余价值的实现。“传媒科技的变革使商品化的新领域不断被发现,侵占闲暇时间与劳动的方法不断被开发,社会诸多方面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置入资本主义产权关系。”( Ekman,2012)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与劳动生产力的媒介使用者被吸纳进媒介生产领域中。尤其在Web2.0互联网时代,以资本利润为导向的数字媒介中介社会生活的过程就是媒介用户被卷入数字劳动的过程。
“积极受众( active audience)”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的重要着眼点。以受众是“意义的真实制造者( true producer of meaning)”为基本认知,斯麦兹开创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研究之先风,把媒介看成是由特定生产关系组成的生产场域,媒介使用者则是媒介生产场域中的劳动实践者。“受众商品”与“受众劳动”概念突出了受众在媒体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强调媒体机构是建构受众劳动与资本市场关系的重要桥梁,作为资本流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置于“总体资本主义经济” (total capitalist economy)(莫斯可,2000:137)中。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受众观”具有几层意涵。首先,强调媒介使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是历史的创造者。其次,媒介使用者的媒介素养与信息能力构成了受众劳动的基本素质,使之有能力参与一般剩余价值的生产。再次,媒介使用者是真实意义的制造者,受众在媒体价值创造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媒介使用者之所以沦落为斯麦兹意义上的“受众商品”,就在于媒介使用者具有社会实践能力,在媒介系统中扮演着劳动生产者的角色,是具有生产性的“积极受众”。大众传媒时代传统定义上的受众,以及Web2.0新概念上的新媒体用户都需要在媒介社会系统中确立自身,他们是意义的真实制造者,具有主观能动性与劳动生产能力。“受众劳动论”的理论预设源自于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生产机制的“媒介观”与作为积极受众的“受众观”。正确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会、媒介与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论证“受众劳动论”合理性的关键。
与许多批评受众商品论为经济简化论的观点相左,积极的受众能动观实际上强调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斯麦兹很明确指出“受众劳动(为广告商)与价值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张力,而这种辩证的矛盾会客观地、现实地、有力地作用于实践意识(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 Symthe,1981)“受众商品的生产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提高的一种反映,并它同时发生。”( Manzerolle,2010)因此,传播学研究 “不能忽视垄断资本主义中需求管理的角色与大众媒体在生产市场主体(受众)中的角色作用” ( Symthe,1981)。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受众研究对理解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学面向与分析媒介与资本社会的关系大有裨益,重新解读受众商品论以及关注Web2.0时代的受众劳动、自由劳动、产消劳动等新动向有
益于我们对当下媒介化社会进行批判性审视与反思。
二、受众劳动论:Web2.0数字劳动的生产逻辑
传统受众商品论受制于大众媒介传播模式,已经无法解释当下数字媒体传播环境中的数字劳动生产逻辑。大众媒体时代,信息生产成本高昂,信息生产格局受制于“有限的生产者”供应“无限的大众消费者”( Wittel,2015),信息生产渠道被权力机构垄断。数字传媒时代,“无限的生产者”供应“无限的大众/小众消费者”,新的信息生产方式产生,技术不仅作用于信息生产,还渗透到了所有的生产、流通与消费领域。呼应卡斯特(2001:26)的论断:“新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世界”,日常生活被媒介技术整合进信息化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capitalism)中去,数字媒介用户被卷入到数字媒体价值链中,服务于生产、消费和市场多个环节。

过去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在对马克思理论的运用上受限于大众传媒技术逻辑之制约(Wittel,2015),而在Web2.0数字经济流通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介作为生产机制的研究取得了理论上的进展,同时建立在此之上的Web2.0数字劳动生产的秘密也被揭开。为了洞察Web2.0媒介资本剥削的秘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被重新运用于阐释媒介用户使用行为,从而揭示了Web2.0媒介作为新的传媒系统在整个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作用。下面着重通过讨论“产消者”“你媒体”与“菲利亚”三个“受众劳动论”的创新性理论发展,分析受众劳动在数字媒体价值链的生产、消费和市场多个环节中的数字劳动生产机制与价值生产逻辑。
(一)“产消者”的两种价值生产与实现方式
“产消者”不是新概念。1980年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中首次提出“产消合一”( Prosumption),预示在第三次浪潮中消费者被卷入传统生产部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日益模糊的趋势。托夫勒揭示在产消合一社会里工作与空闲时间的界限被打乱,“大部分空闲时间不过是用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用品和劳务——产消结合时——旧的工作和空闲时间的区别和界限就消失了”(托夫勒,1984:372)。Fuchs把“产消合一”概念运用到对数字信息资本主义与数字媒介的批判中,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分析数字媒体的价值生产过程,提出了数字劳动“产消商品( Prosumer commodity)”论(Fuchs,2011),认为互联网用户作为数字劳动“产消者”的劳动价值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
(1)媒介使用者的创造性内容生产
受众劳动的信息内容生产具体可分为两类,一部分作为“生产者”创作信息内容;另外作为媒介“消费者”生产用户数据。“网络用户与大众媒介受众明显的差异在于前者是内容生产者,投入创造性活动、传播过程、社区建造与内容生产。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结构,以及多对多传播模式,使互联网中用户的活跃度远高于大众传媒中受众对内容的接收。”( Fuchs,2011)数字劳动“产消者”生产的所有信息数据与内容都将转化为商业平台媒体的无形资产,被无偿私有化与商业化。商业平台媒体依托广告盈利,核心资产与竞争力是流量与数据。平台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不生产信息内容,却拥有社交媒体网络中的所有信息数据,包括海量UGC、流量数据与用户数据,大多为媒介用户所创造。在Web2.0媒介中,信息技术服务是斯麦兹意义上的“免费午餐”,媒介使用者是“产消商品”,而广告则是平台公司价值利润的实现方式。平台公司将用户“产消商品”卖给广告商以赚取剩余价值。
(2)“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
媒介用户不仅是平台使用者,也是广告受众,受众的媒介使用时间就是劳动时间。在媒介使用(往往是观看)过程中,受众劳动生产了价值与剩余价值。这个观点基于Jhally和Livant(1986)对大众传播“受众商品”的论述,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法则(law of value)可以解释媒介资本的增值过程。“劳动时间是社交媒体价值生产的尺度。”( Fuchs,2012b)与大众媒介广播电视受众劳动一致,受众观看时间或者说媒介使用时间就是劳动时间。“使用者花费在Facebook上的时间越多,他所生产的最终被卖给广告客户的数据就越多”( Fuchs,2012b)。没有被付费的劳动时间被具象为商品,并且被资本私有化,受众劳动由此被剥削。Fuchs(2012b)举例“如果有5亿人在用的媒介平台平均每年售卖了90小时的广告(平均15分钟每天),那么它的价值创造是450亿小时的数字劳动。所有这些在线时间都被监视并且成为了流量商品被卖给广告商,其中没有任何劳动时间被付费,因此这450亿小时的劳动被剥削了。”
Mark Andrejevic(2007)把以上现象形容为数字围场( digital enclosure),揭示互动技术中所暗藏的剥削玄机,指出“互动技术中鼓励用户反馈实质上是自我交易,这种反馈最终成为了私有公司的私有财产”。在“产消商品论”中,受众既生产内容又观看广告,媒介使用实为被社交媒体公司商品化的过程。互联网平台实则是一种基于对产消商品剥削的数字围场特殊形式( Fuchs,2011)。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产消商品”的揭示披露了Web2.0媒介技术生产与剥削的秘密。互动技术把媒介受众引入信息生产部门,从事免费的信息生产工作, 数字时代的“空闲时间”实
质性转化为媒介公司资本增值所剥削的劳动时间,印证了斯麦兹的“垄断资本主义无休闲”(吴鼎铭,石义彬,2014)论断。
(二)“你媒体”与“营销劳动”的集约型剥削
Web2.0数字媒介中,用户被卷入到社交媒体价值链的消费、生产和市场三个环节,剥削延伸到市场营销领域。Eran Fisher(2015)指出在Web2.0中还有另外两种
用户价值生产:
(1)媒介使用者自身(the“self”of users)成为“你媒体”(youmedia)的过程。
(2)建构与维护社交网络渠道促成平台对用户“营销劳动”的集约型剥削过程。
一方面,数字媒体技术使社交关系进入资本监控的射程,社交行为异化为市场营销劳动。社交媒体用户在平台建立个人人际社交圈的行为使之转化成为了“你媒体”,自动从事关系网络中的广告营销活动。当个体用户与其他人建立社交关系时,其作为某类广告目标受众的身份就会顺势扩散于其社交关系网络中,“你媒体”成为了产品市场营销机制的一部分。以微信朋友圈广告为例,2015年1月上线的微信朋友圈的“信息流广告”,就利用微信用户的“群圈化”社交网络与大数据分类技术锁定目标受众。此时,朋友圈内的熟人互动效应也有利于广告的传播效果达成,朋友圈用户自动成为“你媒体”。微信朋友圈广告“广告,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好反向讽刺了信息流广告对用户社交生活的渗透与利用。在此,社交过程异化为数字劳动过程。
另一方面,“用户生产传播渠道”亦被剥削。平台使用者维护社交网络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也是持续稳固广告目标受众群的过程。在互联网数字媒介中,用户创造并维护他们自身的分类。商业平台媒体不仅商品化用户生产的信息内容,还有承载内容信息流的“用户生产传播渠道”(Fisher,2015)。因为用户建筑与维护这些传播渠道,广告才能够更为精确地被投放,增进其价值增值。这是传统大众媒体无法对受众做到的“集约型剥削( intensive exploitation)”( Fisher,2015)。平台媒体在对受众的重组过程中使广告投放更为精确有效,对受众劳动的集约型剥削由此实现。
数字平台媒体的“病毒性”与“有机性”确保传播网络建构过程被精确掌控,催生出一种作用于市场营销过程中新的受众劳动剥削形式。社交行为与维护社交的行为被异化为劳动过程。
(三)“菲利亚”与非物质劳动生产
另有学者追寻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借用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与
Maurizio Lazaratto等人的“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ur)”概念来讨论受众在Web2.0数字媒介中的价值生产。Lazzarato(1996)把非物质劳动定义为“生产信息和文化内容商品的劳动生产”,把非物质劳动划分为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两个方面。其中,信息内容( The informational content)作为技术实践实现的是对赛博空间与电脑进行控制的作用;文化内容(The cultural content)则涉及对文化与艺术标准的定义与影响,体现在时尚潮流、审美品位、消费标准,甚至公共舆论。
Arvidsson (2009)借此认为社会生产( social production)遵循着一种特殊的“伦理经济(ethical economy)”价值逻辑,“决定价值的不是劳动时间的投入,而是能够使生产性组织达到扩散连通的能力”。广告建立的是品牌与受众的关系,发挥作用的是“菲利亚( philia)”,一种积极的、情感的社区纽带 (communitybonds) 。品牌是“能够直接稳定人们创造信任、情感和分享意义能力,建立共同性的机制”,其价值建立在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剩余社区 (surplus community)”上 ( Arvidsson,2005)。Arvidsson与 Colleoni(2012)认为社交媒体的盈利不能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劳动时间概念来分析。“社交媒体中的价值生产不依赖产消者所付出的劳动时间,而在于用户参与活动所增加的社会连接(social connections,也作philia)的情感质量(affective quality)”。
媒介平台公司为受众与用户提供免费服务,即“免费午餐”目的在于增加用户对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广告品牌的“情感质量”。社交媒体公司极力在他们的用户和产品上试图建立“菲利亚(philia)”。换句话说,社交媒体中的价值主要是无形资产( intangibles),产生于情感劳动( affective labor),可以为公司股东、消费者、员工、分公司和公众等建立关系。其中,品牌(brands)就是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Arvidsson & Colleoni,2012)。由此Arvidsson与Colleoni认为社交媒体平台中的受众商品不是媒介的使用时间,而是由用户投入的情感劳动所生产的作为“菲利亚”的情感质量。Web2.0媒介平台是没有墙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社交媒体用户都是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Gill & Pratt,2008)投入于非物质劳动生产。
以上三种理论都是在Web2.0数字媒介传播环境下对“受众劳动论”的有力发展,虽然分析角度以及结论各有侧重,但在揭示数字劳动的生产逻辑上殊途同归。这三种理论都把广告与商品化视作媒介价值实现的方式。“产消商品”论揭示受众所生产的数据的商品化,“营销劳动”论强调受众社交行为的商品化,社交媒体非物质“情感劳动”则揭示出社会连接与人类情感的商品化。其中受众的注意力、信息数据、社交关系、社会连接、情感质量等都是商品,商品形式涉及个人的、社交
的与元数据(meta-data),而生产商品的劳动者除了广告从业者与社交媒体雇佣劳工之外,广大的媒介使用者所组成的受众劳动是强大的自由劳动生力军,他们通过媒介使用、内容生产、社交行为、以及情感劳动为资本市场创造剩余价值。
三、理论争鸣:受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
“重回马克思”是近些年国内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界的趋势与共识,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运用马克思的哪一个理论进行媒介批判在学界产生了持续性的争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一种反映社会根源、政治影响与意识形态的针对数字经济的系统性批判性分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面临着与时俱进的挑战,传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无法预见与想象到今日的资本主义数字空间与信息价值生产新形势( Kangal,2016)。马克思主义“受众观”与“受众劳动论”合理性的逻辑支点在于“受众劳动具有生产性”,然而学界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数字时代的受众劳动与自由劳动( free labor)却争论不休。针对“Web2.0数字劳动哪一部分具有生产性以及是否并生产剩余价值?”这一问题有两种争锋相对的理论讨论值得讨论,即租金理论与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labor)理论之争。

(一)垄断租金理论对受众劳动生产性的质疑
争论的焦点在于广告作为媒介价值的实现方式是否是生产性活动。自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到文本第二部分提到的受众劳动理论,广告都是媒介价值的实现方式。但倾向租金理论的学者认为广告不具有生产性,广告是消耗其他生产性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部门。他们认为信息技术在当代生产力的霸权地位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无关,相反,“信息的作用体现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上,以及以剩余利润、租金等形式的整个社会剩余价值上。”( Rigi,2014)广告对于垄断资本的贡献在于通过增加品牌的影响力来获取垄断租金,其中品牌获取垄断租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垄断获取高额剩余利润(surplus profit);二是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property)变现。品牌公司通过卖出自己的商标或者专利来获取利润( Rigi & Prey,2015)。这种观点否定斯麦兹,Jhally和Livant,Fuchs,Arvidsson与Colleoni等认为媒介广告具有生产性的观点,相反认为受众劳动“信息生产的价值趋向为零”,“受众劳动”、“产消者”以及“自由劳动”不具有生产性,“信息价格实际上是租金”(Rigi,2014)。
该理论认为“受众劳动论”混淆了价值传输( transfer of value)与价值生产
( production of value)的概念。Bruce Robinson 通过研究社交媒体平台盈利情况指出“广告的利润来自于非Web2.0经济部门,把广告视作对免费服务商品化的模式是充满矛盾的”( Robinson,2015)。Rigi Jakob与Robert Prey(2015)反对 Arvidsson和Colleoni所提出的菲利亚( Philia)生产新的剩余价值的观点,认为菲利亚的作用在于帮助品牌扩大再生产,但不生产新的剩余价值。他们提出菲利亚的作用有三种形式:“1.帮助品牌拥有者售卖他们的商品赚取额外利润。2.帮助品牌拥有者攫取通过版权和专利垄断地租( monopoly rent)。3.通过虚假资本( fictitious capital)和股票市场的投机”。品牌效应所带来的价格售卖包括广告宣传成本,但商品价值并没有增加。“广告成本并不能算在商品价值里,也不能算作品牌生产的价值。品牌作用能够影响需求的转换,从一种商品到另一种商品,也能够使某一商品的价格高出其价值,但并不增加商品价值”(Rigi & Prey,2015)。由此总结,租金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看”广告不是生产性行为,广告商买的不是受众,而是租用了能够到达未来受众的传播渠道。
(二)回应:广告生产剩余价值与受众劳动具有生产性
支持受众劳动论的学者对质疑进行了反驳,认为广告活动中有生产性劳动与剥削。Fuchs对受众劳动论的批评者回应到:
“把生产领域( productive industry)与非生产性的广告( unproductiveadvertising)做严格的区分是武断的,是一种过时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 orthodox Marxism)的假设。这种过时了的对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的理解产生于广告与消费文化并没有那么盛行于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Flisfeder,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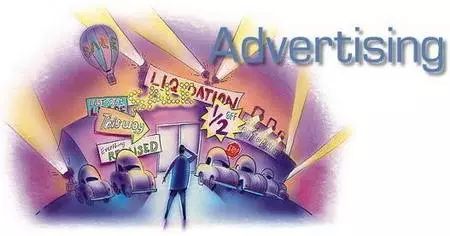
广告作为意识形态商品已经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McChesney,2013),不仅参与别的商品的销售与生产过程,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被作为销售对象的服务产品而存在。
究竟广告活动何以生产剩余价值,以Fuchs的论证最为有说服力。Fuchs用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calist)方法来分析劳动,既涉及劳动过程,也包括意识形态。他指出广告中包括生产性广告劳动与传输性广告劳动。其中受雇于广告公司的员工所创作投放在社交媒体中的广告标语、图像内容等过程是生产广告客户所销售商品的“符号意识形态部分”(symbolic-ideological component),在这个创造过程中,他们同时生产价值与使用价值。广告生产“使用价值承诺”( use-value
promise),是一种与特殊商品销售联系的意识形态承诺( ideological promise)。这种承诺与真实的使用价值相分离,是一种针对消费者的使用价值的虚假形式。广告机构与部门为扩大销售而创造“意识形态的使用价值”( ideological use-value)。而针对消费者,商品的意识形态就是使用价值承诺。马克思的传输劳动是劳动的特殊形式。广告传输工人的工作不是对商品进行物理空间上的传输,而是创造广告传播使用价值承诺给潜在消费者的传播环境。“Facebook的使用者与雇佣劳工相当于21世纪的传统工业社会中的马克思意义上的传输劳工( transport workers)。他们是生产性劳动者,为商品公司传输使用价值承诺给潜在购买者。”( Fuchs,2015)由此,商品的意识形态在广告中表现,是由具体的和抽象的劳动生产出来的。超出基本价值的(basic value)的附加价值( additional value)是劳动时间,体现为被广告的产品。
针对如何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Wittel(2015)借用马克思的概念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剩余价值,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不在于它从事的是什么劳动,而在于他和资本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其劳动成果的商品形式。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Grundrisse)里指出技术和一般智力( general intellect)都可以被资本剥削,Wittel认为自由劳动具有生产性。仅用雇佣劳动来解释当今互联网时代的劳动价值生产是不与时俱进的,Fuchs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只考虑到了雇佣劳动(wage-labour)具有生产性,忽略了非雇性质的免费劳动也具有生产性。比如传统马克思对家庭劳动的剥削性质轻描淡写,被女权主义批判为是一种父权制思维下对雇佣的迷恋”( Flisfeder,2016)。因此,“受众劳动论”媒介批判的理论之基础就在于能够论证受众劳动具有生产性,媒介作为生产与剥削机制的媒介观具有合理性。
(三)受众劳动生产关系与不平等
之所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要强调受众劳动具有生产性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关系与强制性剥削。为了清晰地勾勒社交媒体生产方式中的不平等关系, Thomas与Sevignani (2015)等学者提出了社交媒体生产方式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中社交媒体用户与劳动工具构成生产力,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者与社交媒体用户构成的生产关系(见表格2)。其中,社交媒体的生产力是社交媒体用户与影响在线劳动的社交媒体生产过程的要素构组成的系统,有主客观之分。社交媒体使用者的体力与智力能力构成主观生产力,数字劳动过程要素构成客观生产力。数字
劳动客体包括人类经验,在线信息与在线社交关系;数字劳动工具包括社交媒体平台,互联网与数字设备。而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并组织人类经验、在线信息与社交关系,构成“社会大脑的一般生产力”( Allmer,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