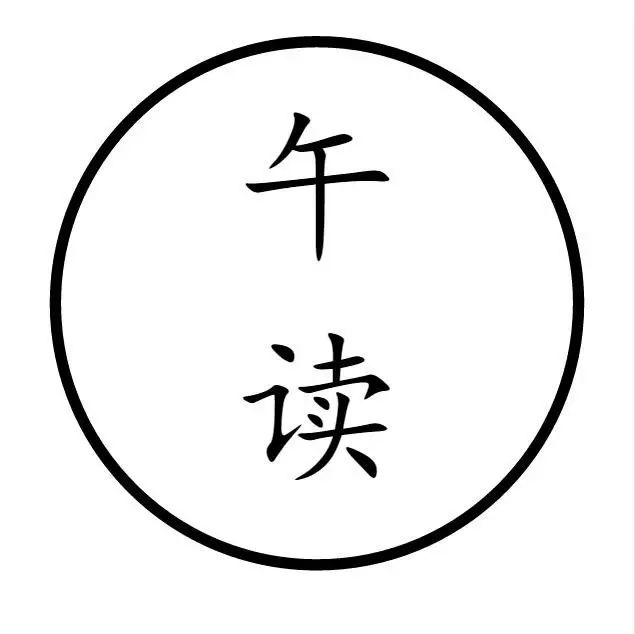赵延年是新兴木刻运动中非常重要的第二代版画家,他的成长与第一代木刻版画家的引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而他也在回忆中屡次谈及从前辈们那里获得的教益。目前有关赵延年的研究比较多地聚焦于他在抗战以后的木刻,特别是新中国以来数量甚多的鲁迅题材作品,
本文则希望将目光投向他的早期岁月,尤其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与他的师友们的集体性艺术行动,以捕捉奠定其艺术探索的“初心”与“本色”的些许信息。
赵延年1939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求学期间,因为受香港《耕耘》杂志所载抗战木刻的启迪,与同学一道组织“铁流漫画木刻研究会”,并自学木刻,由此而开始木刻创作。1940年本欲赴昆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求学的他,滞留广东韶关而转入广东省立战时艺术馆美术系就读。1941年他提前毕业,被派任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艺术干事,负责编创《民教木刻》画刊,且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42年2月,他参加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组织的战地写生队,返回后于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广东韶关等地举办“战地写生画展”;其后又赴江西赣州举办个人“战地写生展”。[1]
1939年,赵延年(前左二)与上海美专同学合影
据赵延年的回忆: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之际,他在广东省立战时艺术馆时的老师刘仑联系了彼时已在第九战区的李桦,获知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2]要组织战地写生队赴长沙前线写生,邀请其参加。他为长沙会战大捷的消息所鼓舞,欣然答应,于1942年2月14日,亦即大年三十夜便乘火车赶赴长沙。在长沙城,他见到了李桦;而在长沙前线,他们给98师师长王甲本将军以及前线有战功的广大将士们画速写;他们还去俘虏营给日军俘虏画速写并让其签名。这些速写有近百张,8开纸大,主要以竹笔粘墨画成,经挑选参加了战地写生队的多次展览。可惜的是,这批非常珍贵的速写作品后来毁于“文革”,只剩下两张日军战俘的速写留存,现藏于中国美术馆。[3]
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会徽
“几十名日军战俘身穿灰色大棉袍在禁区内,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在闲聊,有的神情无聊淡漠,还有的脸上仍充满敌意。”[4]这是赵延年赴日军俘虏营写生时的印象。在另一段回忆中,他谈到类似的情形:“屋子里,俘虏们有的躺着抽烟,有的聚在一起玩纸牌,一幅安闲的样子。”但据看守的士兵介绍,这些俘虏刚来之时并非如此,而是想方设法自杀。他尤其记得其中一个叫相川丰茂的眉清目秀的年轻人。[5]我们从留存的这两张落款1942年2月20日的日军俘虏速写可以看到:《俘虏们在赌纸牌》(图1)描绘了四人围坐在一起埋头打牌的情形;《俘虏群像》(图2)则描绘了姿态各异的8人头像,签名有小川、堀池、山川、沟口、黑木、中曾根等,其中就有赵延年所说的“相川”的名字。两幅作品从运笔来看都应是以竹笔粘墨绘就的速写,简洁而生动,正对应了文字记录中的俘虏诸般形象。
图1 赵延年 《俘虏们在赌纸牌》速写,27x19cm,1942年,中国美术馆藏
图2 赵延年《俘虏群像》速写,27x19cm,1942年,中国美术馆藏
对于战地写生队的这段经历,现如今或许较难寻觅到更多的踪迹,但
笔者试图通过赵延年在这一阶段与其他艺术家的交互关系来探析一个初涉艺坛的进步青年和一个激烈时代之间的关系
。赵延年1938年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高级艺术科绘画组学习时就接受过较为严格的素描训练,后来他在广东省立战时艺术馆学习时所创作的木刻《广东省立艺术院美术室》(图3)受到他的老师刘仑的好评,他评价赵延年以简洁的刀法将绿树丛中的泥墙茅屋生动立体地表现出来,“题材虽平凡,但却是现实的”“用刀的活泼,黑白衬托的适当”让人不敢相信是木刻初学者的作品。[6]
图3 赵延年《广东省立艺术院美术室》黑白木刻,开本27cm×19cm,刊于《木刻艺术》1941年第1期
赵延年所绘的广东省立艺术院原名为广东省立战时艺术馆,于1940年8月成立于韶关塘湾,为抗战宣传的需要而产生。由时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兼任馆长,戏剧家赵如琳任副馆长兼戏剧部主任,原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校长胡根天任教导主任及绘画部主任。因抗战形势的变化,该馆后又迁至连县,1941年才迁回韶关五里亭,并改为永久性的专门艺术专科学校广东省立艺术院,设美术、戏剧、音乐三大部门,学制也由半年期更改为二年期。[7]赵延年的这幅版画成为了这一时期简朴的茅屋校舍的图像见证。而也正是他的老师刘仑后来邀请他参加战地写生队。
在战地写生队,赵延年还近距离见到他最崇敬的老师李桦。此前,他在广东省立战时艺术馆学习时曾聆听过李桦的讲话,在负责创编《民教木刻》铅印画报时,又常常通过书信请教。他学习木刻的很重要资源来自《苏联版画集》的剪贴板,因而受到苏联版画表现手法和刀法的影响。当他将自己创作的较为满意的、刻画细致的作品《秋收》寄给李桦时,李桦指出了作品表现内容事实上的讹误,并强调“搞创作应该到现实生活中去体验、观察”,给其留下深刻印象。而参加战地写生队则直接接触到李桦,并见到了他的很多木刻原作、速写,更是令其眼界大开。[8]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赵延年抗战时期的作品数量有限,一部分是描绘时世艰难背景下的底层人的生活,一部分则为对敌斗争的宣传漫画。其中有一幅创作于1941年的、直接反映抗日战争场景的黑白木刻《最后的一个》(图4),表现激烈的作战前线,一个缠着纱布的战士在倒下的战友旁仍然坚持战斗,体现出中国军人坚强不屈的斗志。
图4 赵延年《最后的一个》,黑白木刻,开本17.7cm X2.9cm,刊于《阵中文汇》1941年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
而他的艺术风格,则是
一面受苏联木刻的影响,一面加以自身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的悉心体察
。1944年,他创作的一幅表现赣南矿工艰辛劳动的木刻《负木者》(图5)入选《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书中评论其为“木刻界最年轻的鬼才”,言其“刀法稳健,精密,颇近苏联作风。但在交错的线条中流露出东方人飘逸的气质”。[9]
可以说,因为对于抗日战争中现实生活的深刻体会,因为同样受到抗战强烈刺激的师友们的引导,赵延年对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有了非同寻常的理解,这也为他以后的艺术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图5 赵延年《负木者》,黑白木刻,20cm×17cm,1944年
赵延年参加的湘北战地写生队,由刘仑带队,成员还有陆无涯。据报载,他们返回韶关后,举行报告展,共展出以湘北三次会战为主的作品约200余件;战区编委会还拟定出版三人的湘北三次会战画集。[10]
根据刘仑对这次战地写生的回顾,他们三人尽管生活、个性和年龄各不相同,但共同点在于“真诚地学习”“真真正正的去写生,写的全是真真正正的东西”,而这也是他们组成“X战区长官部编委会特派湘北战区写生队”的愿望。他们受长沙和湘北战场的鼓舞,满怀崇敬之心,不惧凛冽的北风和肮脏的泥土,“从朝画到晚,从饱画到饿,画到看不见颜色的时分”。他认为,
是抗战把他们“拖出了学院,从大都会到村庄、军营去,从狭小的画室走到旷垠的原野”;让他们意识到现实的重要性,在现实中去重新学习不认识的事物。因而,抗战对于艺术工作者和无数民众都是很好的教育。[11]
这是刘仑为湘北写生队在桂林的展览所写。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辗转于抗战前线进行战地写生。“七七事变”之后,当时身在惠州的刘仑便积极投身到抗战运动之中,指导儿童团工作,创作木刻和宣传画。1938年10月惠州沦陷后,他转至从化、清远一带,创作了大量战地速写。1940年1月,“李桦、刘仑战地速写画展”在香港举行;4月,“刘仑战地素描展”在桂林举行;其后又在曲江(韶关)举行“刘仑前后方素描展”。11月他还在韶关兼任广东省立艺术院特约木刻讲师。[12]正是此时,他成为在该校求学的赵延年的老师。
刘仑在各地的展览陆续引起反响,香港《立报》刊登罗布的文章《战地漫画观后》对其作品的精神和技巧均给予好评。黄新波通过“刘仑战地素描画展”赞誉他是站于战车上的艺术家,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他的生活以及“理解我们民族解放战争诸般英勇艰苦的事迹”;他“以透过现实的情感去驾驶战车”,尽管他的视野还不够开阔以及多少受了繁杂的流行的影响。[13]而就“刘仑前后方素描展”,《中山日报》更是接连刊登了郭锦恩的《看完刘仑画展之后》、周镕的《从野兽派作家刘仑个人画展谈到中西绘画艺术的共通性》、吴琬的《为刘仑素描展说几句话》等多篇评论文章。[14]
刘仑 《前面有咱们的障碍物》 版画 1935
郭锦恩的评论指出刘仑作品在取材和笔法上尽力写实的同时,又提出新的战时写实绘画应不同于机械的摄影机,而是要对现实事物作主观选择,观察与批评,揭示光明与黑暗,才能起到动员、宣传与教育民众的作用。[15]周镕的评论则将刘仑的前后方素描作为中西绘画共通性的一个案例。他认为,中西绘画本有到底是倾向事物的表现还是再现、注重内在的意境还是自然的模仿之区分。而到了现代的艺术这里,因为社会需要,要在艺术的形式中求真理,导致了破坏形体的主观化倾向。刘仑的作品就是破坏形体的一个实例,它融入了思想与心灵的表现以及透视法的远近描写,“在形式之外求画,在气韵之间作画,从西洋画的本来自然主义的作风,进一步转变到野兽派的作风”,正说明中西绘画的内质、表现形式、意境逐渐趋向共通性了。[16]吴琬的评论突出地指出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包括艺术家们艰苦而强有力的锻炼,激烈的社会变动改变了艺术家的生活,使其卷入抗战的大洪流,面临和投身民族生死存亡的肉搏。艺术是现实的反映,因为根植于丰富而生动的现实生活的体验,刘仑的作品构图和形式都发生“不可企及的变化”。[17]
这些评论多少都涉及到艺术与现实生活、写实与表现的关系问题,只是各人对刘仑作品的认知倾向有些差异。郭锦恩站在战时写实绘画的立场,对刘仑作品配合抗战动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刘仑的作品显然不是机械的再现,他或许只是对现实事物的选择与政治宣传的关系理解上还把握不够精准,但在风格取向上,他无疑还保留着其学习背景的痕迹以及主观态度。刘仑早年求学于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得到陈之佛、倪贻德、谭华牧、黄君璧等老师教益,西洋画、中国画成绩皆名列前茅。他又喜读诗歌和新文学书刊,以及文艺复兴和印象派读物,常作水彩画写生;后来受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影响走上版画创作之路。1935年加入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并赴日本学习木刻。[18]从各类报刊所见,抗战时期,刘仑创作了不少关于战场、兵营、军民生活的速写以及木刻作品。他的木刻刀法绵密,善于线的谨细组织,常以弧形排线强化烟雾和树冠的旋转感,使得画面极具有动势,1940年创作的木刻《同志,这里还有一个》《前线军民》(图6)就是代表性的例子。而他的竹笔画或水彩画则造型朴拙,用色简明单纯,有几分后印象派的特点,这可从他来自南战场的写生《桂林警报》《拾穗》(图7)《增从线上的茶粥站》等窥见一二。周镕看到了刘仑作品中现代派风格的因素,但文中所说的野兽派作风也许只是一个模糊的指代,刘仑的创作尚未走得那么远。
图6 刘仑《前线军民》,黑白木刻,11cm×10.1cm,1941年
图7 刘仑《拾穗》,水彩画,刊于《今日中国》1940年第2卷第7期
而吴琬谈及的抗战对于刘仑的淬炼,刘仑自己有过多次非常强烈的表露。作为一位战地写生经验丰富的艺术家,他在《在南战场的十三个月》中饱含深情地叙说这段艰辛而珍贵的经历给予的深刻影响:“
一种刺心的,紧张而悲壮的战争生活,像一把燃烧着的真理火炬,永远地,永远地明照在我的脑袋里。”“这时候,我好像一个捕捉真理的诗人,一个斗争的艺术工作者。因为艺术到了这时候,便兑现了一种慰藉与鼓励杀敌的效能。
”[19]抗战促使艺术家们投身这一斗争的激流,同时也使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得以锤炼而焕发新的生机。1942年,他在《给部队的美术工作同志》一文谈到,美术工作者要充实革命理论基础,并了解文学和时事;还要在战争的生活中“以最活泼的手法,摄取最丰富的画材,以此增强自己工作的能力,间接帮助建立新美术的基础。”[20]
“新美术”或“新艺术”是抗战以来日渐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它的含义也随着抗战的推进而愈加丰富和充实。
湘北战地写生队总共3人,另外一人陆无涯也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录,他说长沙三捷之后李桦便来信催促他们去湘北写生,然而最终并未动员到更多的人参与。他们三人于1942年2月14日冒着凄风苦雨离开韶关曲江北上入湘,来到长沙,这里的一切,包括树木、街景、堡垒以及战士和“湖南老乡”们都给其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战区长官和“泰山”军(国民革命军第10军的代号)的帮助,他们得以自由地前往任何一个阵地和防线写生。他们在战争的残垣断壁之间,在冰冷的风雪和发臭的泥泞陋巷之中,起早贪黑地纵情写生。这次四十多天短促的战地写生给他强烈的感受是:惯居后方的他们在画室里的创作显得虚无而局促,而今奔赴战地,创作的视野大为开阔,技术也得到更新,因而,
只有描绘存在于现实生活里的真实的东西,艺术才具有真实的生命
。他还就战地写生提供一些建议,比如把握战争的时间性,预先搜集口头与文字材料,实地与相关故事相联系,写生器材务必简便,熟悉战役经过和相关地理知识等。[21]
从陆无涯创作的相关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其所说的泰山军以及坚守阵地的战士们的描绘(图8),还有日军俘虏的写生。与赵延年不同的是,我们所见的陆无涯《俘虏群像(湘北写生习作)》(图9)是一幅木刻作品,但显然来自于对速写的加工创作,人物形象作了一定的改造,以体现某种对侵略者贬斥的情绪,可以与赵延年所绘的俘虏群像相映射。
图8 陆无涯《岗位》,黑白木刻,刊于《艺术轻骑》1942年第1期
图9 陆无涯《俘虏群像(湘北战地写生习作)》,黑白木刻,刊于《艺术轻骑》1942年第5期
陆无涯少年时曾就读于新加坡莱佛氏书院,其后又于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洋画,师从陈抱一、王道源等。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赴粤北参加抗战,并担任第六队队长。[22]他的画风受到西方绘画的多种风格影响,1948年他将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的部分习作和创作草稿结集出版,王琦评论说,从这些战争影响下的“可怕可憎可感的景象”中,可以看到他创作主题的鲜明、路线的正确以及技巧的纯熟而强烈,画面色彩光暗对比强烈,笔触粗大豪放,构图有力,主体凸出,一扫旧的写实主义的柔弱和纤细。评论者还继续从他的创作中找到杜米埃、毕加索以及珂勒惠支等的影响。[23]陆无涯《风雨集》[24]里的作品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即反映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以及统治者或敌人的暴虐,但在风格取向上则可以看到与其在香港人间画会的同人符罗飞、黄新波同期作品所共受的外来影响。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可以说,湘北战地写生队连接起三位极为不同的艺术家,抗战以及战地写生的经历对于他们均产生了深刻的心灵撞击和艺术影响,但他们在与现实生活高度结合的艺术行动中实则又演绎出不同的风采。
除了湘北战地写生队的三人,还有前面已经反复提到的李桦。他曾就读于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其后又任教于该校并发起组织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刘仑、陆无涯与之皆有关联,而赵延年则是在广东省立战时艺术馆时便与李桦、刘仑有接触。此次湘北战地写生队,李桦虽然没有同行,但无疑是该写生行动的关键人物。他告知信息,催促成行,并提供联络帮助。并且,他自己就是最身体力行的战地写生艺术家。
“七七事变”后,李桦积极投身抗日运动并创作抗战版画。1937年11月他加入军队,随军辗转豫北、赣北、湘北、湘中等地,创作了大量战地速写。在抗战期间,他还发起和组织“中华全国木刻抗敌协会”,任协会理事和负责湖南分会工作。他编辑《开明日报∙抗战木刻》周刊、《诗与木刻》副刊、《木刻导报》双周刊,办木刻函授班;主办“‘七七’纪念木刻流动展览会”和出版《抗战木刻集》,发表大量作品和文章。特别是他还举办了多次与抗战有关的个人展览,如1939年在桂林的“战地写生展”、1940年在香港漫画分会举办的“李桦、刘仑战地速写”、1943年在桂林举行的水墨画展;1945年在广东坪石举行“李桦版画水墨画展”等。[25]
李桦自刻像
1939年6月李桦在桂林的个人战地素描展引起较大的反响。1939年6月28日《救亡日报》刊登小高的评论文章《创造抗战绘画的新生命:介绍李桦个人战地素描展》,陈述了这个展览的布局和主要内容:展览按照随军路线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配有作者所经过路程的地图,贴满16开纸大的素描画,内容包括后方农民生活、军民合作、突击队动态、汉奸敌人丑态、交通破坏与建设等各个方面。他认为,其中展现湘北的24幅素描取材最为真实生动、构图最为完美。这百余幅作品“完全是李桦个人艺术上努力的成果,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抗战史画”。[26]
艾青亦在《记“李桦个人战地素描展”》一文中评述这些作品所触及到战地人民生活、士兵生活、农民生活、伤兵生活、长沙大火情形、行军的盛大景象等极为丰富的生活面。他还通过李桦的作品案例分析了宣传和艺术、内容与技巧的关系,最后他盛赞道:“李桦先生是把生活的内容和艺术的技巧糅合了的可贵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不仅在我国是可以作为奠定绘画上新写实主义的基础,同时也是我国可以夸耀于世界的艺术文化的巨大的收获之一。”[27]
李桦在评述这一战地素描展的文章中描述了自己随军辗转过程中所见的全新事物。他强烈地感受到,画室只是训练了他的技巧,艺术内容则要到社会的核心中去寻找,于是他要跳出画室,在现实中去学习。[28]次年,他又撰文继续谈到战地写生的重要意义,指出画家由从前狭小的画室跳到战场,与现实打成一片,
认识到“绘画不是为少数人享乐而存在,要为社会而工作,要创造出一种‘现实主义’”。
抗战促使中国画坛获得这种觉醒,由此也为中国的新兴艺术奠定了稳固的基础。[29]
李桦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抗战是如何促进新艺术的建立的。他认为,抗战不只是建立新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基础,也是建立新文艺的基础,艺术不只是满足抗战宣传的需要,它还负有提高广大民众文化水准和建立自身未来发展的根底的任务。“在抗战建国的洪炉中,我们已锻炼出新艺术的认识。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广大的民众身上的。它有着新写实主义的形式,带着浓厚的政治性的内容。”[30
]现实生活、政治性、大众化以及与之结合的艺术语言表现,无疑已经较为清晰地昭示出李桦所说的“新艺术”形态。
虽然作为新兴木刻运动的重要创作者和组织者,李桦最为突出谈到的是木刻,但他所指的“新艺术”绝不仅限于木刻。他似乎是借助战地生活全面地推进其“新艺术”的目标,除了造型坚实有力的木刻(图10),还有大批量的各类钢笔、竹笔、木炭、水墨速写(图11),从数量和内容涉及面讲都是绝大多数战地写生创作者难以匹敌的。他的水墨作品主要着重于对现实生活情景与人物的体察,而丝毫不受传统水墨题材和笔墨程式的约束,在灵活生动的刻画之中体现出水墨的韵致。(图12)并且,他经常就同一题材和内容进行不同媒介的表达。
左,图10 李桦《前线生活》,黑白木刻,刊于《东方画刊》1941年第4卷第2期
右上,图11 李桦《小心地检查你的枪呀?我们的游击队》,速写,刊于《耕耘》1940年第1期
右下,图12 李桦《油菜花》,水墨画,刊于《清明》1946年第4期
正如一则有关他的战地水墨画的评论认为的,抗战对于中国艺术的促进以及现实主义基础的奠定,在木刻和漫画方面自不用说,在作为纯艺术的绘画方面也有所进展。李桦是一个木刻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新艺术运动的建设者”。“他一面运用木刻作为新艺运的尖兵,一面却潜心于现实主义绘画的创作。”他以水墨这一旧工具大胆探索新的表现,却又不失去水墨固有的优点。即使是他的风景画,也不只是自然美的描写,而是与现实生活有关;所描绘的人物和事物则更是触动人心,让人“感到有人类的血肉,脉搏,和时代的气息”。[31]
陈芦荻在谈论李桦的水墨画时,则陈述了他从倾心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派转向崭新的、战斗的新兴木刻艺术道路的经历。而现在,他又摄取西洋画的表现手法,向水墨画领域迈进。在陈芦荻看来,李桦所创造的艺术道路之所以值得珍惜,在于他“不落于前人的窠臼”“肯去生活,迫近人生”,以及“肯定了绘画的现实主义”。[32]
李抗编《滴泉集:李桦的艺术历程》,安徽美术出版社,2012.2
李桦的艺术道路抑或关于新艺术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一批从事新兴木刻和漫画创作的艺术家的共同观点。由李桦、刘建庵、廖冰兄、温涛、黄新波执笔的《十年来中国木刻运动的总检讨》一文,在阐述中国木刻运动的本质和时代背景时便指出,木刻运动不只是技巧的进步抑或引入西画的新流派,而是建立中国新绘画,即新现实主义绘画的首要契机。它否定过去的士大夫文人画以及陈旧学院派和现代主观画派等脱离大众的绘画,而负起建立大众绘画的责任。所以中国木刻只是中国新绘画的前哨,它最终要扩大到对整个绘画的影响。文章还比较了新现实主义与旧写实主义的区别,反对只是对现实事象的照搬,而强调政治上的策略和意识,即“凭借艺术的力量去激动大众的情绪,使大众知道所爱与所憎,指使他们如何去战斗,如何去争取幸福的生活”。[33]
这篇长文以及李桦的众多话语实际上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信息。
新兴木刻艺术家们所主张的新艺术或现实主义,在风格上要区别于机械再现的写实主义,但又不同于同样反对再现的现代派;在思想倾向上,它是为政治和社会而艺术,不是要追求艺术自律的本体革新,或者说,艺术性要与政治性、大众性相结合,在现实生活的锻造中推进语言变革。
而就整体艺术界来说,随着时局的变化,写实主义的确越来越占据主流的位置,但是,人们对写实主义本身又有不同的理解。学院派的写实主义与从苏联传入的强调无产阶级属性的“革命的写实主义”的内涵就迥然有别。于是,又不断出现“新写实主义”的提法,以示与旧的写实主义的区别,然而,关于“新写实主义”的认识仍然是有差异的。[34]同时,艺术界用“现实主义”代替“写实主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以突出取材现实、强调典型化表达的大众化艺术导向。不过,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众多拥有不同学习背景和生活体验的艺术家,因为抗战以及要为中国新艺术付诸努力时,注定是一个透彻灵魂的过程。
由一个战地写生队可以展开一幅宏阔的抗战美术画卷。抗战以强劲的力量推动艺术家跳出画室,投身社会现实生活的洪流。在此当中,现实主义越来越成为某种共识,并经由众多艺术家饱含激情的实践与探索,而在内容取材和语言风格上形成新的变革的动力。在抗战组织、动员和与大众结合的潮流中,一切被认为脱离大众的艺术取向变得不合时宜。
作为抗战最为有力的文艺工具之一的新兴木刻,并不局限于这一艺术门类内部的些微变动。不少木刻家所希望的是以木刻为前哨,吹响整个新艺术的号角。而因为抗战的艰苦环境、绘画材料的紧缺,艺术们在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过程中也自然实现了媒介的跨越。李桦、刘仑、陆无涯、赵延年均谈到在战地写生中所使用的竹笔这种创作工具。虽然以竹笔写字或作画古已有之,但使用者寥寥。
如果说,木刻本身就是因为其取材便捷、传播性强而成为革命美术广泛使用的媒介,那么,竹笔画则是在更加艰苦的环境下被更多人采用。他们以竹条或筷子劈松、削尖作笔,以锅底烟渍混合桐油制墨,在土纸上作画,竟产生未曾预料的效果。[35]当然,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木刻,这两种媒介是并行的,或者一主一辅,或者同一画面不同表现,完全视条件而决定,而更为远景的目标则是突破单一媒介的整体的现实主义新艺术。
沈健编《那年,那画:赵延年先生二十世纪30至60年代作品发表收藏》,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7
所以,抗战还使得新艺术或新现实主义在与所谓旧的写实主义以及其他现代派取向的交锋中日益取得主导性地位。这不仅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的差异,还被注入了鲜明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因素,当然,这一新艺术也是在不断的政治和艺术的整合、调适中逐渐一体化的。与艺术探索之路发端于战前的那些新兴木刻先驱者不同,
赵延年创作伊始便置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彼时已经在抗战前线的李桦等人将其强烈的感受以及关于艺术的新认知传递予他,使得艺术与生活相结合的“新艺术”主张几乎一开始就成为他创作的底色。并且,他自己也奔赴前线,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大时代的激荡,从而成长为一名坚定的现实主义艺术工作者。
[1]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浙江省版画家协会编:《刀木人生——赵延年艺术研究文献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215-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