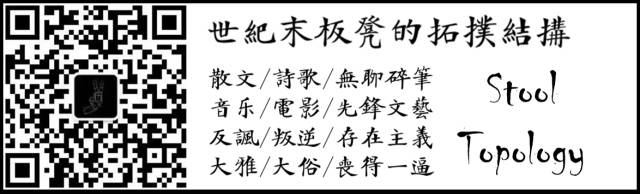
这个栏目歌曲大多来自
青年小伙子
,封面大多来自
@叶飞影
做的非线性图像(转侵删)
咕咕咕~大噶好,鸽王又回来了。回想起来最近的灵感大多是出自宇结电台,那时偷懒把这些点子概括成一句句话发给“我的电脑”或“我的手机”,这导致今天完全记不起当时的细节、内心起了什么样的波澜,这是时常发生的局面。以后试着快速写下来吧,不过令人担忧的是,最近灵感真的是越来越少,以至于拿别的月份来凑了。
这个栏目比较随意,想到什么便写,当然你也可以说,奈何回应者寥寥,只
有
@是鱼啊🐟🐟
写下了自己的
想法,记为“0”。如果你看完的话,底下有一个
投票
,选出你最喜爱的思维碎片吧,超过10个人我就立马再更一篇(笑。
0
@是鱼啊🐟🐟
厌弃自己及周遭
与怕死
矛盾吗 不
(没错 我很无趣 且是个丧狗
05-07
1
谈到欧洲的公共厕所少又贵,以至于穷学生不得已蹭顺风厕,宇结主播们表示很魔幻。青年老师回想起与之相似的世界观的改变,是在品尝到真正的日料后,他突然意识到日剧里的角色原来是吃着这种味道的食物生活的。于是他意识到,看过的欧洲文艺作品里人们的生活除了表现出来的之外,还包含“有人跟着别人进厕所”这样不可或缺的部分。
若是虚构一个欧洲电影,讲述几个年轻人组乐队的故事,在银幕背面我们可能会看到排练结束后的插曲:主唱消费了一杯咖啡,凭小票打开厕所门,贝斯手跟着挤了进去,门关上,慢人一步的鼓手只能憋着。凡此种种,在我看来与非虚构作品的深度挖掘如出一辙,与某个时代背景下不知名人物的传记休戚相关,令我感到“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却又诚知“世事皆可原谅”。
1.5
无独有偶,一月番《比宇宙更远的地方》中也有这样的表述。去南极的少女们在新加坡短暂停留时,得知这里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小决:“那大家就是先齐聚在这里,然后再度出发去往世界各地吧……
不管我们去了南极也好,还是回到日本也好,这里的每一天依旧是船来船往……每个人都维持着这种平凡的生活。”
结月:“今天学校也在照常上课,现在大概正是吃晚饭的时间。”
小决:“嗯,无论是我们没见过的地方还是我们不了解的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人过着形形色色的生活,每一天都不曾中断,这真的很厉害。”
报濑:“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不过,我能理解这种感觉。”结月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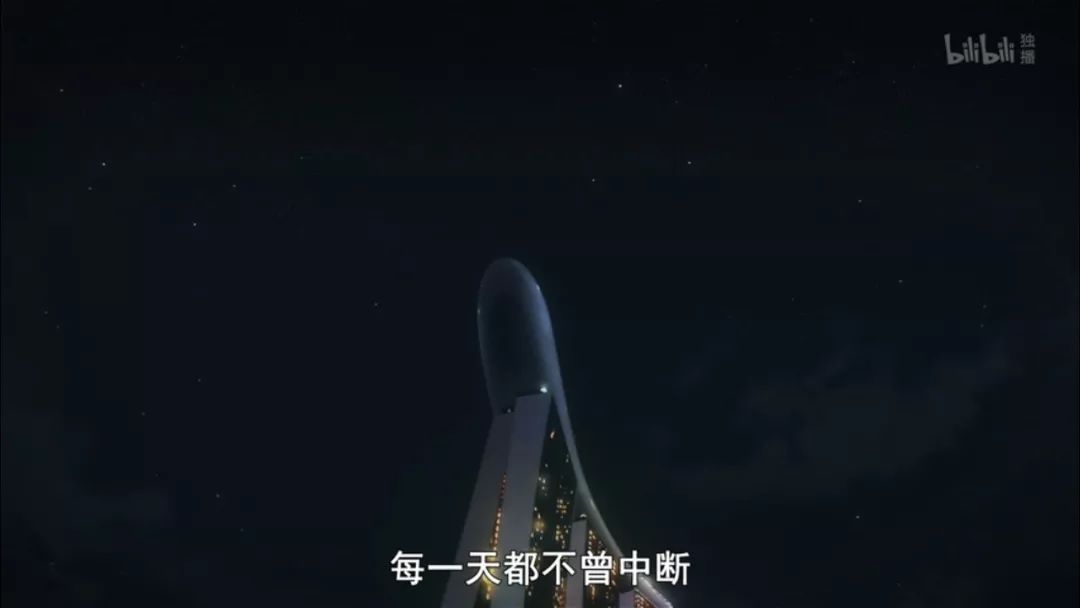
2
1935年瞿秋白被捕,在绝笔之一《多余的话》中,他写道:“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
”上个月写南霁云,我曾感到,这日常小事般的就义过程远比高呼某口号而令人动容。革命家在最后时刻往往不会以自我解剖代替慷慨悲歌,而曾任最高领导人的瞿最后却说了一句无助于点缀自己红色光辉的不合时宜的话。
对此我们可以联想到金圣叹“花生米与豆干同嚼有火腿味”、李斯“复牵黄犬逐狡兔”等往事,这些在悲壮气氛中的小小转折总让后来人沉吟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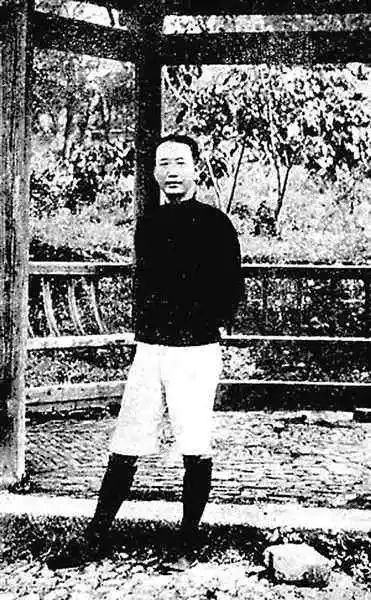
继而我们又可以联想到一些更大角度的转折。《硫磺岛的来信》里中村狮童演的中尉看不起懦弱的二宫和也,绑上炸弹要和美军的坦克同归于尽,最后坦克没有来,睡了一觉后他不想死了决定投降。
同一时期看的《驴得水》中,周铁男面对特派员的枪口大义凛然,可偏偏子弹没打中,在重获新生的庆幸被再度顶上的枪口击溃之时,血性男儿也便跪下了。

《金阁寺》里沟口放了一把火之后,
“取出小刀和用手绢包裹着的镇静药药瓶,向谷底扔去”,
打消了自杀
的执着念头,放弃了
极致的
美的殉道者身份,心想:
我要活下去。《庆祝无意义》里阿兰想象中的母亲跳河自杀,却又在害死了施救者之后产生了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的想法,阿兰把这作为他诞生的一个契机,当然这也是隐喻的一部分。

如此种种,或许正如某条评论所说,“
很多事情睡一觉就会改变想法的
”,在每一个死亡和救赎来临的时刻
。
2.5
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缘故,由历史的小小转折中可以窥见,瞿秋白或是金圣叹都并非以斗士为第一志愿,即便是李斯也未必不想归去。抛去“没有必要的躯壳”,瞿秋白应是一名生活家,“
他真正热爱的不是权力,不是革命中尔虞我诈的斗争和血腥杀戮,他唯爱生活,投身革命是听说共产主义能解救大众的生活
”。
只是这些真诚流露未免也必然太晚。
在勇者与懦夫的逆转中,与一些观点不谋而合的是,我时常想,许多英雄的产生恐怕是由于精准致命的第一枪,让人来不及考虑取舍,便“
一去不回
”。但凡“一鼓作气”后接着“再鼓”“三鼓”,但凡有所迟疑,便有了屈辱生长的土壤。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令人长忆汪义士。

2.75
若是说前面形象的转折甚至是崩坏都是本身隐藏的真实面的主动或被动暴露,那么沟口与阿兰母亲的“
活下去
”是心灵深处的呼喊吗?“
我本来想这个冬日就去死的,可最近拿到一套鼠灰色细条纹的麻质和服,是适合夏
天穿的和服,所以我还是先活到夏天吧。
”写出这句话的自杀5次的人也是想要活下去的吗?大抵是因为,选择“生”的时候是真的想要“生”,最后的“死”也是真的想要“死”罢。(段正淳:我对你们每个人都是真心的。
当然,这些作品有各自的主旨,甚至大相径庭,从中寻找相似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再创作,我想说的实际上是,人间的一切突变都不足为奇,大概就如三岛由纪夫当时所写,都是深思熟虑的对自己意志的报复行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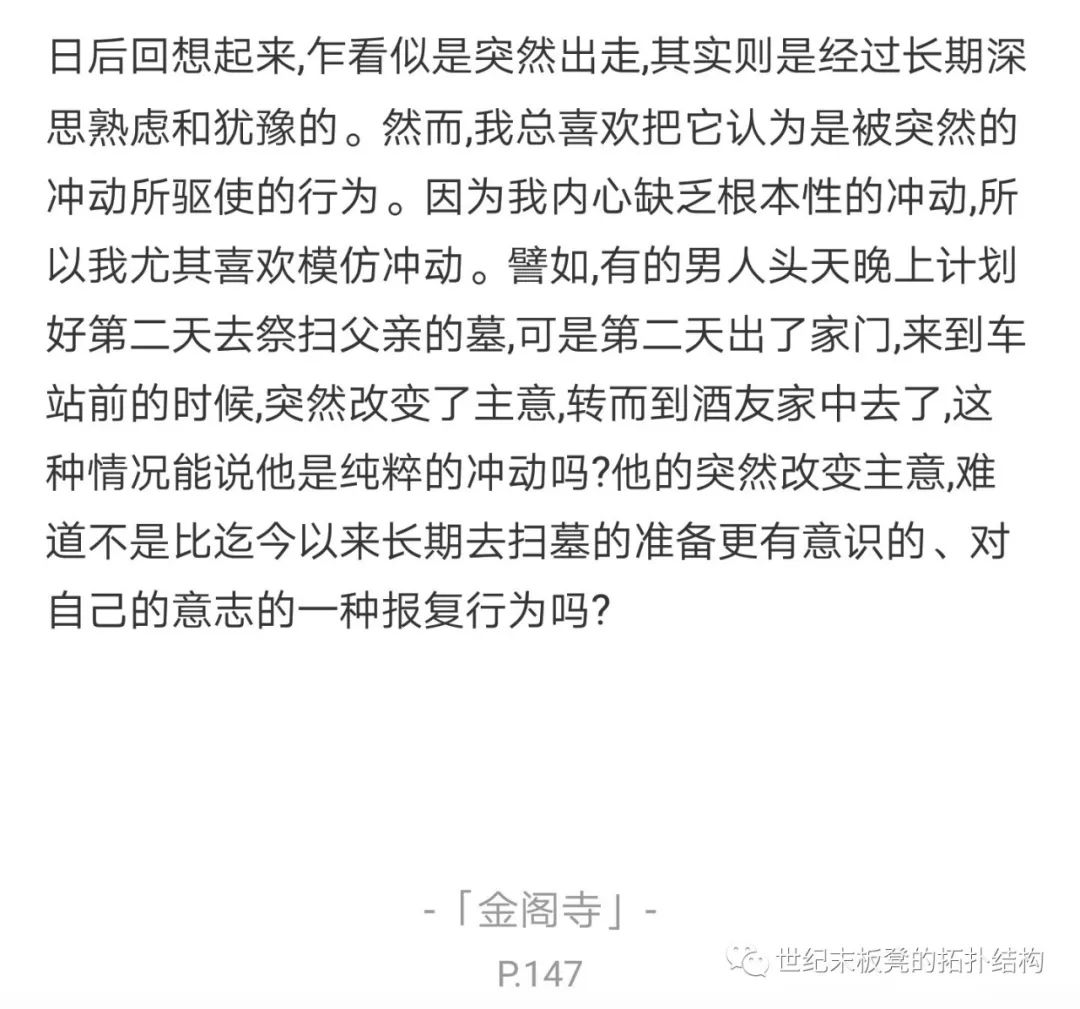
3
上月
提到中岛美雪的《ローリング(Rollin' Age)》,处于后革命时代的打工青年借由60年代末街头的黑白相片想起逝去的年代,却因生得太晚而没有亲身参与而遗憾,如今身处世界的荒野,宁愿乱拨电话恶作剧也做不到与亲友诉说寂寞。
1927年7月,在
大革命失败后笼罩全国的消沉气氛中,
朱自清写下了《荷塘月色》,直言“这几天心里颇不平静”,但坦承“Petty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看清自己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也不隐藏对投机假装“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