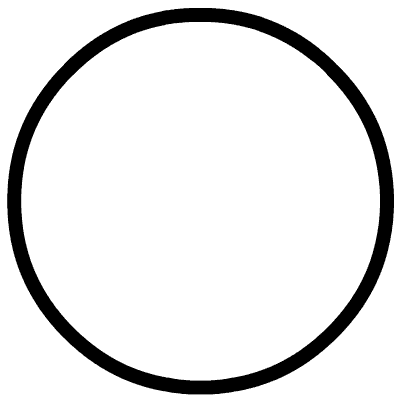 Hi,这里有提升你幸福感的一切
Hi,这里有提升你幸福感的一切

前段时间我和你说过,我想写关于“
我是如何成为女权主义者,以及我对女权主义看法
”的文章。
我所说的
“女权主义”,也就是平权主义,支持男女权利、机会平等,反对性别刻板印象。
用“女”字是因为当下我们身处男权社会,女性权益更难得到保障,所以在话语上加以强调,希望唤起更多人对女性获得平等权利的重视,减少性别歧视。
而当我动笔写时,我发现,要解释“我是如何成为女权主义者”,
我无法回避掉自己曾经是一个重度厌女症患者,以及现在也依然在和体内残存的厌女症做斗争的现实。
你没看错,从童年到青春期,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是一个厌女症。
我努力隐藏和否定自身的女性倾向,不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希望被当成男性来对待和接纳。
教会我厌女症的是轻视女性的男权社会。用《厌女》一书中的话说,在这样的社会里,“
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
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换个更加浅显的说法,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
有一次都没有庆幸过没生为女人的男人吗?有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生为女人吃了亏的女人吗?
”
我成为女权主义者、追求男女平权的过程,也是对自身厌女症从不自知到自觉自省、与之斗争的过程。
接下来我就要坦白我的
厌女症病史
了。

1
“你一点都没有姑娘家的样子。”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小小的我就会想,什么叫“姑娘家的样子”?
我慢慢意识到,
大人们口中“姑娘家的样子”大概是:
乖巧斯文、安静整洁有收拾。最重要的一条是听话顺从。
但
小时候的我并不符合这个标准
——我
爱跑爱跳
、坐不住、胆子大、爬树翻墙一把好手,
粗心冒失、丢三落四、不爱收拾
,课桌一团乱,不注意干净,衣服才穿一天就脏了。
我童年住在大院里,除了我之外,其他家都是小男孩。我跟他们一起玩,我妈就会对我说,“你怎么老往外跑?”我如果说可是谁谁家的小朋友也在外面玩,我妈会说,“你是女孩子呀,斯文一点不好吗?”
在玩耍中,如果爸妈在,他们常会以
“危险”
为由禁止我玩某些游戏,“不要爬那么高/跑那么远……”但和我同龄的那些小男生们收到的来自家长的
警告和管教则更少,指导和鼓励更多
。
儿时的我就会困惑,为什么同样都是在外玩,男生们听到的更多是
“小男孩淘气点正常,受点伤没事的,还能练皮实点。”
而我听到的更多是:
“女孩子不要那么匪(fei,读3声,是我家那的方言,有淘气不听话的意思)啊。”

2
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
自己生活的世界里,好像有一本女生行为指南,上面写满了女生就该如何如何。
而我不想要被这个指南规范,也没兴趣做
家长口中的“淑女”。
我只想痛痛快快去玩、去跑、去跳,有和男孩一样的自由。
不过诚实地说,那时我还没有仔细想,
为什么这指南针对女生,而对男生没有这样的要求。
我只是觉得
被这么要求,作为女生,我不舒服、不自在。
上小学时,有个关系不错的女生找我吐槽说,她爸妈重男轻女,什么好的,都给她弟弟。
我是家里唯一的小孩,但听她说完后,还是忍不住问我妈,你是不是原本比较想要男孩?我妈很诚实地告诉我,“你爸爸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我那时会比较希望怀的是个男孩。不过,你爸他是想要丫头的。”
她很爱我,但她心中依然有传宗接代的想法。当时还是小孩子的我,因着朴素的公平观觉得很委屈,“男孩、女孩不都是人嘛,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多年后,我看到了一本家谱,家里的长辈告诉我,过去女人是不登记在家谱上面的。“不过现在上面有你的名字哦。” 我在阳光下,翻开那本家谱,此前密密麻麻都是男性名字,最近这一两代才出现了女性名,
我突然对社会学家们说的那个词“被消失的女性”有了很直观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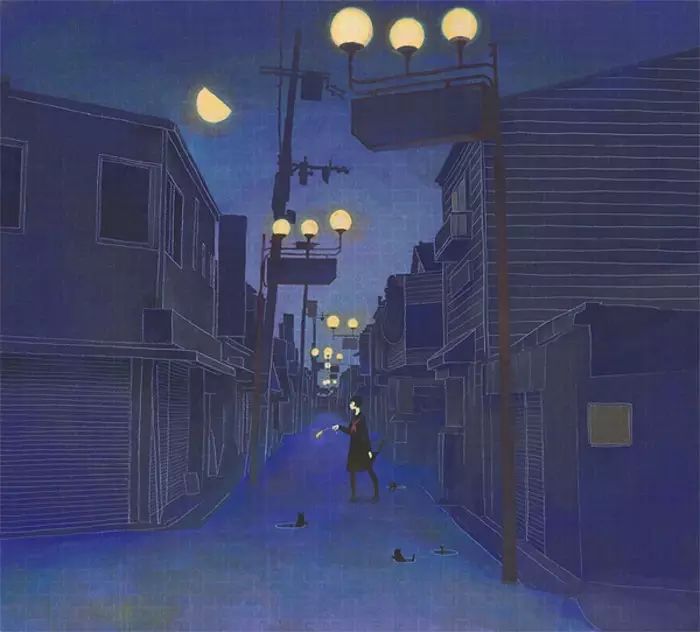
3
初中时,我步入青春期,女性生理特征开始显现,月经初潮、乳房发育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女生。
但我周围环境传递给我的信息是,
月经也好,身体发育也好,都有种见不得人的意味。
因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
很有默契地回避掉了生理教育这一课
。同龄女生们提到月经,都用“那个”隐晦带过,那些身体发育较早的女生则往往成为男生私下讨论的话题。
班上男生会用投票方式做女生身材颜值的排行榜。我第一次听同学告诉我这事,我有种被评判、审视的感觉,我觉得不安全、被冒犯,但当时我又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只会说“男生真无聊。”
后来学习性别理论,我才知道,这叫“
男性凝视
”,在
男权社会下,女性是被看者,是客体,男性是观看者,是主体。
我觉得不舒服是因为这种“凝视”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是自上而下的压迫。
我讨厌被当成“他者”来打量,也不想被“女生就该怎样”的标准来要求。
更诚实一点说,
在“不愿意被标准要求”的背后,还藏着隐秘的自卑和自傲
——我一方面觉得作为女生,自己不够好看、整洁、斯文。另一方面又觉得“我和那些娇气、爱哭、不能吃苦的
女生
才不一样呢”,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对女性的认知其实很狭隘,完全来自于男权社会灌输给我的刻板印象。
 4
4
这一切导致某个午后,读初中的我站在镜子前,凝视镜中的自己,默默决定:
反正我没法按你们对女生的要求演好一个女生,那我就自觉脱离于女生队伍。
于是我的整个青春
期都是以
假小子
形象度过,我
剪短发,穿男装小码,
颜色不是黑灰就是蓝绿,
买了辆男士赛车,骑得飞快。
高中时,我和女同学下晚自习后,手拉手并排骑车回家,第二天就有看到我们背影的同学找她八卦
,“我看到你昨晚和男生牵手啦,那男生是谁啊?”
这种被人错认成男生的事时有发生,而我也乐得被人当成男生。我现在分析当时的心态,大概是
想通过把自己“男性化”而获得和男性一样
的自由
,更少评判、压制和约束。
虽然我的厌女症使得我不愿正视和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但我还是很喜欢和女生一起玩,只是带着一种“我和你们不一样”的心态。
前段时间我在豆瓣上看到有个姑娘表述自己在厌女症时期对女生的感觉“类似于贾宝玉看姊妹,属于旁观,
但‘没有跟他们是同类’的自觉
”。我觉得这句话也准确说出了我当时的状态,觉得
自己是“骑士”,其他女生是“公主”。
那时,我也有关系不错的男生朋友,在我内心,
我
希望他们把我看成和他们是一样的人。
我会让男生朋友和我以“兄弟”相称。
我上大学后,有次和高中时的男性朋友见面,
对方还习惯性地喊我喊“哥哥”
。他身旁的女友很惊诧。现在想来,自己也觉得有点好笑。
初中时,有一次和男生有冲突,
我跟对方说“放学后别走,我们打一架”。
我当时潜意识里,大概觉得男生之间有矛盾大多打架解决。而我把自己也看成是男生中的一员,自然地,
我会选“男人式”的约架。

5
那时的我一边刻意压抑自身让人联想起女生的性格和喜好,比如敏感、同理心强、爱美,一边努力表现自己大大咧咧、什么都无所谓的“男生”一面。
压抑到什么程度?
初中时,有次语文老师对我说,“你的文字很温柔、细腻,你的内心很女生啊。”我的第一反应是惊吓,回过神后立刻反驳,
“我哪里女生了?”
“可是你的文字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呀。”老师笑着说。
“我手写我心”的文字的确很难隐藏一个人的内心属性,而
我连文字泄漏我有女性化的一面都感到恐慌。
我后来读到《厌女》这本书对厌女症的阐述时,深有共鸣:
“男人的厌女症,是对他者的歧视和侮辱。因为男人不必担心会成为女人,所以可以放心地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歧视。
可是女人呢?对于女人,厌女症是对自身的厌恶。
”
“
但女人也有可能不讲厌女症作为自我厌恶来体验,其方式就是把自己当做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
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
被男人当做 ‘名誉男人’来对待
,即成为 ‘女强人’的策略。另一种是自动退出 “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 ‘丑女’政策。”
我当时采取的方法算是这两种策略的混合,
一方面,努力学习,因为我知道好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我赢得他人的尊重,从而获得
被男人当做 “名誉男人”对待的待遇,另
一方面从外表上偏离社会对女性穿着打扮的要求,以避免被当成女性评判
。
6

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当时我做的一切,其实是一种徒劳的、掩耳盗铃式的努力。
虽然我有交到一些尊重我的男性朋友,
但整个男性群体并不会因为我的假小子形象,就不对我评头论足,不把我的名字写在女生颜值排行榜里。
父母也并不会因为我的男性化打扮,而减少对我的约束。
他们照样限制我出门,如果发现
有男生往我家里打电话,或是翻到男生给我的情书,往往会归结于我的错,告诫我“不该
招惹男生”,
如果我顶嘴,则会被教育:
“他怎么不找别人,就找你?”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
多年后,我才知道有个词叫“荡妇羞辱”,这是一种专门针对女性的言语暴力,用“荡妇”这个空泛又莫须有的罪名指责女性。
7
最可笑的是,我其实也没有真的成功骗过自己。我虽然行为举止、着装打扮上像男生靠拢,但我就真的逃脱因为厌女症而自我厌恶的诅咒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