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小刚的新片《芳华》中,战争戏只占了6分钟的时长。但在电影的新版海报上,原本解放鞋与舞鞋交织的青骢物语几乎清一色地换成了由黄轩饰演的男主角在越战战场上身着戎装凝目伫立的仓皇一幕。它意味着某种深刻的寓意——
《芳华》是关于毁灭的。
战争与死亡无疑是最能直接引领毁灭的存在,但关于这条线的叙事只是《芳华》的细枝末节。电影的野心不在于此,《芳华》试图描述一种讳莫如深却又厄运高悬的宿命感。电影创作者别出机杼地把它揉进了舞台帘幕的后背、姑娘衣袂的褶皱和革命青年荡漾的春心中,然后等待着美好支离破碎、悲情接踵而至。这种无从具象更无从逃离的宿命感可化用德国作家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的那个名句来形容:
“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的一代人,他们尽管躲过了时代巨轮的直接碾压,但还是在其中逝尽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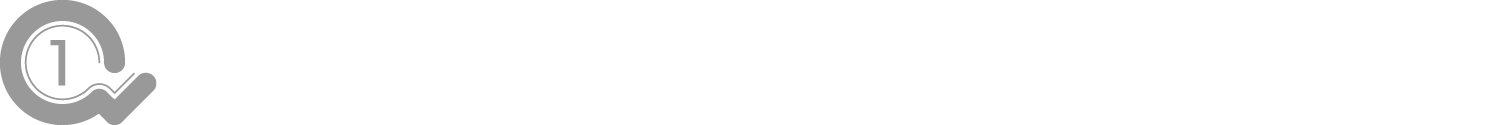
“前十年、顺流而下;后十年、逆流而上”
很多人说这部经历了撤档风波而今涛头弄潮的革命文艺青春怀旧片是冯小刚迄今为止最好的电影,这听上去是在赞誉,细品之下却也五味杂陈。

文化评论家解玺璋曾如此论述在国内市场运作和电影生产方面得心应手的冯小刚及他个人色彩浓郁的“贺岁”代表作:“他的影片不再是艺术家通过重新介入社会历史、去除俗常之蔽以恢复洞见和更高的人生关怀、重建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仅仅是按照一纸订单生产的‘年货’。在这里,艺术家对社会历史作自由超越的冲动,被电影投资人冷静而精确的算计所取代。”
曾经的冯小刚热衷于唯资本和票房马首是瞻,纠结于“非科班”身份的他更多是通过颠覆艺术叙事态度、使电影恢复娱乐和审美本性的方式获取世俗与行业的承认。在那时,作为局外人的冯小刚是不理会人们从艺术角度对其作品进行的批评的。直到有一天他发现钱挣够了,整个社会可供拍摄严肃认真电影的环境却突然皮之不存,已经身为圈内大咖的名导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然后冯小刚开始拍“现实题材”,开始常怀悲悯,开始批行业、骂观众——
他说《芳华》这样的类型片国内近十年内没有、往后也不会太多,他还告诉许知远,一名导演能拍出《美国往事》这样的片子才算是实现了天命。

就在使命与责任的一张一弛之间,善于避重就轻的冯小刚完成了从“前十年、顺流而下”到“后十年、逆流而上”的转换。轮到《芳华》这里,专业评论的两极分化凸显了时代对于这位溯洄者的观察。褒扬意见肯定了创作者在话语权受限的前提下寄予其间的隐性反讽,而“不买账”的观点则担忧一贯讨巧有余而力度不足的冯小刚会把《芳华》拍成叶京的那部《记得少年那首歌》。后者的症结与其说是技法与表述上的混乱,毋宁说是对于特定年代苦难记忆与虚无题旨的迷醉美化与刻意回避。虽然《芳华》里不加节制的明媚有冲淡反诘的嫌疑,但冯小刚毕竟不是叶京,如果说电影中很难看到陈词滥调之外的历史观,笔者倒更愿意将其归结为审查制度使然。过于指责《芳华》不伦不类或者隔靴搔痒的批评者,至少应当看到电影对于“人的立场”的坚守,至于对中国社会而言更真实和更深刻的表达,绝非银幕工作者们可毕其功于一役的份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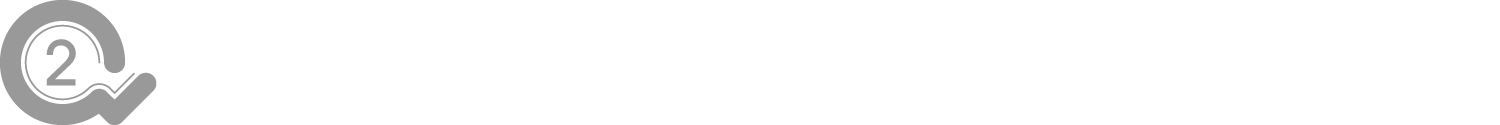
革命年代的爱情
《芳华》里最惊艳的角色不是那些爱红妆更爱武装的文艺女兵,而是由黄轩饰演的男主角
刘峰
。至少在电影版的《芳华》里,刘峰这个角色对故事本身的承载要比严歌苓原著小说的权重更大。从《黄金时代》里的骆
宾基、《推拿》里的小马到《妖猫传》里的白居易,黄轩极为擅长处理沉静感与爆发力的两相交错。这个双鱼座男演员的优雅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与生俱来的优雅——多愁善感、无功利心、不流于俗,以及《芳华》中
体现在男主角潜意识里的“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美好愿景。

有评论形容刘峰这个“活雷锋”活得太不真实:他吃煮破了的饺子;自学手艺替女兵修表;主动帮结婚的战友做沙发;甚至把上大学的机会都拱手让人。文工团的女兵们恐怕也是这么看刘峰的——
一个无缺憾、无死角的楷模;一个完美的、大写的人。
然而,故事最畸形的一面也就在这里:在女兵们看来,一个举世罕见的好人是尤其不应犯浑的,他甚至都没有表达正当情欲的权利。所以刘峰只是表露了对心仪者
林丁丁
的爱慕之情,就把对方吓坏了,然后被开除、被审查、被流放。
当一种饱含虚假寄托的幻想不允许被戳破,实际上最畸形的不是被压抑和定义的对象,而是那些掩耳盗铃和粉饰太平的人。后者希望宏大叙事周而复始,人性压抑如初,血统论永不褪色,所以她们只期待一个理想主义者从始至终都扭曲成她们想象中的理想主义应有的样子。
理想主义者总是被误解成迷醉于幻梦和愿景的存在,可那恰恰是伪理想主义者们的惯用筹码。
刘峰是混在伪理想主义者营帐中的真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追求切实具体的东西,比如爱情。正是在刘峰朝林丁丁迈出那一步之后,他才对存在于朝夕相伴的革命战友之间的塑料情谊恍然大悟——原来她们从来没把自己当作“自己人”,原来她们的“双标”这么严重,
从尚武到拜金、从集体到个人之间的辩证逻辑,道理都在她们那边。

革命年代的告白与试探,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发觉乌托邦现实马脚的最佳路径。
正所谓“以大煽情揭破大煽情、以春光明媚对抗春光明媚”,一个遍布虚无教旨的年代中理想的错位和重置,从中作梗的不是命运的无常流转,而是名不副实的时代精神与集体主义本身。在那个面色红润、高歌猛进、赶英超美的豪情万丈的历史纵深处,正埋葬着那些被遗忘、被忽略的无法进入叙事的渺小个体原本肆意昂扬的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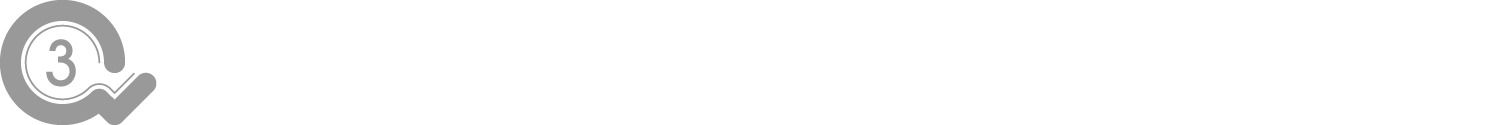
撕裂与幻灭
仍有评论认为冯小刚在对《芳华》的处理上犯了左右逢源的老毛病,即所谓个人回望与庄严审视在同部作品中彼此抵消,原本足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题旨一再作浅尝辄止的尴尬收场。但我倒认为,即便抛开影片延迟公映的版本是否较本初的版本有所剪辑,电影的主旨也已经在不动声色的矛盾与拉扯中逻辑尽显:
它前半部分有多美好,后半部分就有多残酷。
因此,不必苛责创作者没有做到知无不言和言无不尽,重要的是观众能在电影构建的那些恍如隔世的对比后面领悟多少。

在《芳华》中,关于乌托邦的假大空、理想国的无处安放、隐秘心事的星流云散、集体对簇拥者的分门别类,以及个体精神关于先验主义的质疑与出逃,这一切压抑与迸发的铺陈都与男主人公刘峰如影随形。文革中的刘峰是所有人靠拢的模范,但他的劳模动力并不出自对信仰的极端狂热,电影开篇的镜头语言可以佐证这一点:热心肠的刘峰帮战友捉猪,与大街上迎面走来的抬着领袖像的游行队伍狭路相逢,他的逆流而过已经给出了暗示。
刘峰在革命浪潮中的“不违和”,恰好是因为集体主义将他乐于奉献的自发精神定义为“正常”
;而当历史的玩笑余韵殆尽,刘峰的纯粹与坚持就只剩下“不合时宜”这一桩形容。
理想主义者刘峰之所以能在人生前段感受到岁月静好,只因他现实步伐的一丝不苟正与象征世界的整齐有序无缝重合。
实际上在大多数人那里,乌托邦只是一场浮夸跃进的人为建构,那里面充斥着无法整合的复杂经验。对于刘峰来说,他对于未来的想象以及人际关系的期待并不复杂,他认为文工团战友之间应该互相关爱、帮助、学习、进步;他认为无怨无悔地对一个人好,她就一定能感受到自己的真诚;他甚至认为红旗下阴暗的角落也可以通过自我的隐忍与牺牲完成恰如其分的填补。
刘峰并没有错,只不过是单纯与善良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刘峰一直将林丁丁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不止是林丁丁,文工团里的所有人以及这里的一切存在在刘峰眼中都是彼岸之花的现实绽放。所以刘峰无怨无悔地牺牲奉献,永远是冲锋在前的姿态。
直到他向暗恋之人投去一次拥抱,才发现一个理想主义者孤苦伶仃的后脊背简直凉入骨髓。
对于林丁丁来说,“活雷锋”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符号,它的光芒四射在现实主义者的字典里是有
时效性的
——在革命浪潮中,她比刘峰更认可那个平滑完整、不含杂质的虚假映射;在浪潮退散后,她亦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面对社会转型与个人前途上“姓社姓资”的拷问。
林丁丁们和刘峰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性善论者”,而刘峰是“性善者”。
“性善论者”只是颂扬“人性善”,她们号召真正的“性善者”完成对于乌托邦的献祭,而这个过程丝毫不妨碍她们实践“人性恶”。被侮辱与被伤害的
何小萍
最先发现了歌舞升平的现实场里遍布着的残忍与不公正,直到被刘峰善待,她才头一遭感受到了人性的温度。所以当刘峰遭遇文工团的排挤,何小萍宁愿被那个曾经试图融入的集体彻底放逐,毅然决然地步其后尘。

在“流氓事件”发生后,何小萍去男兵宿舍帮刘峰整理衣物,她看到后者将他那满载荣誉的奖品用箱子腾了出来,准备扔掉。两人接下来的这段看似漫不经心的对话尤为值得注意:
何小萍: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刘峰:
你帮我把这箱东西扔了。
何小萍:
都还能用呢!
刘峰:
印上字了怎么用啊?
何小萍:
都是好字啊!
刘峰:
那你拿去吧,只要你不嫌难看。
曾经的标准与期许,早已在现实境遇虚假而深刻的背离之下皮开肉
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时的刘峰已经心中有数。相
比后来的身患残疾,精神家园的轰然破碎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才是更重的挫伤。一个最纯粹的灵魂,遭遇了最污秽的谎言。
剧团里的现世安稳和战场上的慷慨赴死对于刘峰来说全都是伪命题,只因悲怆与荒诞的始作俑者正是覆盖了他青春底色的整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