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把登山当作一场男人的战争。在他的价值坐标里,一场对大自然史诗般的宣战,被界定为一个男人身体内的挣扎。
文 / 张文政
编辑 / 卜昌炯
张梁又要上路了。
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他被淹没在熙熙攘攘的面签队伍里。看起来,他跟周围的人没什么区别,但他自己知道,他跟那些人不一样。
隔着珠江,张梁望见江对岸被雾霾包围的广州塔和几幢高楼,到处是灰蒙蒙一片,塔下是零星亮着的路灯。
这是他熟悉的世界,却总觉得陌生。相反,那些已排进日程的雪山、大洋,倒更像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在远方召唤他。
从2004年登顶8201米的卓奥友峰,到2015年登顶8091米的安纳普尔纳峰,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他已经征服了12座。从南北极地,到加勒比海、百慕大和大西洋,张梁享受这种在工作单位特批的假期到处闯的状态,尽管在这些无人之境,没有文明社会的繁华、光鲜与现代化,有的只是单调而无垠的颜色、疾速流转的云雾、陡峭的冰壁、巨大的冰裂缝。
偶尔,还能遇到过往探险者被风化的躯体——每年都有人从各国赶来,为勘探自然、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或视之为是对人性的考验和磨练。壮观的风景下,暗藏着极大的危险。
这天是2016年11月16日,52岁的张梁为几天后的环球航海计划来到广州办理签证。在不适宜攀登高海拔雪山的季节——北半球的冬天,他决定随帆船队到地球另一端去航海。
起点设在地中海,张梁和船队将从直布罗陀海峡出西班牙,穿越大西洋到达巴西里约,然后到南非好望角,最后进入印度洋北上回到中国香港,计划用时近3个月。其间,张梁会去登南极洲的最高峰文森峰。“这些难度不大,只是概念。”张梁对《博客天下》说,听起来这于他像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短期三五年内,张梁说自己会继续在探险领域“玩儿”。高海拔攀登、环球航海、马拉松、热带雨林漂流、水下深潜……这些是他定义的“大活动”,而这样的大活动排满了他明年的日程。
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年,张梁不缺钱,缺的只是让生命泛起波澜。自从2000年前后,他和知名企业家王石一起踏上登山之途,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路上多变的气候、复杂的地势、滑坠和雪崩的危险,都没有阻止他的脚步。
虽然已过知天命的年龄,他仍不断在现代都市与古老雪山两个世界间穿梭。身边人对他说“梁哥,别爬了,年龄不小了”,他听了心里头骂,“我去他的,我还是一个小伙子,你们怎么能这样想呢,什么差不多就行了,是你们这帮人心态有问题”。他一向严峻的面孔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如果说一开始张梁还带有不甘平凡的情愫,现在,每年的高海拔攀登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不再像早期那样觉得新鲜、刺激,“登顶了也没特别的感觉,不会太激动,只想照完相马上下去,活着下去”,但不妨碍他换座山再来一次。
对张梁而言,高山是一门人生必修课,训练他的体能和处变不惊的精神力量。他喜欢“跟自己较劲儿”,连看电影也要“审慎”选择,伤感的不看,觉得会消磨意志。
登山十余年,张梁真正开始面对并思索死亡始于6年前。那是2010年5月,张梁攀登有着“魔鬼峰”之称、海拔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登顶后队伍下撤时陷入慌乱,各自逃命,最终中国队有3人遇难。
“好像跟个噩梦一样,觉得怎么昨天还在一起,今天就没了。”接受媒体采访,他无法完整回忆在山上的整个过程,“全部是七零八落的片断。”但他始终记得一个画面:遇难者之一的李斌在失去意识前向他大声呼喊,说“梁哥,我们明年还一起爬雪山”。
“我说‘好,坚持,坚强点,不要放弃’,那时我还想通过这种方式鼓励他。”张梁回忆。
夏尔巴人向导人数配给出了岔子,加上经验能力不足,全队找不到下撤路线,各自分散自救,在高寒低氧环境下很快体力不支。“在那种恶劣环境下,你心里再定,死亡还是在等候。”张梁感觉到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哆嗦,无法控制,最后在一个夏尔巴人搀扶下,才回到距离峰顶最近的3号营地(突击营地)。
张梁说自己“死”过4次。除2010年在道拉吉里峰遇险外,2012年攀登马卡鲁峰“差点被干掉”,2013年攀登干城章嘉峰,12人登顶,下撤途中死了5个,2014年攀登迦舒布鲁木姆Ⅱ峰也是险象环生。

▵2013年5月20日,张梁在世界第三高峰海拔8586米的干城章嘉峰峰顶展示中国国旗
每次谈到自己及他人经历的这些死亡时,他有一种近乎残酷的冷峻。“遇到这些事,他说‘正常吧’,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不真诚,也不是没有感情,一方面可能有那种看开了的感觉,另一点是,张梁这个人本质上是很内敛的,感情的东西放在心里,很深。”一位熟悉他的深圳媒体人告诉《博客天下》。
张梁的回应是:“即使到后来,我也不会有情感的波动。当你对高海拔攀登有了充分了解,就知道在死神面前人是多么渺小,你不可能会再像平常一样思考这些。你唯一要考虑的是在那种环境下尽可能保持清醒,并一定要意识到一切只能靠自己。高海拔攀登,你首先就应该确认自己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力。”
在山上张梁见过了太多,无论自然对生命的吞噬,还是被环境逼出的残酷的人性真实。有的在山上受到一些刺激就慌乱、胆怯,“自己先把自己吓死了”;有的碰到状况,出于本能撇下其他人独自逃命;有的无法理性评估客观条件和身体状况,遇险不敢果断下撤,非要做“强弩之末”……他说这些都是极难用现实生活的寻常话语去如实描述和储存的。
张梁也曾萌发过放弃的念头。2014年,他第一次登安纳普尔纳峰,由于天气忽然生变,在离顶峰仅300米的地方,张梁理智选择放弃。没想到下撤时再度出现意外,3个夏尔巴人发生滑坠,张梁当机立断组织队员把人救了回来,死神又一次与他们擦身而过。当天张梁对着录像机,一度说出“我喜欢登山,但更热爱生活。再见,安纳普尔纳,再见,雪山”的话。
但高海拔登山的“瘾”,他戒不掉。一年后,他重新踏上征程。“我一定每时每刻都会是‘在路上’的状态,绝不会躺在床上等死……等真爬不动了、跑不动了,我可能开着房车周游世界,就这样,不回头的,一定不回头的,走到哪儿死到哪儿就算了。”
在登山界,有“14+2”的说法,即登顶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外加徒步南北极。这是一些人的终极梦想。如今,张梁就差两座雪山就全部完成了。另外,他还登顶了七大洲最高峰中的4座。
他把登山当作一场男人的战争。“我很享受这个能给生理、心理以及视觉带来无与伦比的冲击的过程……这样的磨练让我有了一种超然,有了豁达。”在他的价值坐标里,一场对大自然史诗般的宣战,却被界定为一个普通中国男人身体内的挣扎。
性格上的特质使张梁更自我、独立,不光是因为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还有他粗犷的面庞和说话时透出的某种笃定,陌生人见他,会误以为他曾当过兵。
“走远一点,尽量离家远一点,不想一辈子都待在石家庄。”抱着这种想法,1986年大学毕业后,张梁主动选择分配到深圳的中国农业银行,成了一名普通信贷员。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要每天步行数公里去见客户,工作生活平平淡淡。头一年过年回老家,他穿了一款白色纯棉套装,宽上衣、窄裤脚,还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像那个时代的港台明星”——在登山之前,他通常以这种方式来释放内心的冲动。
1999年到2000年,张梁开始慢慢涉足户外运动。策源地是万科周刊搞的一个游山玩水的论坛,户外爱好者在这里相互熟识,张梁也在那时候结交了王石等同好。如今户外运动在深圳如火如荼,可在当年,张梁、王石们踏入的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郊野岭,要“带着砍刀”开路,到了山顶立马掏出背包里的啤酒,喝上一整晚,第二天下山,常常如此。
起初攀登高海拔山峰,张梁自己筹措经费,好友王石也会支持,假期要用工龄假和周末拼凑起来争取,上山心无旁骛,下了山回到单位依然像个普通职员面对客户。后来登了几年,张梁也不再需要上班打卡,但只要一回到单位,一切如昨,“我就是普通人啊”。唯一不同的是,他成了农行的形象代言人,“各个场合都会被用来宣传”。
在十几年的好友马啸眼中,张梁从没变过,只是更加阳光了,成熟却不世故,他给自己立下3个原则:大酒不喝,应酬酒不喝,只跟朋友喝。“官场上的那种我从来不参加。”
在朋友眼里,张梁嗜酒,遇着性情中人会贪杯。与歌手汪峰在KTV碰杯,他说喜欢汪峰的歌;和哥们儿、《新周刊》社长孙冕在大理喝酒,“喝高了就开始朗诵诗歌”。
现实中张梁和各种圈子打交道,在登山界小有名气。他没有经纪人,也很少接商业广告,甚至不习惯摄影师为他精心安排的造型照。
“我不喜欢他们拍的那些照片,那不是我。他们非要拍得干干净净,我说那你还不如用一张登山那个状态的,这样才能让人感受到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现在西装革履的,多难受啊,我特怕化妆,还要化妆拍。”
有不少经纪公司找到张梁,希望包装他。曾经一个香港的经纪公司造访,拿出一整套方案,“他们想(把我)包装成国际的,而不是中国的”。张梁不喜欢,认为没必要。他觉得那是爬完最后两座8000米以上雪山和七大洲里剩下的3座最高峰之后的事,那时他将是世界上第二个、中国第一个完成“14+7+2”的人。
感觉一切只是时间问题。他不急,也不刻意,认为不过是玩儿而已,何必慌张。“我什么都玩儿,我不属于那种把登山看得太重的那种人。”他说。
近年,他看到国内有几个玩命追逐“14+2”的人,觉得很难理解,“我非常不赞同这样的一些行为,他们连工作也没有,没有其他的爱好,就把这个当做唯一的人生目标,他们就想靠这个一炮成名,目的性非常明显。”
如果说登山意味着某种精神上的探索,是为了超脱世俗,那在张梁眼里,把登顶14座高峰当作唯一人生目标的人似乎重新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泥沼。
张梁毫不留情讽刺的,还有那些想靠登山、跑马拉松去炫耀的人,“花了好几千块钱去另一座城市跑一趟(马拉松),跟我去笔架山跑一趟效果是一样的,我就一个人、一瓶水,所以,中国人有时太浮躁了”。
张梁不买车、不买房、不炒股,觉得人死带不走,都是负累。他讨厌在酒桌上听身边人讨论房价股价。“房价又涨了,他受不了,股票跌了,他也受不了,天天都是,在哪儿都是这样。”他在国外看到还有人用着砖头式的手机,感慨国人“精神上跟不上去,一切都是胡扯”。
他已经是一个24岁孩子的父亲了。儿子现在日本留学,两人很少交流,“他都要把我拉黑了”。某种程度上,儿子继承了他的独立和孤僻。儿子高考那天,张梁在山上,填报志愿他也不问。到了大学,儿子和他当年一样,不去上课,只一个人看书,觉得那些课程“听了难受”,只做想做的事。
坐在楼下咖啡馆的外面,张梁只向店员要了一杯白开水。前一晚喝的一场“大酒”让他至今感到晕眩。他问采访会不会进行到太晚,因为他打算傍晚用跑步来让自己更清醒,还是笔架山,还是一个人、一瓶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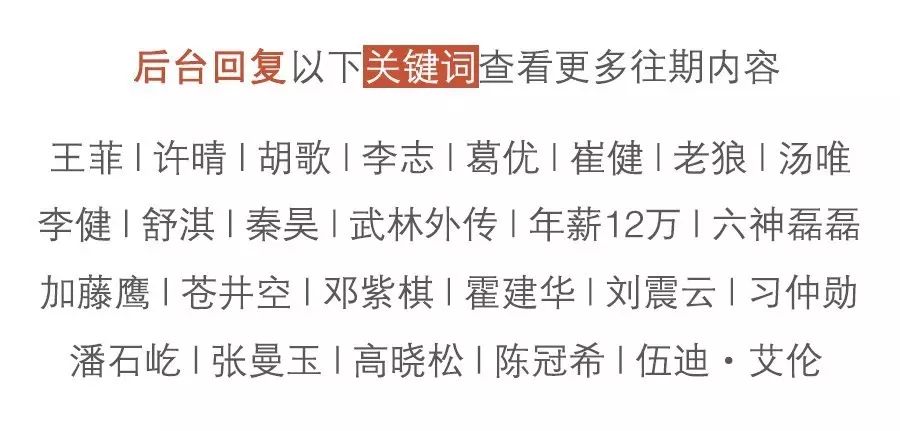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32期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