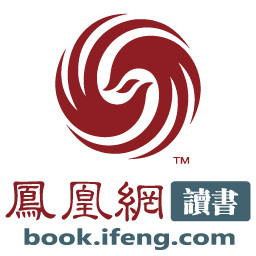图片来自网络
有些人收获得比较早。但是收获得早的可能很快就耗尽或者不行了,后面收获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好。
“不着急”
是我对人生的感悟。
>>>
人人都有故事
这是
有故事的人
发表的第
773
个作品
作者:张军
原标题: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
“你经历了很多人生之后,你的厚积薄发,一定会有一天得到回报,不管早与晚,只要你努力了。”
生活在别处
我出生在一个江边的县城——云阳,在重庆东部挨着奉节与巫山,离长江三峡很近。
整个童年,我都在搬家。父亲先是在南充,接着搬到和母亲一起,然后去了文教局,再到进修学校,最后又进了党校,所以小时候我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玩伴,这点像王小帅导演。王小帅从小就是这样,他生在上海,一个月后去了贵阳,去了贵阳之后又搬到武汉,然后又考上中央美院附中。他就像个流浪者一样,但我的漂泊是在城市之间,不在全国,基本上是搬家。
变动的生活使得我今后不太依附于别人,跟某些人很难形成同党,有一个圈子或者联盟。这是计划经济下中国人的无奈,在很多
60
后家庭中的孩子都有,不光是我。
1973
年,
5
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看了第一场电影,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戏。那个年代电影很少,《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八个样板戏,文革以后这些电影就不放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电影是露天放映的,在广场上支起非常大的银幕,全城的小孩都挤在那看。有些小孩去的比较早,就带个木头小板凳在那占座,下午就去了天还没黑。后来就是在房子里面看电影了,我记得当时的电影院非常神奇。不是木头的凳子,是水泥墩子,之后慢慢发展才有了翻盖的木板座椅。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个小孩都觉得吃瓜子是一种享受,电影院是允许嗑瓜子的。小时候经常买不到电影票,影院已经卖光了,很多卖瓜子的早上就会提前去订票。堆一堆瓜子在山上,然后树棍上插上一根像竹签一样的东西,票就支那上面,你买一斤瓜子才肯把这张票卖给你,特别有意思。
现在我还爱吃瓜子,常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外面摊子上买,挺邪门的。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机,只要有电影就去看,一部电影即使看过两遍三遍也还要去。父亲是教语文的,每次都会布置一个任务,让我看完这部电影回去再复述一下故事。真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上电影学院还要学这个,写故事梗概,我小时候就写过这个嘛。父亲的培训让我对电影和文字有了一定的敏锐度。
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电影,但是电影院的票已经卖完了。父亲认识电影院的人,就把我带到电影院的放映室,在楼上放电影的
孔那儿看完了电影。我跟其它小朋友不太一样,小朋友每次看电影都会特别当真,“啊,那个演员肯定死了,那个人被坏人打死了,演坏人一点都不好,就会倒在那被子弹打死,英雄也会被打死。”他们会觉得那个人真死了,吵半天。
我也会被故事吸引,为英雄牺牲与敌人的死感到惊恐。但一看,电影是用机器投影到屏幕上的,装的是胶片拷贝。我知道这是假的,虚构的东西我从不会去当真。但我也愿意投入到剧情很真的感情当中,所以我从小就知道那是虚构编制出来的东西,也喜欢去看。
走自己的路
中学之后我变得十分叛逆,
1982
年我上初三,有一次母亲偷看了我的日记,姨妈说
:
“你妈为什么不能看你日记?”我站在床上暴跳如雷,“你们看我的日记是在侵犯我的人权。”我不知道谁教我的,没有任何人。县里面选举,爸爸妈妈去投票,回来我就质疑他们,母亲讲领导画好圈他们说投谁就投谁。我说这是不对的,选举应该你信任谁才选谁,我觉得这些质疑或者说怀疑精神融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我愿意相信最爱我的外婆告诉我,我们村那个地主是好人,而不愿意相信课本上描述的地主有多可怕有多坏。我不相信老师,不相信《**日报》,不相信课本,选择相信我的外婆,相信一个人说的话。我很庆幸亲人能够教给我人性的课程,让我在那么早没有被洗脑。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以至于后来成为一个写作者。
上高中后我桌子上摆的都是语文和小说,数理化从不看,几乎一到晚自习就逃课去看电影。坐在教室里往窗户上看老师有没有在外面,“蹭”的一下就跑了。我当年写的日记现在还记得,第二天被班主任训话,“你昨天晚上去哪了,带着班上的女同学去电影院看电影?”老师就以为我跟女同学有什么事,根本不知道我是喜欢男生的。
爸爸妈妈给我买豆浆油条的钱,过年的压岁钱,我都省下来看电影,不吃就饿着。那时哥哥也喜欢文学,他就把所有的钱省下来去买《三国》的小人书。但他没有我幸运,他是按照妈妈的要求去读书、去考大学,
16
岁就考上大学。
1983
年,我在《大众电影》杂志上发表人生的第一部影评《充满希望的一年》,把当时全国那些电影厂上一年生产的所有电影做了一个点评,那一年我念高一。同年在《中学生》杂志上也发表了文章,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碰巧当时刘晓庆发表了自传《我的路》,看到后我更加坚定要走自己的路,成为一个作家。
1985
年,我非常渴望离开家乡云阳。有一天在学校橱窗上,看到《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启示,便汇款过去买了招生简章。后来听当地的人说,这里从没有人有过这么大胆,敢独自去报考电影学院。我看了招生简章后发现北京太远,碰巧武汉也有考点,便从云阳坐船到宜昌,再从宜昌导汽车到武汉去了。
我是家里的反面教材,父母不同意去,我就偷偷翻开母亲的被子,偷了她们的钱当路费,但不够。
1983
年我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文,当时的稿费是二十几块钱。河北滦平县叫王兆梅的一个女孩给我写信,她是一个农村人,已经中学毕业了,在做花卉养殖业,希望我能够支持她的事业。
我不顾家人的反对也不管她是否是骗子,便把钱寄给了女孩。但是没想到王兆梅在
1984
年成为了那个时代像今天马云一样的创业成功榜样,被各种媒体报道和表彰。所以还有一笔钱是我考学时向王兆梅求助,她给寄来的,九几年的时候王兆梅患癌症去世了。
武汉是我人生中去的第一个大城市,但是那一年武汉考点只有导演专业没有编剧。在小县城里完全没有接触过相关知识,根本不懂什么是导演,也没有人辅助我任何东西。
回来后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是这样,真正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是十年以后。那一年王小帅、娄烨都考上了,我跟他们是同一年考的,后来又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要是考上了就真成了同学。
我总觉得我不是这儿的人
没考上大学后,我参加了县里的招工考试,来到小镇放电影。那时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感情,迫切想离开。当时逃离只有考学呀,我不逃离就没法离开那,跟我的初恋男友在一起。
1987
年我还参加了中戏考试,专业通过但文化没过。
1995
年,在我发表的小说《盆地少年》的开头,写下这样一首小诗
:
"
你羽翼未丰,便注定不能飞翔,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天空。
"
川东这种险峻地方的生活让我渴望离开,希望有一个改变,不想在穷山恶水的地方待着。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使我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极度困扰,虽然说山水那么的美,但人并不想在那待着。
你不要以为生活在高寒地、雪山上的人就喜欢待那,可能生活非常恶劣。不在那的人会有想象,觉得在山峡生活的人多好,那个时候你会看到视野的狭隘。后来章明导演给我讲述他在巫山,每次出门看到灯火通明的船,从巫山县城往宜昌方向走出三峡的时候,他都渴望被带走。
我总觉得我不是这儿的人,有一天我一定会离开这里,不会在这生活一辈子。这是我很小时就说过的一句话。
在电影公司一待就是九年,这九年放了多少部电影我也没算过,春节一天要放八场,平时每天至少放三场。《红高粱》、《老井》、《边城》,商业片《峨眉飞盗》、《世界奇案的最后线索》、《危险的蜜月旅行》这些都是我当时放过的影片。
八十年代的商业片和现在的网剧很像,烂片多也有好片,《红高粱》、《黑炮事件》、《芙蓉镇》……那个年代的好电影也都放过。但八十年代和现在又不同,那个年代的产量低,电影上映一段时间后观众没有什么看了就会放复印片,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再早一点就是把前两年放过的电影再拿回来放,补缺嘛,
1989
年把
1980
年前后的电影都有放过。
当时也有国外引进的电影,日本的、德国的、甚至台湾的电影。胡慧中演的《欢颜》,主题曲叫《橄榄树》,大林宣彦导演的《姊妹坡》也是在我工作的电影院放过,《海街日记》跟它很像
,
非常动人。还有得了戛纳金棕榈奖的文德斯导演的电影《德克萨斯州的巴黎》,引进的时候要配上中国人的配音。
黑白电视的年代电视剧还不是电影的竞争对手,电影很火,在那放电影时经常有人“走后门”找我买票,但到了彩色电视普及以后电影受到的冲击太大。
1990
年电视剧《渴望》播出后简直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
1990
年到
1997
年,这七年是中国电影非常衰弱的时候,电影院就不行了,开始转型放录像。我在
1991
年就不再放电影,领导派我去录像厅了。
九十年代初有很多的录像,香港引进的大部分都支持录像带,它可以连看两场甚至三场,夜场通宵呀什么都有。记得当时还有林彪儿子林立果选美的一个八集录像片,不是电视剧电影哦,是专门为录像厅拍的,那种当时超级火。蔡明演过一部录像片叫《地下俱乐部》,也是专门给录像厅拍的。
录像带是彩色封面,很诱惑人,但不是情色而是暴力的封面。当然录像厅外面也有贴海报吸引人,比电影院演得要暴力和情色得多,所以录像厅非常火爆。
放电影的时候同事都在干别的事,织毛衣、打麻将呀之类的,因为电影放出之后就可以歇会儿,但我一直都在看。把光调整以后我就看那个情节,我会想每一遍看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有没有新的发现。银幕上画幅信息还是很多的,你不能看一遍就知道它的前后左右是什么,没有那么确切,所以我喜欢多看几遍。
在小镇工作一年以后,上街去贴海报,他们远远的就喊我“程电影”。
背水一战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去做这个逃离,最终在
1995
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成功地逃离出来。
1993
年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下,我执意办了停薪留职回去准备这个考试。再次参加北京电影学院招生考试,已经
27
岁,那年电影学院招生对年龄是有规定的,要求在
28
岁以下,我只能选择背水一战。
1995
年在老乡邱永波的帮助下,我住进了他的宿舍,在北京电影学院进行备考。邱永波是贾樟柯班上的班长,宿舍里面有四个人,邱永波、顾峥(贾樟柯的文学策划)、王宏伟(饰演小武)、邹健。但是宿舍里只有四张床,住不下。晚上睡觉的时候邱永波在两张床中间搭一个折叠椅,他睡折叠椅,让我睡他的床备战考试。
那时候顾峥,王宏伟和贾樟柯成立了一个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准备拍一些学生作业短片,当时想找一个考生拍他考试的场景。然后顾峥就跟贾樟柯说他们屋里住着一个,最终贾樟柯找到了我。起床、刷牙、去看张榜、体检、考试……什么都拍。
我认识邱永波班上所有的同学,他们对我都特别好。顾峥骑着自行车从电影学院送我去中戏考试、口试紧张时贾樟柯站在旁边跟监考老师说,“我这个朋友非常不错。”老师让我放松好好考,郭小橹陪我去看的张榜……那一年我感觉所有的人都来帮我,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好像受到了老天爷的指令一样。当你真心实意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口试时,张献民老师让我高考后去巫山玩,当时他在拍《巫山云雨》,那是我第一次进剧组。但是这一年成绩还是不理想,文化分才考了
270
多分。据说当年是
320
的线,应该差
50
分,由于专业考试成绩不错,最终被破格录取了。我成了
1995
年这届唯一一个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就去电影学院上学的学生,到学校后录取通知书才被寄出。
在万州的码头上,我穿着印有北京电影学院的黑色
T
恤,那是备考时在北京买的,这一次我终于成为正式的学生了。走的当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送我,有画家、音乐家、诗人……我后来自己总结道
:
你经历了很多人生之后,你的厚积薄发,一定会有一天得到回报,不管早与晚,只要你努力了。
这是我对人生的一个信条,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努力了都不能实现人生愿望,我不认同。我认为只要你努力了你耕耘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只是有些人收获得比较早。但是收获得早的可能很快就耗尽或者不行了,后面收获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好。
“不着急”
是我对人生的感悟。
(
备注
:本文由
程青松口述,张军整理
)
责编:苏龄童
本文
版权归属
有故事的人,
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阅读更多故事,请关注
有故事的人
,ID:
ifeng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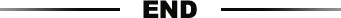

扫描或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
人人都有故事
有
|
故
|
事
|
的
|
人
投稿邮箱:
istory2016@163.com
合作邮箱:
sto
r
y@ifeng.com
主编:严彬(微信
larf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