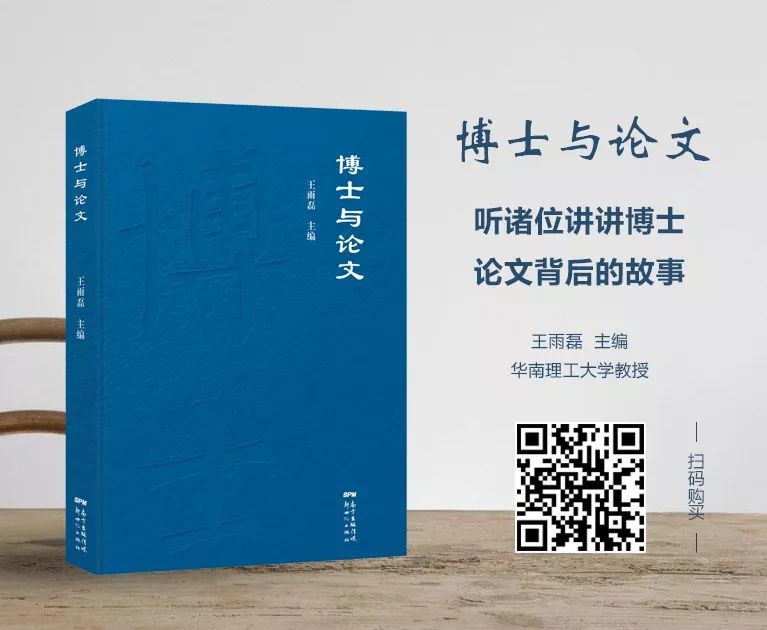潘光旦,
原名光亶,后改名为光旦,1899年8月13日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
本文系费孝通先生在1999年9月15日民盟中央、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共同召开的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张冠生根据录音整理。今天是潘光旦先生诞辰120周年,谨刊此文,纪念潘先生!
接到参加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通知,我就开始想该怎么讲,花了很多时间。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
在这个会上,怎么表达我的心情呢?
想了很多,也确实有很多话可以讲讲。
可是我来开会之前,我的女儿对我说:
不要讲得太激动,不要讲得太多。
我马上就到90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不宜太激动。
可是今天这个场合,要不激动很不容易。
我同潘先生的关系,在座的大概都知道。
我同他接触之多,关系之深,大概除了他的女儿之外就轮到我了。
从时间上看,我同潘先生的接触要比他有的女儿还要长一些。
小三出生之前,我已经和潘先生有接触了。
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时间是1930年之前,早于我来北京上学的时间。
后来,在清华大学,我和潘先生住得很近,是邻舍。
到了民族学院,住得更近了。
有一个时期,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一直在一起,可以说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联在一起,分不开了。
这一段历史很长,我要是放开讲,可以讲上半天。
今天只能少讲一点,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左起:潘光旦、费孝通夫人孟吟、费孝通
张祖道摄于1955年5月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
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人的差距也很清楚。
差在哪儿呢?
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
做法不同,看法不同。
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才能觉得过得去?
不是人家说你过得去,而是自己觉得过得去。
这一点,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差别很大。
潘先生这一代和我这一代就差得很远。
他是个好老师,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学到他的很多东西。
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
己,推己及人的己。
懂得什么叫做“己”,这个特点很厉害。
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
归根到底,要懂得这个字。
在社会上,人同别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有一个“己”字。
怎么对待自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是个“吾”,是“己”。
在英文里讲,是“self”,不是“me”,也不是“I”。
弄清楚这个“self”是怎么样,该怎么样,是个最基本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个问题了。
很多人倒是天天都在那里为自己想办法,做事情,但是他并不认识自己,不知道应当把自在什么地方。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很清楚。
他们对于怎么做人才对得起自己很清楚,对于推己及人立身处世也很清楚。
不是潘先生一个人,而是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这样。
他们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已,怎么才算对得起呢?
不是去争一个好的名誉,不是去追求一个好看的面子。
这是不难做到的。
可是要真正对得起自己,不是对付别人,这一点很难做到。
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我认为是好的。
怎么个好法,很难说清楚。
如果潘先生还在世的话,我又该去问他了。
在我和潘先生交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把他当成活字典。
我碰到不懂的问题,不去查字典,而是去问他。
假定他今天还在,我会问,这个“己”字典出在哪儿?
在儒家学说里边,这个世界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提出“推己及人”?
“吾日三省吾身”是要想什么?
人在社会上怎样塑造自己才对得起自己?
潘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过课,专门讲儒家的思想。
我那时候在研究院,不去上课,没有去听。
后来我想找到他讲课的时候别人记录下来的笔记。
新加坡上个朋友叫郑安仑,听过潘先生的课。
我要来了郑安仑(注:
1936年社会学系毕业
)的课堂笔记,可是他记得不清楚。
我后来想,其实不用去看潘先生讲了些什么,他在一生中就是那么去做的。
他一生的做人做事,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
他不光是讲,更重要的是在做。
他把儒家思想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了出来,体现了儒家主张的道理。
这个道理的关键在哪里?
我最近的一个想法,是觉得关键在于“己”字。
“己”是最关键、最根本的东西,是个核心。
决定一个人怎么对待人家的关键,是他怎么对待自己。
我从这个想法里想到了自己。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看人看我”,意思是讲我看人家怎么看我。
潘先生同我的一个不同,是他自己能清楚地看待自己。
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
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这个面子已经是个问题
了。
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
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
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孔子的社会思想的关键,我认为是推己及人。
自己觉得对的才去做,自己感觉到不对的、不舒服的,就不要那样去对待人家。
这是很基本的一点。
可是在现在的社会上,还不能说大家都是在这么做了。
潘先生一直是在这么做的,这使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差距。
我看人看我,我做到了,也写了文章。
可是我没有提出另一个题目:
我看我怎么看。
我还没有深入到这个“己”字,可潘先生已经做出来了。
不管上下左右,朋友也好,保姆也好,都说他好,是个好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怎么对人,知道推己及人。
他真正做到了推己及人。
一事当前,先想想,这样对人好不好呢?
那就先假定放在自己身上,体会一下心情。
我今天讲潘先生,主要先讲这一点。
我想这一点会得到大家的赞同,因此可以推广出去,促使更多的人这么去想,这么去做。
现在的社会上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做人的风气。
年轻的一代人好像找不到自己,自己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做。
要想找到自己,办法是要知道自己。
不能知己,就无从“推己”。
不能推己,如何“及人”?
儒家不光讲“推己及人”,而且讲“一以贯之”,潘先生是做到了的。
我想,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达到的境界,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现在,怎么做人的问题,学校里不讲,家里也不讲。
我们今天纪念潘先生因此很有意义。
怎么做人,他实际做了出来。
我作为学生,受潘先生的影响很深。
我的政治生命,学术生命,可以说和潘先生是分不开的。
我是跟着他走的。
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
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
在思考这个差距的过程中,我抓住了一个做人的问题,作为差距的关键。
我同上一代人的差距有多大,我正在想。
下一代人同我的差距有多大,也可以对照一下。
通过比较,就可以明白上一代人里边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家公认的好人。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
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
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受些启发,多用点脑筋,多懂得一点“己”字,也许就可以多懂得一点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有一种超越自己的力量。
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
这一点很了不起。
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
他没有怪毛泽东。
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
为什么呢?
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
因此不应该怪他。
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
这使潘先生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是尊重到底的。
他没有觉得自己冤,而是觉得毛泽东有很多苦衷没法子讲出来,也控制不住,最后演变成一场大的灾难。
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
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
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这一点我体会得到。
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
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关注《学术与社会》,在后台回复关键词“
石头
”,可以获取公号的所有文章。
《
为人师表
》摘选
【1】张杨波:我的十年大学从教心得
【2】宣朝庆:天地一沙鸥 ——我的从教经验浅谈
《
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
》摘选
【76】汪广龙:在无限困惑中寻找“控制感”
【77】侯庆斌:读史十年
【78】李怀印:我的求学经历与治史心得
《
读研指引
》摘选
【1】
怎样读研,才能不虚度未来三年?
【2】
致研一新生:这学期,一定要上好seminar!
【3】
再致研究生:毕业前,先掌握这五项基本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