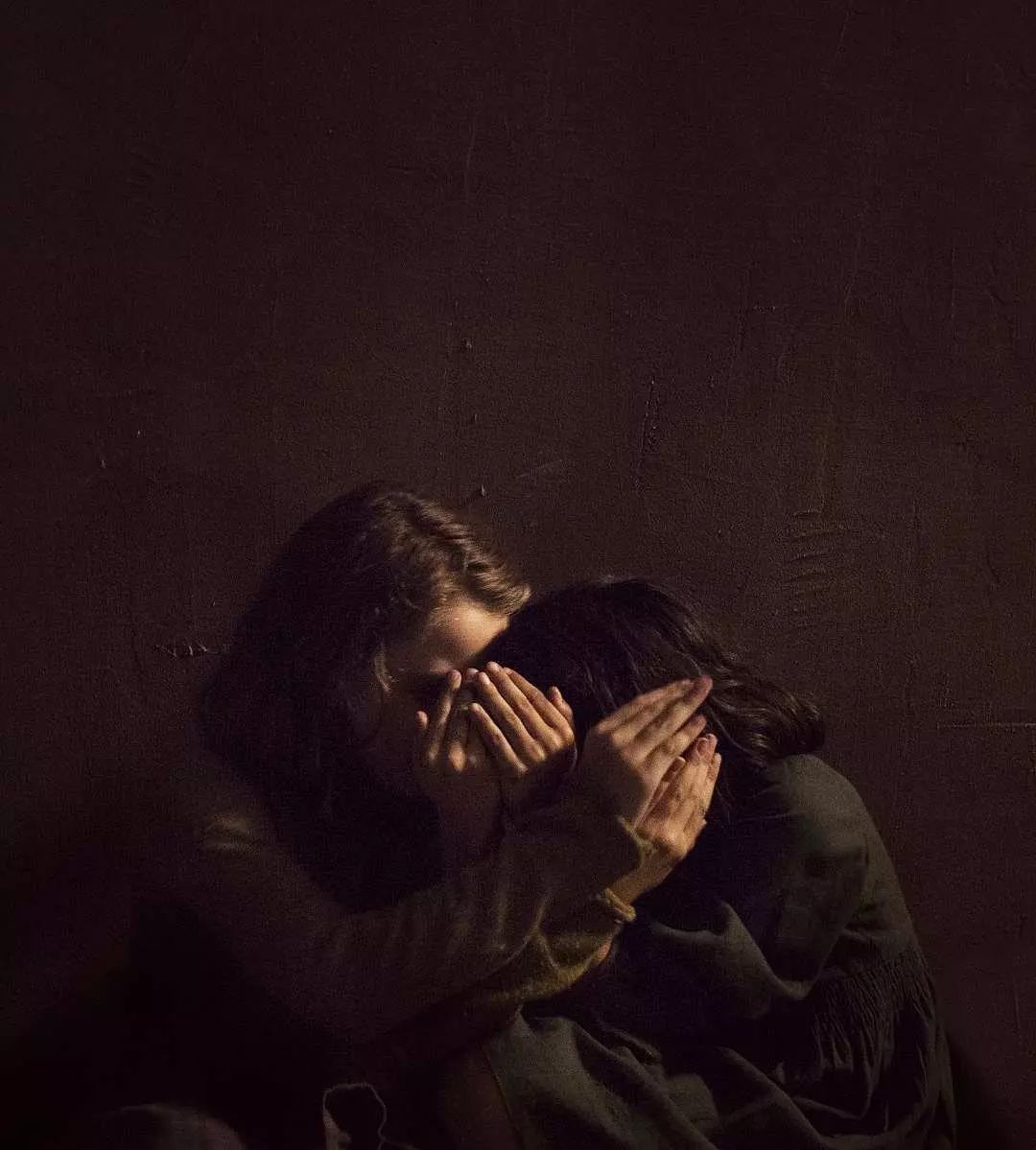
米兰达·裘丽的长篇《第一个坏人》
在北京的发布会之前,我和Madi见了一面。我们保持着工作上的零星联系,而社交软件给人的幻觉是即便几年没有见面却始终觉得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对方一部分的生活。然而米兰达的长篇出版,便不由郑重地觉得应该面对面见证一下彼此真实的存在。
我和Madi相识在大陆互联网初级阶段的黄金时代尾声。如今重新打开她与搭档Patrick的摄影项目My Little Dead Dick的主页,能够看到P对着空旷水域撒尿的照片。下面有两段有关他们照片的评论,巴黎东京宫(Palais de Tokyo)对他们照片的一句评价是“不无幽默地重温了沃克·埃文斯和南·戈丁的遗赠”(revisit, not without humour, the legacy of Walker Evans or Nan Goldin)。底下有另外一段短短的话,“My Little Dead Dick的照片日志从2006年夏天至2007年夏天——正好从他们遇见的第一天开始。之后P和M继续一起工作和生活直到2008年夏天分手,那一天,中国西部发生了大地震。”网站里的照片拍摄地点从澳门,香港,广州,到拉萨和尼泊尔,到厦门,直至最后Madi离开厦门去北京。
我在震后认识了Madi,这个摄影项目已经完全结束,而在此之前结束的还有她和爱米于2005年6月在广州一起创办的女性网络杂志After 17。以全女性的班底合力推广女性创作,关注女性成长。Madi在某次采访中提及这个杂志的精神灵感也来自于米兰达·裘丽创立自1995年的女性创作项目Joanie 4 Jackie(原名为Big Miss Moviola)。当时裘丽感受到主流独立电影总会有的厌女倾向,很受挫,受到盛行于俄勒冈波特兰的暴女事件启发,始终致力于身边团队建设。自1995年起的十年之间,裘丽鼓励女性创作者将自己的影像作品录像带寄给Joanie 4 Jackie项目,之后她们会收到“连锁信”——她们自己的作品和九部陌生人的作品剪辑在一起的录像带,并附有每位创作者写给其他女性的信件。在前网络时代,女性可以以这种方式看到其他人的影像创作,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独的存在。这个项目鼓励很多年轻女孩第一次拿起摄像机,给女性创作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等到这个项目结束时,有超过200位影像工作者参与制作了22盘录像带,之后这些影像在世界各地展出,从朋克俱乐部到MoMA美术馆。
而我在翻译米兰达·裘丽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之前没有看过她导演的电影或者参与的艺术项目,所以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这些小说轰炸了我的心。里面每个故事都既冷酷又温暖,极其悲伤和抒情地插科打诨,是真正的浪漫与迷人与孤独。所有出场的人物分不出是老人还是孩子,是男性还是女性,世界和情感都用另外一种方式进行了切割与划分。当时我和这本书的编辑曾经考虑过把作者名翻译成米兰达·七月,再三犹豫之后觉得任何形式上的古怪都是我们想要抛弃的。
2013年Madi和我一起做了一个有关米兰达·裘丽的对话给Vice中国。她对于裘丽是否能够被大陆读者接受始终怀着复杂的困惑,而我却以一种天真的确信和傲慢写过这样的话:
说到底这个世界上是不能缺少怪人的,而怪人们之间也有雷达,就好像是裹在人类皮肤里的外星人那样彼此打探。我对于怪人存着太多的宽容,各式各样的怪人都应该有他们存在的理由,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我只喜欢那些无害的怪人,那些善良的人。只有善良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无情才能打动我,其他的,无非是提醒着我,离这个世界更远一些才好。但是天真的不正确太难了,大部分的怪人都是形式化的假货,古怪也变成标签。而米兰达·裘丽的动人之处在于她的浑然天成,她是形式化的极其反面。

但其实我始终无法解释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提出的裘丽风格(著名的July-esque)是什么。针对米兰达·裘丽的小说阅读我有一个非常私人的提议——或许可以先打开她执导的第一部电影Me and You and Everyone We Know(台湾的译名是《爱情你我她》),裘丽自己扮演的女主人公在开头有一段冥想般的话:
好了,跟着我念,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勇敢……
(我想要勇敢)
很好,我想要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来生活。
裘丽的声音有种少年神经质的紧张和诙谐,不确定地踩在认真与玩笑的边界线上。她的声音,肢体语言,形象,语言,思维方式,甚至她的字迹都是一个奇妙的总和。所谓的裘丽风格在我看来或许是:我甚至可以辨别出她的字迹。她有意识地将字迹也融入各种漫不经心的表演艺术作品中,之后你会觉得她小说或者电影中所有人物,无论性别和年龄都在使用这样的字迹,并且都在用她的语气诵读所有的日常台词,不由要怀疑众多的人物也不过是裘丽过分庞大的自我在无处容身以后分裂成的附属品。以至于对我来说,她在Instagram上的一段慢动作小视频与她小说中的一段文字也仿佛是等同的,而任何定义都会成为局限。
《第一个坏人》翻译出版之后Madi再次问了我用中文转达裘丽风格是否会遇到障碍。在此之前我们聊了各自正在进行的工作。Madi正在筹备一个播客,年轻女孩相关主题,其中有一些新鲜有力的想法令我精神为之一振。After17停刊以后,2008年Madi和爱米曾经想要做一个新的电子刊物叫Here Comes 18,这个继承刊物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网站雏形,背景音乐是No More Little Girls。然而在那段时间里出现过很多独立音乐和摄影杂志,年轻人发表创作的渠道也很多样化,Madi质疑是否有继续做独立电子刊物的需要。这个疑虑或许存在很久,直到十年过去,一些以为会兴起的力量过早衰竭。
“你认识什么幽默的创作者吗?”Madi突然问我,这是她最近想要做的女性创作主题——啊真是一个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的问题,或者我很久没有考虑过幽默的意义和价值。我有几位在生活中非常好笑的朋友,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思维,行为或语言中,然而这些栩栩如生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似乎是被阻隔于创作之外。即便要我以旁观者的身份将这些我认为珍贵得不行的东西描述出来也做不到。仿佛那是无数个稍纵即逝的时刻,只存在于一个个不可复制的语言背景下。这种东西不是快乐,不是任何一种情感的表达,不会引起情绪的共振,不是喜剧,不是忙于制作笑声,不是悲伤痛苦的反义词,不是讥讽,要强调的是绝对绝对不是讥讽。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啊。它是基于相同的思考领域,视线范围,平等的认知,以及可被联结的情感而构成的。甚至需要绝对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其不机械化,但同时又是绝对的筛选,练习和控制的过程。
“像是《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那样吗?”
“唔……但是麦瑟尔夫人是个脱口秀演员,某种程度来说过分典型地强调好笑的价值了?”
“不过可以用来解释将自己的生活当作素材进行创作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同一段素材用不一样的表演方式会是失败和成功的本质差别。全部细节的精确性都是考验。”
“所以米兰达·裘丽算是吗?”
“啊,算!”
美剧《都市女孩》(Girls)的主创兼主演莉娜·邓纳姆(Lena Dunham)对《第一个坏人》的评价是:“So heartbreaking,so tender,so dirty,so funny。”心碎和温柔是裘丽风格中始终存在词语。这里的心碎区别于被碾压之后的破裂,甚至相较脆弱,反而有无畏的伤感。温柔也是出于一种庞大的明亮的爱,是绝对的暖色调。Dirty这个词语令我非常迟疑,仿佛任何一个现在有的中文词汇都无法解释邓纳姆在此处的定义。有哪个与性相关的中文形容词在某种语境下可以同时具有天真和调侃。裘丽在一次访谈中说她在写《第一个坏人》初期,在一个瑜伽教室里见到一位中年女人,她不由自主地开始幻想和这个陌生女性做爱的情景。小说里有大面积不可思议的性幻想,女主人公将所有本应作用于现实人际交往的情感努力都用于拓宽自我的情感边际,最后把自己变成了巨大的蓄水池。裘丽在与作家希拉·海蒂(Sheila Heti)的对话中说,她在写这些性幻想的时候常常不得不停下来自慰,她们也会交换和使用彼此的性幻想。“哈哈!别再自慰了,回去写小说!”海蒂笑着说。
《都市女孩》有一集,邓纳姆扮演的主人公汉娜和朋友洁莎一起从纽约去乡下看望洁莎的浪荡子父亲,她俩辗转交通工具,天气炎热,汉娜还遭遇着尿路感染的烦恼。在乡下洁莎与父亲剧烈冲突,汉娜莫名其妙在夜晚的郊外和刚刚成年的小男孩做爱,人物都一如既往地被卷在莫名其妙的情绪里。最后的早晨洁莎消失了,汉娜一个人背着包去小镇的车站转车回纽约,继续被炎热的天气和尿路感染折磨,在车站蹲下来小便,结尾的时候发出一声短促的疼痛的,“哦。”
一个可爱的烦恼的讨厌的尴尬的女孩。你,我,她。
以及最后一个词语,funny。在中文的转述中一定会缺失的funny。不是好笑,幽默,有趣,不完全是。更接近于不无好笑,不无幽默或者不无有趣,以此来减轻所有这些形容词的重量,因为这里有一种过分轻盈的东西让我甚至都不舍得用稍微确切一点的词语去损伤或压抑。
所以裘丽风格变成中文的过程中必然是有缺损的,我非常遗憾,却在脑子里浮现出裘丽领着我们在一个小区里郊游的画面——很难想象和裘丽去其他地方郊游,可能就是会在天气还不错的居民小区里——沿途风景突然卡帧,某一段变成低像素,失真,走音,但也不失好笑。
2014年米兰达·裘丽做了基于社交软件的项目Somebody。宣传语是“发短信差劲,打电话尴尬,写邮件老套”,所以她设计了一个非常裘丽风格的社交软件Somebody。简单来说,注册登录以后,你如果想发送信息给你的朋友,这条消息不会直接传递到她那里,而会传递到她附近同样使用这个软件的人的手机上,这位附近的陌生人如果点击接收,就得负责把这条信息传递给你的朋友,而且你还可以备注以什么样的语气,神态和姿势去传递这条信息。这个项目是与服装品牌MiuMiu合作的,之后拍摄成了一个10分钟短片,讲述了几段信息传递的故事。人类交流中的尴尬,错位,缺失因为信息无效率的传递和延误而被进一步放大,却没有一丁点讥讽,反而因此觉得所有人的孤独与快乐都以某种命运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以及被传递。
所以一旦想到在文化与语言的缝隙中消失或者跌损的东西,想到卡顿和无穷无尽的误解,一方面我能够想象米兰达·裘丽用她渗透式的语气说,“没事,没事,好了,好了,下面请跟我念,我要自由……”一方面却也认为米兰达·裘丽或者莉娜·邓纳姆是否能够被中国女孩接受不是那么重要或者了不起的事情。然而我的朋友们,正在此时,正在此地经历着一切的你们,你们的笑,你们的叹息,你们发出的那声短暂疼痛的“哦”才是最最重要的。
摘自《鲤·匿名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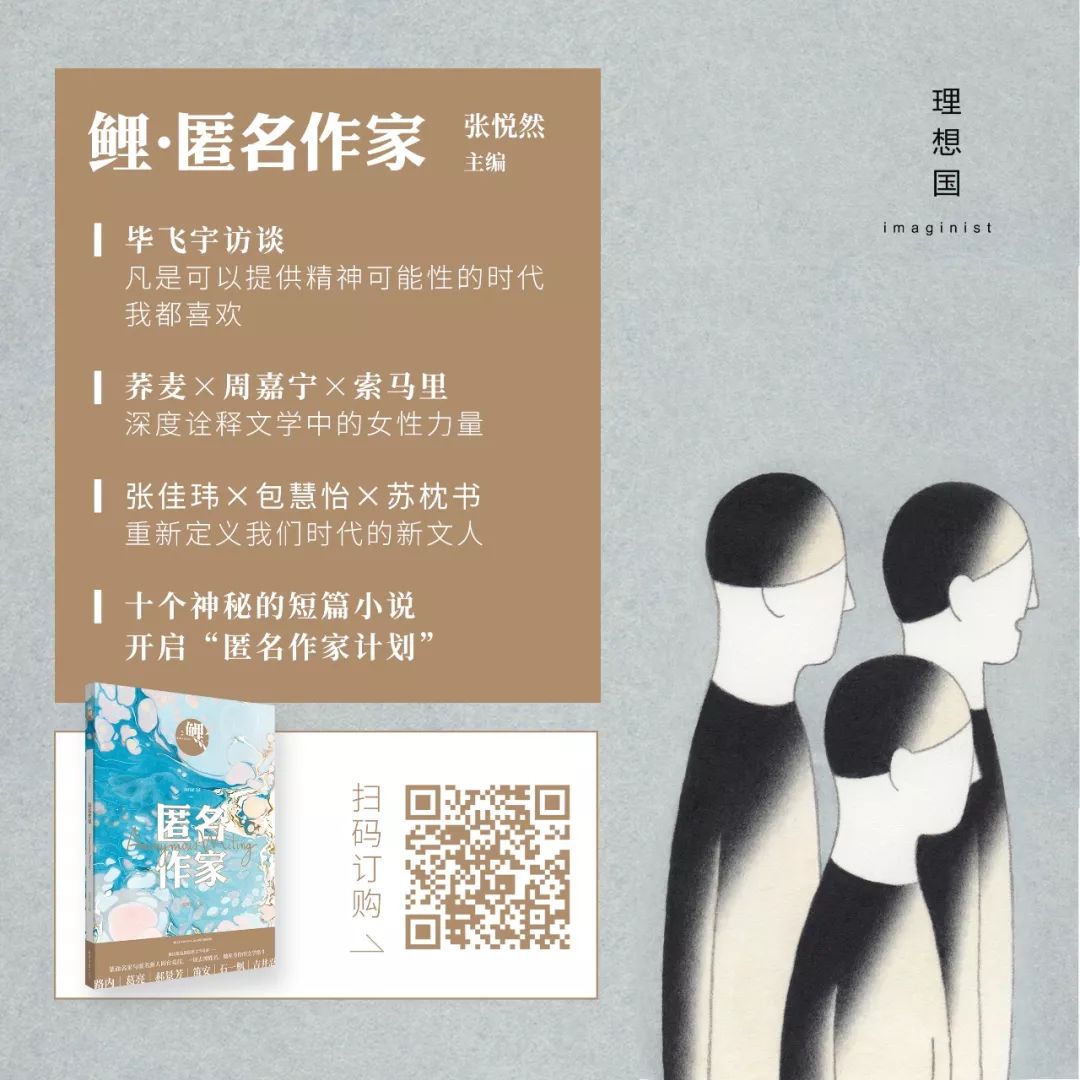
想快速了解当下中国小说写得最好的是哪些人?他们在思考什么?想明白为什么这篇小说好,而那篇不好?
张悦然主编、创刊已有十年的纯文学主题书系《鲤》,以专业的尺度,汇聚当下中国同时具备好读与思想性的三十位小说家。
一周十分钟,一堂开放的当代文学课。资深文学批评家随文伴读,犀利的评语、富于洞见的观察,教会读者理解最新的中文小说创作,学习如何判断一篇小说是好小说。
帮助匿名新人走向台前,与蒙面名家同台竞技,顺应“作品比作者流传得更久”的古老文学规则,抛开光环、名气、身份,让文学的归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