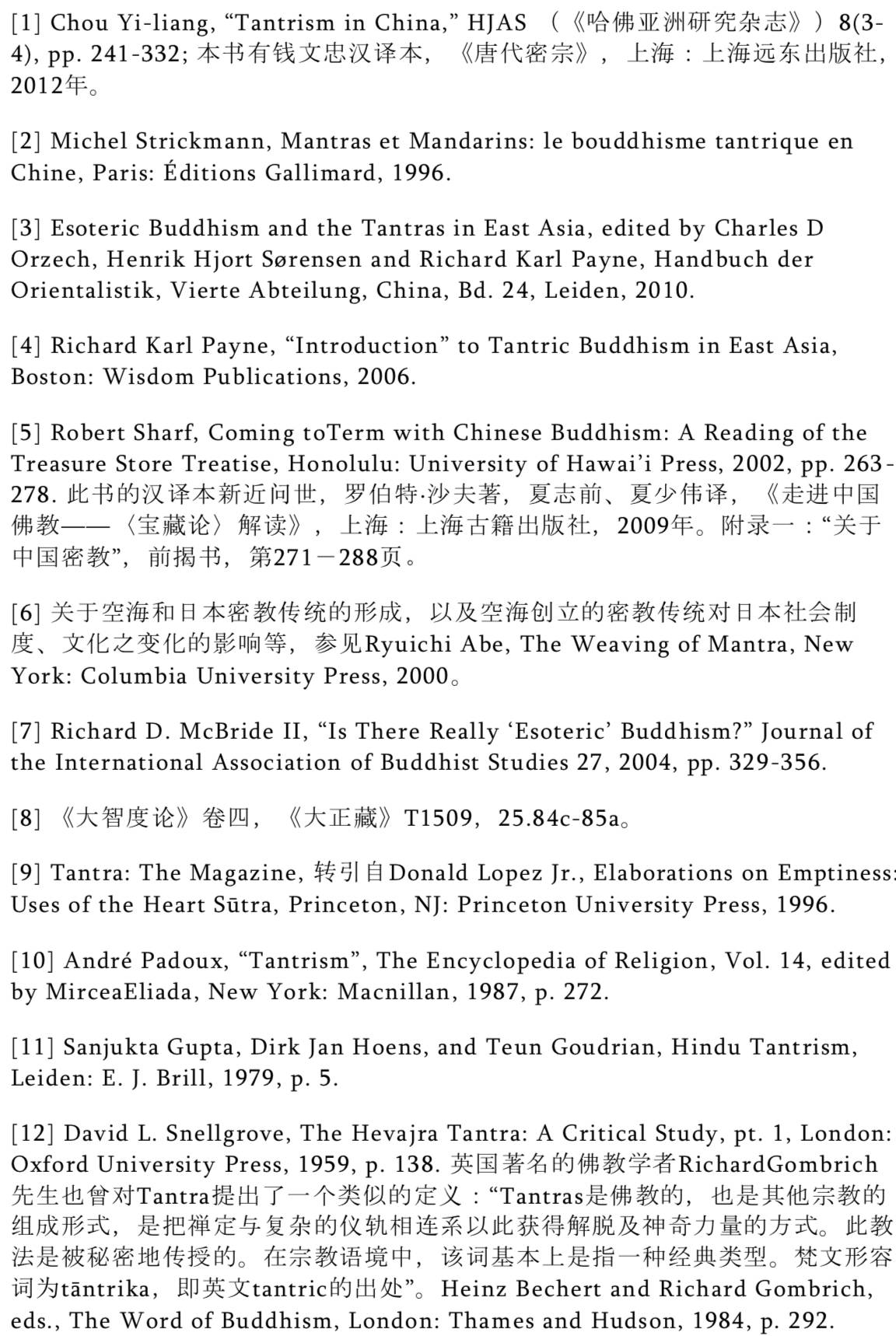封面图片:莫高窟(第465窟)。“密教”既是宗教学者的基本词汇,也是流行文化中带有“神圣性爱”标签的极具魅力之物。但作者认为,密教并不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辩证的范畴。如本雅明所说的“辩证的想象”,密教产生于西方和印度思想之间的投射和模仿,它同时发生在本土与他者之间,由幻想、恐惧、愿望的满足所构成,这个术语冲击了异域东方与当代西方的建构要害。
关于密教的定义、历史建构和象征意义的诠释和争论
作者:沈卫荣
来源:《何谓密教 : 关于密教的定义、修习、符号和历史的诠释与争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
一
上个世纪40年代中,中国学者周一良先生(1913-2001)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密教》(Tantrism in China),文章对汉传密教之创立者善无畏(657-735)、金刚智(671-741)和不空(705-774)三位高僧的传记作了翻译和介绍,为西方学者提供了以这三位人称“开元三大士”的汉传密教创始人的生平事迹为中心的唐代汉传密教的基本资料,从此成为西方汉传密教研究的奠基之作,也基本塑定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基本结构和研究范式。[1]
在以后的五、六十年间,汉传密教,或曰东亚密教的研究,虽不绝如缕,但于西方学界似并没有像印藏佛教(Indo-Tibetan Buddhism),特别是藏传密教研究(Tibetan Tantric Buddhist Studies)一样蓬勃地发展起来。西方学界对汉传密教研究更侧重于日本的密教传统,而非其本土唐代中国所传之密教。
迄今真正研究汉传密教的著名著作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部,如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 1942-1994)的《密咒和中国官话:中国的密乘佛教》,讨论的是汉传佛教中有类于“迷信”、“巫术”的偶像崇拜、火供、驱魔、魇胜等等内容。[2]
晚近,有一部卷帙浩繁的《东亚密乘佛教和怛特罗》作为荷兰莱顿Brill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手册”(HdO)的一种出版。这部作品集结了世界各国密乘佛教研究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东亚密乘佛教的历史及其文献、人物、修习、仪轨、特点等作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和探讨,凸显出今日国际学界之“东亚密教”研究的最新面貌,是一部值得常备案头的重要参考书,也是今后东亚密乘佛教研究的新起点。[3]
二
事实上,将“汉传密教”(Chinese Tantricism, Chinese Tantric Buddhism)或者“东亚密教”(East Asian Tanricism, Tantric Buddhism in East Asia)建构为一个可知的研究领域,至今依然受到严峻的挑战和质疑。
尽管佛教学者们普遍认为密宗佛教是东亚佛教的重要资源,它贯穿于整个东亚佛教史,故对密教如何于东亚被传播、发展、挪用、颠覆和阻断的历史都值得深入探究;可是,于国际佛教学界,主流的密乘佛教研究通常和印藏佛教和南亚宗教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东亚密教的研究从概念、术语,到学术话语、分类和历史谱系的建立和叙述,都有很多难以给予明确答案的问题。
甚至,连汉传密教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过也依然还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所以很难像藏传密教研究一样建立起一个成熟、规范的学术体系,形成一个自成一体、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领域。[4]
几年前,两位美国佛教学者、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Robert Sharf教授和美国夏威夷杨伯翰大学的Richard D. McBride II教授曾经分头撰文,再次提出和讨论了汉传密教或者东亚密教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一问题,而其结论则显然更倾向于否定。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汉传佛教中所说的“秘密教”不过是“大乘佛教”的另一个称呼而已,与今天学界所称的“密乘佛教”(Esoteric Buddhism,或者Tantric Buddhism)不是同一个概念,所谓汉传“密教”不过是后人演绎和人为建构出来的东西,它在历史上并没有真的存在过。
Sharf教授的文章“论密乘佛教”(On Esoteric Buddhism)是作为他的专著《理解汉传佛教:〈宝藏论〉解读》的附录发表的,[5] 其富有挑战意味的观点于国际佛教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争论,激发了学者们对汉传密教的进一步的兴趣、思考和研究。
Sharf在其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汉文文献中缺乏足够的证据说明汉传佛教中曾经有过密乘、或曰金刚乘教派的传承,“开元三大士”本身并没有自立宗派,他们所强调的密咒、陀罗尼的念诵、以及通过手印、壇城、祝祷诸佛菩萨、密修仪轨等获取诸佛神变、加持的修行等等,自一开始就是汉传佛教寺院修行的基本内容。
对于汉传密教的混淆实际上是因为受到了日本教派史学的影响。
日本佛教对显密的区分源自空海(779-835),后者认为密教基于法身佛,并围绕金刚界和胎藏界的宇宙观而构建,通过手印、壇城、密咒、陀罗尼以及观想来现证佛身、语、意三密,立地成佛。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东密护教士又进而发展出了“纯密”和“杂密”的概念,即将空海在汉地(唐朝)所接受的金刚界和胎藏界灌顶的内容称为“纯密”,而将其他在此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的具备密教因素的经文和仪轨统统归入“杂密”一类。[6]
受此影响,汉传佛教史家往往将“开元三大士”所传的密法与日本佛教界所说的“纯密”联系起来,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汉文文献中找到材料来支撑日本佛教学界对于一个自觉的唐代密教教派或者传承,以及纯密、杂密之分别的阐释。
Sharf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唐代汉文佛教文献中的“现(显)”、“密”的分别,并非用来指称一个独立的组织、派别,甚至教义,而是用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佛教行者之根器有利钝之差别,所以佛陀必须随机应变、因材施教。显教可为所有人印证,而密教则惟赋异秉之人才能证悟。
“开元三大士”的教法于当时代或被视为有神通的新技术,但绝非一个独立的传承、派别或者说乘。事实上,是10世纪时的赞宁(919-1001)在编撰《宋高僧传》时,才开始渲染“开元三大士”的神通,将他们的修法、行为归入“密教”的范畴的。
西方早期的佛教学者多倾向于将佛教看成是一种排斥偶像崇拜、仪式化、神力加持等内容的具有诠释性、理性,甚至审美性的信条,而将密教看成是印度佛教晚期吸纳了印度教的元素、甚至受到了民间信仰的污染而形成的重在防病禳灾的方便之术,所以颇为中意于后人创造出来的所谓“纯密”和“杂密”的区分。
然而,从文献、艺术史及人类学的记录来看,可确信构成密教的根本要素,如密咒、手印、仪轨、偶像崇拜、祝祷、追求成就、体认三密等等,几乎为所有的汉传佛教教派所共同继承,无论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是经院的,还是俗众的。总而言之,传为唐代“开元三大士”所传的汉地密乘佛教传承实属子虚乌有,是后人凭空建构出来的。
在Sharf先生对汉传(东亚)密教这一个有问题的学科分类进行了一次福柯式的解构之后,McBride先生的文章《果真有“密乘”佛教吗?》则“想要用一种更为细致的方式,来探索从公元5世纪到8世纪,及其以后中华文化圈中的佛教徒(包括一些历史学家想要把他们归入汉地最早的“密宗”或“怛特罗”佛教信徒的人物),是如何采纳了‘密教’(esoteric teaching)和与之配对的‘显教’(exoteric teaching)观念,以及相关的用于描述和分类佛教教义的概念。”[7]
McBride先生此文的出发点是:所谓密教从定义上说就是更高深的、适合于菩萨的大乘教法,因为“密”与“显”的概念,必须被理解为它们仅仅在佛教将其教义判定为声闻、独觉和菩萨三乘,或者小乘四谛、大乘般若空性和大乘“无生法忍”密意这一判教体系内才起作用。
它们不仅指秘密、隐藏、掩蔽与公开、显现和展示之间的对立,而且还暗含了大乘与小乘相比所具有的先天的优越性。而支持McBride先生这一观点的最有力的依据便是传为龙树菩萨造、鸠摩罗什译的中世汉传佛教最权威、最重要的文本《大智度论》中的一段话,其云:
佛法有二种:一、秘密,二、现示。现示中,佛、辟支佛、阿罗汉,皆是福田,以其烦恼尽无余故。秘密中,说诸菩萨得无生法忍,烦恼已断,具六神通,利益众生。以现示法故,前说阿罗汉,后说菩萨。[8]
显然,按《大智度论》之密意,“现示法”就是声闻和独觉二乘,而“秘密法”则是大乘用以证得戒、定、慧三学的集成。
McBride先生接着仔细地查检了从公元5世纪到8世纪之间汉传佛教之诸家注疏,确认尽管各家对于“显教”和“密教”概念的解释并非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有着某种一致性,即“密教”指的是高深的大乘教法,而“显教”或者“显示法”指代的即是非大乘佛教的传统。即使是那些被人认为是“密教”大师的人物,实际上也不曾想要重新定义“密教”和“显教”,“开元三大士”并没有创建一个根本上不同于大乘教法的新体系,他们只是在广大的大乘教法中,为他们超越二元性的仪轨化修行方式与证得佛性之愿望争得了一席之地。
这就是为何在唐代汉文佛教文献中并没有出现明确记载独立的“密宗”的文献证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若问在公元10世纪以前是否真有“密教”?可能的答案有两个:一、有,但所谓“密教”指的就是甚深的大乘教法;二、没有,因为“密教”所指无非是甚深的大乘教法。
三
显而易见,上述Sharf和McBride两位先生的文章虽然视角不一,但异曲同工,实际上都否定了这样一个传统的说法,即唐代中国曾经存在过一个由“开元三大士”所创立的作为宗派的,并有明确和系统传承的“密乘佛教”。
这一挑战旧传统的新观点对于以往的汉传佛教史,特别是东亚密教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颠覆性的影响,它对于东亚密教史这个领域今后的走向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无疑,只有花力气去对他们提出的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才能理清许多与密教相关的基本问题,从而加深对汉传密教传统的理解,对汉传佛教史,特别是汉传密教史的历史谱系作出新的构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位先生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在汉传佛教史上是否存在过密教的教法和实践,而是唐代中国是否存在过作为一个宗派的密教。
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否定密教的因素曾经在汉传佛教中存在这一历史事实,甚至他们都确信构成密教的根本要素不但早在“开元三大士”之前就已经在汉传佛教中出现了,而且它们几乎为所有的汉传佛教教派共同继承。
他们的文章更专注于讨论的是当时汉文佛教文献中到底有没有出现过专指“开元三大士所”创立的“密教”传统这样的名相,以及当时汉文佛教文献中提到“密教”、“秘密法”时指的是否就是由开元三大士传承的、今天被人认为是“密教”的东西?显然,他们的研究结论对此持否定的观点。
因为古代汉文文献中“密教”这一名相之所指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密教之所指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确定10世纪以前汉文佛教文献中所说的“密教”指的只是与小乘佛教相比更为甚深、广大的大乘佛教,实际上并不等于全盘否认10世纪以前汉传佛教中曾经出现过“密教”的教法和修习这样的事实。
这场讨论的一个重要意义或在于它引发了我们对佛教史研究中的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的讨论,即究竟何谓密教?密教的历史应当从何时开始?
即如Sharf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可以把对密咒和手印等的运用作为密教的标志,那么汉传佛教中密教的出现当远早于“开元三大士”。
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对“密教”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那么,汉传密教的内容将比我们现在所界定的、所知的要丰富得多,汉传密教的历史也比我们现在所构建的历史谱系要悠久得多。职是之故,在我们讨论东亚佛教史上究竟有没有汉传密教传承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更应该首先理清到底什么是密教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密教(怛特罗)于今日之西方世界已被追捧为“艺术和科学的综合体,它承认作为人类的形而下和形而上的经验。密教修习提供了个体一个与日常生活达到平衡与和谐的机会,”“是唤起一种对男人、女人和神灵关系的敏锐探索”,[9] 而且迄今西方学界对密教的学术研究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了,近年来国际学界对密教的研究也日趋繁荣,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密教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密教就像是“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一样,成了一个以某种方式拒绝被定义的术语,学人们对密教的认识基本上处于盲人摸象,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
当代著名的南亚密教研究专家、法国学者André Padoux先生(1920-)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说过:“对密宗做出一个客观而又科学的评判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一主题是富有争议和令人费解的。对于密宗不仅专家们给出不同的定义,而且其真实存在有时也被否认。”[10]
与此同时,另一位密教研究专家Teun Goudriaan先生也认为“给予密教——主要流行于过去一千五百年的印度宗教传统之一——极端多样而复杂的本质一个单一定义的处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该词的精确范围有着普遍的不确定性。”[11]
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很少有术语像密教一样在当代话语中看起来是如此普遍、如此广泛地被使用,却如此不明确、不恰当地被定义,通俗的和学术的二者均是如此。
当然,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学者曾经尝试过要给密教一个合适的定义,在近年出版的密乘佛学研究著作中,我们也常常见到对“密教”定义的讨论,学者们对密教之源流的追溯、核心内容的诠释和其历史谱系的建构等等问题,都有相当激烈的争论。虽然这些争论都还没有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论,但这些争论本身却为我们理解密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印藏佛学家David Snellgrove先生(1920-)曾经在他研究印藏密教无上瑜伽部母续《喜金刚本续》(Hevajra Tantra)时对密教下过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定义,他以佛典中对“经”和“续”的明确区分而将佛教作显、密两种传统的划分。因为Tantra(怛特罗),即密教,于藏文中译作rgyud,译言“续”或者“本续”,通常就是指与“经”(mdo,显宗经典)相对应的“本续”(rgyud, 密教经典),故Snellgrove把密教这一术语限定在其特定的文本应用上,而不把它更广泛地运用到其宗教实践体系中。
此即是说,他把密教只限定为其标题中出现Tantra,或者rgyud的那些文本,所以他提出的密教定义是:“密续这一术语涉及共通于印度教和佛教传统的仪轨文本的清晰的、可定义的类型,它们通过各种密咒(mantra)、禅定(dhyāna)、手印(mudrā)、坛城(maṇḍala)来召唤神衹和获得种种成就。”[12]
显然,这样的定义不但不足以涵盖作为一种宗教传统的密教,因为密教首先应该是一种实修的方式,而且甚至也无法涵盖所有密教的文献。
众所周知,有些佛教经典虽然其标题中也有Tantra字样,但实际上并不是密教文本,例如被列为“慈氏五论”之一的Uttaratantra(《究竟一乘宝性论》);反之,有些佛教经典的标题中并没有出现Tantra的字样,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密教续典,如《圣吉祥文殊真实名经》(Maňjuśrināmasaṃgīti),它被藏传佛教徒列为密续中首屈一指的、最殊胜的一部密乘根本续,自宋、历西夏至蒙元时代,它至少先后有四次被译成了汉文,同时也还被译成了畏兀儿文、西夏文和蒙古文等等。
还有,最著名的大乘佛经之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于藏文大藏经中既列于显乘的“诸经部”,也见于密乘的“密咒部”,换言之,它既可以是“经”,也可以是“续”,或者说它是“总持”(陀罗尼)。后世的注释家既有把它当作经,也有把它当作续来解读者。[13] 甚至,《心经》也可以用作密教的一种修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我们就见到过一部题为《持诵圣佛母般若波罗多心经要门》的密修《心经》成就法,源自西夏时代。[14]
显然,仅仅依靠佛经标题中有无Tantra或者rgyud的字样来判定它是一部显乘的经典、还是一部密乘的续典并不十分可靠。将密教狭隘地定义为作为文本的“本续”,不但无法揭示甚深、广大之密教传统的教法理路和实修本质,而且也不能包罗所有的密教文献。
密教的“本续”虽然是五花八门的密教修行、仪轨的教法依据,但以它们为依据而由印度大成道者和历代密教祖师们发展出来的用以指导行者实修的仪轨类文献,如“修法”(sādhana, grub thabs)、“教授”(gdams ngag)和“要门”(man ngag)等等,乃指导行者实修密法的指南,其数量远远超过“本续”,它们是密教文献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仅仅以作为文本的Tantra来定义密教有其明显的不足。为了弥补其不足,Snellgrove还特别规定只有那些其中出现了“密咒”(mantra)、“手印”(mudrā)和“坛城”(maṇḍala)的文本,即拥有俗称3M的文本才能成为“密续”,或者密教。
如此一来,虽然他为后人理解密教的修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但他对密续的定义则更受限制。我们或可做这样的理解,判定一种佛教教法是否属于密乘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看这种修法中是否包含有3M的因素。换句话说,所谓“密教”一定得拥有“密咒”、“手印”和“坛城”三大要素。[15] 若此说成立,那么Sharf的说法,即密教早在“开元三大士”之前就已经在汉传佛教中出现,委实不无道理。
于上个世纪80年代,Padoux曾经在他为《宗教百科全书》撰写“密教”这一辞条时综合其前辈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一度相当有影响的密教定义,他指出:密教的教法“试图将欲(kāma)的一切意义不折不扣地服务于解脱——,不是为了解脱而牺牲现世世界,而是在救赎的角度上用不同的方式来巩固这个世界。通过欲以及红尘万象可以取得现世和超世的利乐(bhukti)、成就(siddhis),并达到解脱(jīvanmukti),这种功用透露出了一些密宗大师在宇宙观上的特定倾向,即将宏观/微观宇宙合一的完整宇宙观。”[16]
显然,Padoux对密教的这个定义与藏传佛教徒自己对密教的定义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我们在传自西夏时代的一部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见到过与Padoux上述定义相类似的说法,其云:
圣教中说:欲成就究竟正觉者,有二种:一依般若道,二依秘密道。若弃舍烦恼而修道者,是显教道;不舍烦恼而修道者,是密教道。今修密教之人,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返为道者,是大善巧方便也。[17]
这里所说的“般若道”和“秘密道”显然与前引《大智度论》中所说的“秘密”和“现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确实就是分别指大乘佛教中的显教和密教两种传统,其中的“秘密道”或者“密教道”者,即是我们正在讨论的密乘佛教。而其根本思想,即将“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返为[成佛之]道者”,或者说“不舍烦恼而修[佛]道者”,即与Padoux上引对密教的定义同出一辙。
此即是说,在佛教的传统中,显教与密教的差别就在于显教要求行者必须断除贪嗔痴等一切烦恼才能达到成佛的境界,而密教则认为贪嗔痴等一切烦恼不再是成佛的障碍,而可以转为道用,成为通往成熟解脱的一条道路,行者可以在修习贪嗔痴、获得大喜乐的当下,体认“乐空无二”,即身成佛。
虽然Padoux对密教的定义可谓抓住了密教最关键的理论依据,但它显然更多地专注于密教修行的终极目的,而没有将密教修行的内容、性质、方法和特征等也纳入其考虑范围,以致于过分宽泛而难以用来界定密教的具体修行。
晚近,美国密教研究专家David Gordon White先生(1953-)在他主编的《实践中的密教》(Tantra in Practice)一书的导论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讨论密教的定义和历史框架等问题,他给密教下了这样一个暂时性的定义:
密教是一个亚洲信仰和修行实体,它主张“神性”(godhead)孕育并维系着这个宇宙,我们所感知的宇宙只是这种神能(divine energy)的集中体现,密教试图以各种创造性和突破性的方法,在人类中的“中千世界”(mesocosm)中通过仪轨接近并与这种神力沟通。
White的这个定义听起来相当的抽象和哲学,然或正因其大而化之,故可适用于亚洲所有地方性和区域性宗教,如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中的密教修行方式,成为一条富有价值和条例的准则。
但是,它似乎比前述Padoux的定义更加晦涩、模糊,显得有点空山灵谷而不着边际,很难为普通的密教修行者和研究者们所理解和认同,也很难与具体的密教修行方式和观念联系起来,故它必须根据实际、具体的语境进行补充和调整。
为了弥补这样一个概念性的定义的不足,White在他的这篇导论中还对密教修行的几个关键性因素,即密教壇城(maṇḍala,中围,是沟通宇宙大千世界和个体小千世界的中千世界,观修中围和观修本尊一样,是令小千世界和大千世界、行者和本尊相应的一种修行方法)、密教灌顶(abhiṣeka, dīk ā,通过上师的灌顶和加持将行者纳入密教的传承谱系中,种下觉悟的种子)、瑜伽(yoga,通过风、轮、脉、明点的修习,获大喜乐,成正等觉)、密教性爱(手印母, mūdra, 依行手印修欲乐定,得大喜乐,证乐空无二之理)等作了相当详细的讨论,试图用这些十分具体的密教因素来为密教的界定提供更基本的依据。
如果一种教法修行具备上述这几个最典型和关键的密教因素中的全部或者部分,那么它就可以被称为密教。
显然,在很难为如此复杂的密教做出一个十分恰当和可以一锤定音的定义的情况下,用罗列其宗教实践中的最典型的特征来描述和界定密教,采用所谓“多元化判教”(polithetic classification)的方式来叙述密教,实在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权宜之计。
所以,用这样的进路来定义密教也已经成为其他密教研究者通常所采用的方法。当然,不同的学者罗列出来的密教特征各不相同,从六个到十八个,不一而足。[18]
例如Richard Karl Payne先生在他为他所编的《东亚密乘佛教》(Tantric Buddhism in East Asia)一书所写的导言中就没有对密教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罗列了十余条通常被认为是密教之理论和实践的最典型的因素和特征。若把它们归纳起来实际上也不出前述White所归纳的密教坛城、灌顶、瑜伽和性爱等四个条目。[19]
还有,Lopez提出在前述3M的基础上,或许还可以加上诸如guru(上师、喇嘛)、abhiṣekha(灌顶)、vajra(金刚)、sukha(喜乐)、sahaja(俱生)、siddhi(成就)等等的一系列关键词,来更具体地描绘密教传统及其主要特征。[20]
四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迄今我们对密教的认识确实还没有摆脱盲人摸象的状态,所以,虽然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对密教的定义辨别出印藏佛教或者东亚佛教传统中出现过的密教修习因素,但很难判定作为一个宗派或者一种传统的“唐密”是否真的存在过。
一方面,正如Sharf所说的那样,密咒、手印、仪轨、偶像崇拜、祝祷、追求成就、体认三密等等可以被认为是密教因素的东西远早于“开元三大士”就已经出现;但另一方面,即使是所有被认为是“开元三大士”所传的密教恐怕也不可能涵盖前述所有那些被认为是密教之主要特征和因素的东西。不管是密教,还是后人对密教传统的判定(classification)和对密教历史的建构,它们都还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之中。
汉传密教史研究遭遇无法摆脱的困境,除了由于密教始终缺乏一个清晰的定义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汉传密教历史的构建受到了印藏密教史的多方面的影响。
二百年来,在西方学者所构建的佛教史中,密教始终是被作为佛教衰亡期才出现的宗教运动,所以,它的出现不可能太早。
而将汉传佛教中出现密教传统的时间定在开元三大士传授“唐密”的时候,却正好暗合了西方学者关于密乘佛教的文本于公元7、8世纪才最初出现的时间认定。
如果说构成密教的根本就是它的文本,即所谓“本续”(Tantra),那么迄今为人所知的最早的“本续”是密乘佛教的《密集本续》(Guhyasamāja Tantra)和《喜金刚本续》(Hevajra Tantra),它们分别被认为是密乘佛教无上瑜伽部的父续和母续部的根本续。[21]
关于它们最早出现的年代,学者间曾有过长期和激烈的争论,或以为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密集本续》),或以为直到公元8世纪(《喜金刚本续》)才出现。目前学者相对而言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密教本续的出现大概是在公元7世纪。[22]
毫无疑问,用作为文本的“密续”来定义作为一种宗教实践的密教,这样的进路完全不适用于汉传密教。如果真有“唐密”存在的话,它们一定与作为文本的“密续”(即怛特罗)没有关联,至少和前述这两部大瑜伽部(Yogatantra)和无上瑜伽部(或称瑜伽母续部Yoginītantra)的密续毫无关系。
因为这两部密续的非常不完美的汉文译本是在公元11世纪初年的宋代才出现的,它们分别是施护翻译的《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即《密集本续》)和法护翻译的《佛说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即《喜金刚本续》)。
它们不但出现的时间晚,而且即使在宋代也没有对汉传佛教产生过任何明显的影响。密教无上瑜伽部的修习是从西夏时代开始经由藏传佛教徒才在汉地传播的。可是,如果我们同意Snellgrove对密教的定义,即将密教等同于作为文本的“密续”,并将汉传密教和藏传密教放在同一个判教体系中观察的话,那么说汉地于开元三大士时期(8世纪中)出现密教从时间上说却大致符合,而Sharf等所主张的说法,即于此前很久汉地就已经出现了密乘佛教的因素,则于佛教史上反而遭遇了难解的年代学问题。
显然,将密教等同于作为密教经典文本的“密续”对于理解汉传密教、构建汉传密教的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困惑,如果我们非要坚持密教(实践)是随着密续(文本)的出现才兴起的宗教运动,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在“开元三大士”以前汉传佛教中就已经出现的种种密教因素和实践。
显然,只有将作为宗教实践的密教和作为宗教文本的密续分开,我们才能对汉传密教的历史作出相对客观的描述和理解。
最近,丹麦知名佛教学者、韩国佛教史研究专家Henrik H. Sørensen先生在尝试对汉传密教作定义的时候,明确地将密教(Esoteric Buddhism)和密续,或者怛特罗(Tantra)作了明确的区分,将长期以来被我们笼统地称为密乘佛教的东西分成了汉地的密教和印度、西藏的怛特罗两大部分,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明智的做法。
如果我们查检汉文大藏经,不难发现在汉传佛教中“怛特罗”这个词汇出现的频率极低,宋以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大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密续的汉译本。
密续本来就是于7世纪才开始在印度出现,其后分别于藏传佛教的前弘期(7世纪中至9世纪中)和后弘期(10世纪中后期至今)两次大规模地被翻译成藏文,被分别称为“旧译密咒”(gsang sngags rnying ma)和“新译密咒”(gsang sngags gsar ma),于西藏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
可见,汉地的密教传统与于7世纪才开始出现的怛特罗无关,它指的是早期佛教中所传习的密咒、陀罗尼、手印和坛城的修法,形成为另一个早期密教的修行系统。
除了中、晚唐时期出现的真言宗或可认为是汉传密教的一个派(school of practice)或者一个宗(tradition of practice)以外,中古中国确实没有出现过一个密教的教[宗]派。
但密教,或者说Esoteric Buddhism,确实曾经在汉传佛教中存在过应当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3]
用“密教”(Esoteric Buddhism)和“怛特罗”(Tantra或者Tantric Buddhism)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来将汉传和藏传密教做出明确的区分不失为一个可行的策略,但是,不管是在两种不同的密教传统的具体修法实践中,还是在佛教史研究这个学术领域内,实际上我们均无法将它们作出如此明确和截然的切割。
首先,我们将面临的是如何来分别定义密教和怛特罗这一难题,如果我们不仅仅将Tantra当作一种文献类型,而是也把它当作与这些文献相关的宗教实践,那么我们就很难明确划分密教和怛特罗二者之间的差别。
按照目前学界通行的说法,密乘佛法分成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等四大部类,其中的“根本续”(Tantra)为数寥寥,其中属于瑜伽部的主要续典是《密集》,属于无上瑜伽部(瑜伽母续)的主要续典是《喜金刚》和《胜乐》。
它们当然与纯粹的汉传密教,或所谓“唐密”无关,汉传密教的修习在藏传密教于西夏、元代传入汉地以前从来也没有达到过无上瑜伽部这样的高度,它们更应该是属于较低层次的事部、行部的修法,最多也不过是瑜伽部的东西。
显而易见,用这种目前为学界习用的密教分类法来规范、判定汉传密教传统的源流和体系是反历史和不科学的,将使汉传密教史的构建面临多重的困难。
众所周知,密教的四部分类法是藏传佛教,特别是其后起的格鲁派的习惯做法,是藏传佛教在其引进、发展印度密教的过程中逐渐创立起来的一种判教传统,在印度佛教中并没有这样明确的分类方法。
换言之,藏传佛教对密续做出的这种四重划分法,其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印度证据。
据说其来源是因为有藏传佛教论师在无上瑜伽部母续之根本续——《吉祥喜金刚本续》中见到了一个寓意不明的段落,它用极其神秘的语言提到了“微笑、凝视、拥抱和性爱”这四种神秘莫测的姿势,于是,他们便将这四种神秘的姿势用来和密续四种等级的划分联系起来,将密续构建成一个由低及高的、连贯的整体。
不仅如此,密续的四部分类法也绝对不是对密乘文献的唯一划分法,藏传佛教中对密续种类的划分还有五分、六分,乃至九分的分法。[24] 而这种对密续分成四部的分法在西藏最后形成的时间远晚于开元三大士于汉地传播密教的年代,用这种后出的分类法来规范此前早已存在的宗教实践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五
虽然我们迄今依然无法对密教做出明确的定义,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说不清楚到底何谓密教?可是,密教这一范畴不但在西方大多数宗教学者的词汇里是一个基本的、常见的词汇,而且它也已经成为一个在大众想象中十分有魅力的东西,通常被打上“神圣的性爱”(sacred sex)的标签,充斥于西方的流行文化之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众说纷纭的这个密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存在,而是某种形式的西方思维的产物,是一个西方思维发展出来的错误概念。
正如美国南亚密教研究专家、俄亥俄大学宗教学系教授Hugh B. Urban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密教
是一个辩证的范畴(dialectical category)——很像沃尔特·本雅明所说的‘辩证的想象’(dialectical image)——产生于西方和印度思想之间的映像和模仿(mirroring and mimesis)。
它既不是单纯的本土演化的结果,也不是少数东方学家的虚构,密教是同时发生在本土与他者之间的,由幻想、恐惧、愿望满足所构成的一种不断变化的混合体,这击中了我们对异域东方和当代西方的建构的要害。”[25]
密教虽然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又确确实实曾经在东方存在过,所以,我们不能说它只是一种纯粹的殖民主义的想象物。但密教作为一个统一的、独一无二的、抽象的存在,无疑是西方几代东方学家们精心构建出来的一个“极端的东方”(The Extreme Orient),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产物,它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创造过程,受到了过度多样的、相互冲突和矛盾的诠释。[26]
由于密教是一个非常多变、游移的范畴,它的意义随着特殊的历史时刻、文化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所以,作为宗教史家,我们应当批判地检视以往学者们建构并处理密教的方式,并把他们对密教的想象,与学者们所处的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此来追溯这个有着独特范畴的宗教的谱系。
建构密教的谱系学就是要结合特定的学术背景、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来追溯西方和东方学家们定义和再定义密教的方式, 使其成为一部宗教史的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将诸多看似离散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构想到一个统一体,即一个共同的概念——“密教”中来,是一个十分复杂和耗时的大工程,为此西方学者们已经花费了不少的功夫,而且势必还将花费更多的功夫才能达成这一目的。[27]
总而言之,西方人对密教的想象曾经是其对印度的整体想象中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知识的征服(conquest of knowledge)从来就是西方殖民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与西方殖民征服印度的过程相伴随的是,印度也被逐步构建为西方最典型的、最重要的“他者”。
印度被塑造成了一个激情的、无理性的、柔弱的世界、一片充满幻想的、杂乱的土地,它被置于进步的、理性的、阳刚的和科学的现代欧洲的对立面。而密教在西方人构建这样一个印度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首先,当19世纪的东方学家和传教士们开始构建一个叫做“印度教”(Hinduism)的抽象实体时,他们也开始把密教想象成为它的最主要的,也是最不值得赞扬的组成部分。
他们将拥有吠陀和奥义书的古代印度定义为印度的黄金时代,而将开始实践密教的印度定义为印度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于是,密教被他们称为印度最糟糕、最愚蠢的信仰,密教的修行是世界上最不道德、最堕落的、最令人恐怖的宗教实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于西方人的视野中,密教往往与不道德的、淫荡的性联系在一起,密教自始至终被不断地色情化。
这种倾向当然不是西方人对密教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来的结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对密教中莫须有的不道德的性和性变态的兴趣显然不过是他们对性的更广泛的关注的一个部分而已。
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英国的中、高层阶级一反清教徒对性十分拘谨的态度,开始着迷于性,并对性津津乐道。这种维多利亚时代幻想曾经沉溺于对性心理失常(sexual aberration)的认同、分类和列举,也沉溺于对能够想象的性变态或恋物进行详细的科学描述。
他们对印度人的性行为,特别是密教的所有修行仪式的兴趣,不过是他们对于性和性变态的广泛的着迷的一个核心部分而已。正如萨义德(Edward Said)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殖民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总是一个“性别的”(gendered)计划。
在西方殖民话语中,印度的男性总被描述成既软弱、阴柔、好色、卑鄙、道德败坏,而印度的女性总被想象得极度性感、魅惑、放荡、对肉欲贪得无厌。无怪乎常常被表现得十分性感的印度女神迦梨成了印度女性的代表而被顶礼膜拜。将密教定性为猥琐、下贱、堕落和放荡等等,实际上暴露了维多利亚时代殖民印度的时代精神。

印度女神迦梨(Kali)的雕像,加尔各答美术馆
除了色情化密教的传统之外,西方也存在着另一种浪漫化、哲学化密教的传统。在西方密教学术史上,John Woodroffe先生曾被称为“当代密教研究之父”,是他开启了纯化密教的另一种传统。
Woodroffe是一位具有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名英国殖民地的法官,曾任孟加拉检察总长,但私底下却对密教研究情有独钟,是一位杰出的密教学者,曾化名Arthur Avalon,发表了大量研究密教的学术著作。
他一反西方色情化密教的传统,以捍卫密教传统为己任,用力鼓吹密教不是一种荒谬、性放纵、不道德和邪恶的东西,而是一个高尚的、有哲理的、理智的宗教传统。
密教不仅与印度古典时代最崇高的传统吠陀有基本的连续性,而且甚至也与欧洲科学的最新发现基本一致,符合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和哲学观念。
这与今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教授Robert Thurman先生将藏传佛教说成是人类最伟大的心灵科学,声称藏传佛教的杰出代表喇嘛在心灵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西方研究太空的科学家们在空间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Woodroffe捍卫密教的这个传统也为诸多后起的密教专家们所继承,使得密教于近代学术背景中也曾被推崇为完全哲学的、高度理智的和纯文本的一种宗教传统。例如前面曾经提到过的法国密教学者Padoux就强烈反对把密教定义为主要是仪式或修行的传统,坚持认为密教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一种哲学以及思辨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具有一种极度复杂而且精妙的世界观。
不管是性化了的密教,还是高度哲学化了的密教,它们显然都是西方思维的产物,而不是密教的真面目。只有当我们把被我们叫做“密教”的传统放置于以往它被不断想象和建构时的十分具体的历史、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背景中来考察,把它当作一个在宗教历史中非常具体的、历史的——尽管非常混乱并有疑问——范畴来看待时,我们才有可能超越这种把密教作为外来的“极端的东方”的学术建构,从而开始对密教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研究。
六
“想象密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子工程就是首先要完成对密乘佛教历史的基本想象,否则就难以确定密教研究的资料范畴、解释方法以及用于历史知识结构中的意识形态等等,也就难以进而为密教研究在现代学术界合情合理地取得一席之地。
有意思的是,我们通常所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那些成就历史之具体事件和事实的产物,我们所写的历史常常无法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十分客观地还原历史的真实(wie es eigentlich geschehen ist)。历史经常是那些设置、建构历史的历史学家们的诗意的想象,是一种将这些事实置于某个传统叙事结构中的想象。如同一切人类活动,西方学者们对印度佛教史的最初的想象过程也有自己的一段历史。
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Christian K. Wedemeyer先生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修辞、分类学与转向:简论佛教密宗历史编纂源流》的文章,分析从19世纪早期直至今日支撑着印度密乘佛教史结构的话语体系的演化,以及这种结构化(以及正处于结构化过程中)的叙述是如何随着对密教的研究的推进而发展变化的。[28]
Wedemeyer强调历史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叙事形式的制约,后者不只是历史学家在其中安放材料的外部包装,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cognitive instrument),没有这个工具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获得某种现象的“历史”。
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们最为常用的理想化历史叙事模型就是将历史当作一种有机发展的过程(organic development),任何故事、历史都像人的一生一样要遵循一个有机发展的周期,即如黑格尔“将任意给定文明的历史以及文明本身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出生与原生长时期、成熟时期、老年时期,以及瓦解和死亡时期”一样。
根据这一原型的观点,如同植物和动物一样,任何文明现象都会经历一个出生、成长、成熟、衰落和死亡的过程,所以,所有的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在沿着这一轨道行进中的某个阶段的产物。于是,任何城市、国家、思想流派、政党,乃至宗教,都被放到这个模型中进行概念化,而其历史过程中的各个事件也因循这个模型而得到了相应的解释。
由于正当西方佛学研究滥觞的时候,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此即是说,佛教在印度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全部历程,所以它被赋予了一种历时叙事结构(diachronic narrative),人们可以讲述一个佛教从生到死的完整故事。
于是,西方佛教史的编纂便完完全全地使用了这一有机发展的历史原型,这个叙事结构为佛教史家构建印度佛教的历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们可以讲述一个既熟悉又容易为人接受的完整故事。佛陀释迦牟尼的出生就是佛教的出生,佛教的小乘或者上座部时期是佛教发展史上的成长期,故其经典又被称为“原始佛教”。
紧接着出现的大乘佛教是佛教史上的成熟期,达到了佛教有机发展的顶点,于此佛教便不得不草草收场,进入佛教史上衰亡期,也即密乘阶段。于是,佛教传统中的小乘、大乘、金刚乘(密乘)的层级结构(以及密乘内部的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被建构成为一个简易的佛教教义史时间序列。换言之,原本被佛教思想家认为是一个佛教教义逐渐精致化的玄秘序列,这下却被现代史家叙述成为一个伪佛教经论发展的时间序列了。
按照这个有机发展过程构建起来的印度佛教历史,密乘佛教自然就必须符合“衰落并灭亡”的经典叙事想象原型:一种曾经强大而充满生机的文化难以抗拒世间喜乐之诱惑,人们放弃了以前对纯真和美德的信仰,于是,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社会变得颓废不堪,一个盛极一时的文明终于走上了消亡的道路。所以,大乘佛教是佛教可以达到的顶峰,从此它便不断遭到印度人懒惰和淫荡的本性的侵蚀,于是虚假的经文(密教续典)纷纷出笼,行者被准许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密教修行成了放荡淫逸的代名词,宗教不过是为实现不知厌足的性的现实提供了一种宗教维度。
当这样一种有机发展史观和叙事方式确立之后,佛教史家在构建佛教历史的时候实际被给予的叙事空间已经很小,通常他们对情节结构的迫切需求远远胜过并取代了他们对有充分证据的具体内容的追求。所以,在一部完整的印度佛教史中,密乘佛教一定不可能太早的出现,密教经典形成的时间也一定要晚到足以为佛教的衰落承担责任。当然,密教也一定与堕落、腐朽和衰亡联系在一起,必须与佛祖所传的崇高道德和修法背道而驰,它也一定是以性道德的丧失和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为典型特征的。
当佛教史上的这个有机发展过程一旦被建立起来以后,哪怕是最好的学者(如最精致的语文学家)的最好作品,最终也不得不顺从这一幽灵般的共识,为此他们可以无视佛教实际上在密教兴起之后依然在印度持续(并且事实上是繁荣了)好几个世纪的事实,无视密乘佛教今日于世界范围内呈方兴未艾的繁荣局面,甚至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所有佛教文献中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让人得出上述这样的一个结论,即密教是一个晚期出现的、导致佛教走向腐败和衰亡的宗教传统。
事实的真相是:当我们已经确信这种说法时,我们便永远无法透过想象叙述模型所布下的前景而看到事实的真相。如果有人敢于打破这种已经延续了近二百年之久的构建印度佛教历史的基本想象,破除这种“有机发展”史观,那么,一部完美地构建起来的佛教史就会变得很不完美,就会引发出一长串亟待解决的新问题,甚至使整个佛教学术领域陷入一种令人沮丧的崩溃状态。
而回到传统范式那种舒适和安全的怀抱或许是我们所有人的更好的选择,这就是形成我们时常可以感觉到的一种顽固的和跨世代的学术保守主义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密乘佛教历史的主流观点能够在没有任何确凿的历史论据支持的情况下经久不衰,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官方的学术教条。
Wedemeyer这篇鸿文虽然揭示的只是西方学界在印度佛教史的编纂过程中在有机发展史观结构中的叙事原型对佛教史,特别是密教史想象过程的深刻影响,但它对我们检讨、反思汉传和藏传佛教历史的构建和编纂过程同样具有极其深远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迄今为止,不管是汉传佛教史,还是藏传佛教史的书写,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有机发展史观的影响,如果我们希望突破迄今主导佛教史写作的这种“有机发展”叙事原型,我们必须把一部佛教历史的编纂突破印度佛教史的范畴,而把它和汉传和藏传佛教史整合在一起。鉴于藏传佛教作为硕果仅存的密乘佛教传统今天不但没有走向衰亡,反而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事实,我们很难再如此坚定地相信密乘佛教的出现是佛教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标志,或者说,我们不再应该把密乘佛教史当成是佛教史中的最后一个篇章——即佛教衰亡史,而应该开始更加尊重密乘佛教发展史中的重要历史事实,重新开展真实的、富有建设性和创造力的密乘佛教史研究。
当我们脱离前述叙事模型,抛弃既定范式,立足于更具批判性的态度来考量佛教史研究应该采取的范式,我们的研究就会使得许多以前视而不见的新信息浮出水面,并保证我们对密乘佛教史的新的想象的建构过程不像从前那样武断。譬如说,如果我们脱离“有机发展”这一历史叙事模式来重新考量密乘佛教的历史,那么我们就既不会为密教因素于开元三大士之前就已经出现于汉传佛教之中而感到惊讶,也不会对藏传密教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而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密乘佛教的产生既不代表佛教衰亡的开始,它也还远远没有到达该终结的时候。
如前节所述,将密教与性联系在一起是西方“想象密教”工程中的一大创获,以至于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密教几乎就是“神圣的性爱”的同义词,成为那些既不愿放弃物质的喜乐,又希望获得精神的解脱者们的最爱。有意思的是,在被“有机发展”史观框定的密教史中,密教同样与性结下了不解之缘,性爱成了密教修行的一个最中心的概念,密教俨然是一种放纵肉欲的宗教。
事实上,文明衰落紧承道德(特别是性道德)沦丧出现的叙事方式,早已在古典历史传统中就已经得到确立,佛教史家于此不过是在他们对佛教历史进行历史想象时捡了个现成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藏传密教在汉文化传统中也常常被人与性和房中术联系在一起,这个传统缘起元末西番僧于蒙古宫廷传播之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或曰“演揲儿法”。

号主按:图为萨迦派所传修习喜金刚本尊瑜伽的所谓“喜佛三十二妙用定”之一,内分顺行、逆行和混行,共九十六种图式,藏于北京故宫博物缘。1983年《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马健题为《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短篇小说,它以游记的形式讲述作者于西藏的所见所闻。沈卫荣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座上说:“实际上,马建在这部小说中所讲述的大部分故事根本就不可能见于或发生于1980年代的西藏,它们不过是一些现代版的《僧尼孽海》式的西藏故事。”《僧尼孽海》据说是明代“江南才子”唐伯虎根据《庚申外史》中有关元顺帝宫中双修的故事写的艳情小说,他甚至把汉人房中术经典《素女经》中的内容解释为藏传密教的修行方法,将之演绎为龙飞、虎行、猿搏、蝉附、龟腾、凤翔、兔吮、鱼游、龙交等号为“采补抽添”之九势。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转引,马健的小说讲述的五个故事都涉及怪异、不伦的性行为,特别其中对三代乱伦和宗教仪式性的性行为,即上师以灌顶为名与女弟子(女活佛)发生的性行为的细致描述,而被在京藏族同胞们视为侮辱而演变为一场政治事件。
尽管汉族作家对藏传密法一知半解,可深信不疑地将它视作宫中淫戏,其中缘由竟或也与汉族史家书写王朝历史时同样秉持的有机发展史观有关。于传统汉族史家笔下,一个王朝必定要经过兴起、成长、鼎盛和衰亡四个阶段,历朝的亡国之君又没有一个不是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而其无耻之极致则一定与不知厌足的淫欲有关。可以说,明初史家在对元末衰亡史进行历史想象时也正好捡了个现成,西番僧所传的秘密法为传统的亡国之君的叙事模式提供了花样翻新的、富有异族风情的好作料,从此藏传密教也就再也难以摆脱被情色化的厄运了。
七
密教至今蓬勃发展,今人甚至将其列入“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之列,但也常常遭人诟病,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密教修行中包含了五花八门的、匪夷所思的修法。
西方学者常常将密教的修法指称为“违背常理的”(antinomian),因为它的最受推崇的经典(Tantra)中说的话听起来像是“疯子的胡话”,它似乎是在建议它的信徒们不但违犯其自身传统,即佛教的最根本的清规戒律,而且甚至也违犯人类正当行为的一切最根本的时代标准,它彻底地超越了人类最基本的是非、好恶观念和日常伦理纲常。
所以,密教曾被西方人认为是印度思想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堕落的东西,它们是如此的可怕、暴力、变态、下流和令人厌恶,以至于不应该让它进入基督徒的耳朵中。[29]
例如,密教中的所谓5M仪轨,曾令密教声名狼藉。这个仪轨允许修行者吃肉(mā asa)、吃鱼(matsya)、喝酒(madya)、吃干粮(mudra, 或曰手印)和性交(maithuna),即以做极度违背佛教戒律的事情,最后甚至以一次性的狂欢来完成一次神圣的宗教仪轨(即所谓的“大集轮”仪轨)。
还有,在密教大瑜伽本续中还常常出现以“五肉”(mā asa)和“五甘露”(am ta)作供养的记载,而“五肉”指的是牛肉、狗肉、象肉、马肉和人肉,“五甘露”则指的是大香(大便)、小香(小便)、人血、精液和骨髓等等。
大家知道宗教学是一门“解释学的”(hermeneutic)学科,对这些匪夷所思的密教修法及其宗教意义的解读无疑是密教史家们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30]
近两百年来,学者们也一直在努力地弄清解读密续的一个最基础的问题: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至今对此还没有一个彻底令人满意的答案。
于密教的现代学术中,学者们对如何来解读这些违背常规的密教因素有过长期和激烈的争论。尽管现今我们对密宗的教义和实践的结构和范围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离结束这一场争论还相差甚远。
迄今对此问题进行解释的进路可以实用地分成两种趋势:
其一是实指论(literalism),即认为密续准确地表达了它的本意,所以如何解读它的问题不过是一个人为的伪问题。他们将密续当作直白的、字面的表述,断言密续的作者准确地,而且仅仅准确地表明了他们所说出的话的本来意义。换句话说,密续的原始作者意图表达的只是其字面意义,任何非纯粹字面意义的问题只可能是“后来的注释家”提出的。西方早期的佛教学家、东方学家们基本都持这样的观点,因为他们相信佛教中的密教运动来源于这样一种希求,即放松传统所规定的道德戒律,容许他们更自然地享受生命的快乐。
其二则是喻指论(figurativism),持此论者认为密续作为隐秘的、密传的经典,乃通过某种特别的密码,即通过“隐喻的”(figurative)和“象征性”(symbolic)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后人必须破解其中的密码,才能理解那些若按字面理解似乎是违背人伦常规的表述和隐藏在奇异的肉类和令人恶心的体液等表达背后的真正意义。
晚近Wedemeyer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牛肉、狗和其他神话:大瑜伽续仪轨和经典中的涵指符号学》的文章,对如何解读佛教密续中出现的那些违背人伦常规的因素提出了一种名为“涵指符号学”(connotative semiotics)的新的进路,发人深省。[31]
Wedemeyer认为不管是实指论,还是喻指论,这两种解释进路在处理密续中的那些有违常理的表达时,实际上一样把它们当作直接指意的自然语言(directly denotative natural language)的实例,从而都忽略了这些传统的符号学的核心方面。
他的这篇文章要论证的是:
密乘佛教大瑜伽续采用了一种被称为‘涵指符号学’的指意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来自自然语言的符号(一种能指和所指的联合体)在更高阶的话语中,是作为能指发挥作用的。
那些在基础层面发挥影响的——既在仪轨的实修中,又在经文的叙述中——是在与更早期的佛教密续中和更广泛的印度宗教范式的重要对话中的某种有关净和秽的文法(grammar)。这表明,这种‘违背常理论’(antinomianism)——远非代表‘部落式’的实践或者神秘的瑜伽密码——反映了主流印度宗教固有的关注。
Wedemeyer认为实指论和喻指论虽然都曾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密续的理解,但它们各有其局限,密续文本的读解显然要比从“字面的”和“象征的”这两种指意方式来理解其文本要复杂得多。
我们在大瑜伽续中见到的话语是高度出人意表的,在符号学上是精妙复杂的,大瑜伽续系统中运用的不是自然语言的指意模式,而是称为涵指符号学的更高等级的符号学系统中的指意模式。涵指符号学是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先生创立的一种语言指意系统,它是指来自自然语言的一个完整符号,在更高级的系统中,不担任一个所指,而是充当一个能指。
举例来说,巴特曾在1950年代的《巴黎竞赛》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一幅一位非洲裔法国士兵向三色旗(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于是巴特联想到这张照片一定不只是要向读者们无辜地传达这位非洲裔士兵的外貌,而是为了通过这张照片表达一个更高级的内容,即通过这位爱国的殖民地居民的风采来表达“法国的帝国性”,即用这个符号来合理化法国在西非的殖民。在符号学上,观者被这一张照片引诱进了一个法兰西帝国“的确是事实”的意义世界。而这就是涵指符号学的功用。
与此相应,Wedemeyer认为对在大瑜伽本续仪轨中出现的诸如“五肉”、“五甘露”一类明显违背人伦常理的东西,均无法用实指和喻指的指意方式来对它们作出圆满的解释,而必须揭示行者举行仪轨时享用这些东西所隐含的指意过程(semiosis),必须理解这些物质在当时主流印度文化的主导语境下所意指的是什么?
显而易见,与“五肉”、“五甘露”接触绝对违犯当时印度社会最核心的洁净约束,所以在大瑜伽本续的仪轨和经典中对它们的指称,只可能构成一个故意的指意过程。它们意指令人厌恶和具污染的东西。而大瑜伽续的行者享用“五肉”、“五甘露”这两种供养表达的正好就是行者对于传统的净、秽二元范畴的超越,意指行者证得了[净秽]无二的觉悟状态。
若用通俗的话来形容这个涵指符号学的指意过程,即是:无二的觉悟状态?这可是真的:看我连 “五肉”和“五甘露” 都吃了。在这个解释体系中,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讲究“五肉”、“五甘露”是实指、抑或喻指,重要的只是它们的意指功能。作为符号的“五肉”、“五甘露”只是当它们在一个更高级别的系统中作为能指发挥作用的。而在外借符号的自然语言中,其实际的能指是随意的。所以,困扰现代学术的问题——它们是不是大、小便——实际上偏离了主题。作为直接所指的牛肉还是人肉的实在的真实性本来就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它们在作为讲话人的密教男女瑜伽士团体中所指的意义。
Wedemeyer引进涵指符号学的解释模式来诠释大瑜伽本续中出现的“五肉”、“五甘露”供养的意义大概还很难成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对此问题的共识,对于它的争论势必还将继续下去,但他的这种尝试无疑为我们解释密教提供了一条十分有启发意义的新进路。饶有兴味的是,上述Wedemeyer所讨论的佛教密续的解释模式也见于藏传佛教自身对如何理解密法仪轨、名相的讨论中。
藏族佛学家也曾提出过“实指”和“喻指”这两种不同的方式,甚至也提出了“涵指符号学”的方式。在见于著名的汉译藏传密教宝典《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篇萨思迦三世祖师名称幢所造的《大乘密藏现证本续摩尼树卷》中,我们见到了作者对 “如实作解”(sgra ji bzhin pa, 即如其名,即“实指”)和“随宜消释”(sgra ji bzhin ma yin pa,非如其名,即“喻指”)两种解释法的讨论。其中
一、‘如实作解’者,即‘母’等八亲,及‘婆罗门’等八类,通成一十六种,《本续》云‘亲母及亲妹’等八种亲,又云‘舞染金刚母’等八类是也。
二、‘随宜消释’者,将‘母’等八亲转成‘婆罗门’等八类。故《三菩提》云:‘为母二生佛,女是勇健母,妇成魁脍母,姊妹为舞母,染是姊妹女。’将‘世母’等八亲之名而转说成‘染’等八母。”而或可引以为“涵指符号学”者,于此被称为“连续灌顶者”(dbang dang rjes su ’brel pa,意谓“与灌顶相联结者”)和“等同功德者”(yon tan dang mthun pa,意谓“与功德随应者”),即将实修时的手印(dngos kyi phyag rgya)呼为母等,并成为其所具功德之象征。即曰:
三、‘连续灌顶’者,举一手印而具八体,将密灌顶手印而呼为‘母’等。四、‘等同功德’者,以是手印约功德体辨,每一手印具十六德,方成‘母’等,故《本续》前分第五品云:‘因生众生故,以智号曰母’。[32]
于此,手印只是一个涵指符号,实际所指则是佛母之功德。
此外,在同样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篇传自西夏时代的修法仪轨《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中,我们见到了作者对于依行手印密修欲乐定,得证空乐无二之理、成正等觉的一段解释性的描述,从中也可以看出上述诠释密续之修法的三种进路,即实指、喻指和涵指,于此都得到了体现和运用。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若依大手印入欲乐定者,然欲乐定中所生觉受,要须归于空乐不二之理。故今依大手印止息一切妄念,无有织毫忧喜,不思不虑,凝然湛寂,本有空乐无二之理而得相应,即是大手印入欲乐定、归空乐不二之理也。今依密教,在家人则依行手印入欲乐定,若出家者依余三印入欲乐定,契于空乐无二之理也。
问淫声败德,智者所不行,欲想迷神,圣神之所远离,近障生天,远妨圣道,经论共演,不可具陈。今于密乘何以此法化人之快捷方式、作入理之要真耶?答:如来设教,随机不同。通则皆成妙药,执则无非疮疣,各随所仪,不可执己非彼。又此密乘是转位道(lam ’khyer),即以五害烦恼为正而成正觉。亦于此处无上菩提作增胜道。言增胜力者,于大禅定本续(大修习本续、无上瑜伽本续)之中,此毋(母)本续,即为殊胜方便也。前代密栗咓钵师等依此路现身上而证圣果。《胜惠本续》云:下根以贪欲中造着道门而修习者,应当入欲乐定也。其欲乐定有十五门,若修习人依修习,现身必证大手印成就。[33]
显然,按照作者的本意,对于在家人来说,修欲乐定就是与手印母(明母、行手印)实修,故本篇之仪轨是实指;对于出家人来说,修的手印不是行手印,而是记句手印、法手印和大手印等其余三种手印,故不是与明母实修,而是观修,故对仪轨中的语言、符号我们都不应该按其字面意义,而应该按其喻指的意义来理解,它是喻指;而诸如“秘密大喜乐禅定”、“乐空不二”、“方[便]智[慧]双运”、“方智交融”和“大手印”等等,尽管内含不同的实修方法,但其本身即是“成正等觉”、“觉悟”和“成佛”的同义词,在这意义上说,他们都不过是成佛这一概念的涵指符号。
八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汉传密教研究和主流的密教研究(印度、南亚和藏传密教研究)基本上是相互脱离的,虽然对印藏密教的定义、历史建构和其象征意义的阐释等,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汉传密教的研究,但在西方学术界二者俨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不同的学科。
这样的格局和整个西方佛学界内汉传佛教,或称东亚佛教的研究与印藏佛教研究互相脱离的局面是一致的。然而,密教研究的进步显然必须依靠对印度、南亚、藏传和汉传密教研究的整合,只有将这些不同的密教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我们才能对密教的起源、历史发展脉络、变化过程等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才能最终脱离俗套的有机发展史观,重构一部更贴近历史真实的世界佛教史。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只有把汉传密教的研究当成整个密教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才能拓宽汉传密教研究的视野,弄清汉传密教的历史脉络,扩充汉传密教的内涵,推动汉传密教研究的进步。若完全脱离印藏密教传统,汉传密教势必成为一个受时代限制的、孤立的宗教现象,以至于其存在与否依然还要受到学者们严肃的质疑。
显然,要打破以往对汉传密教的这种理解模式,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积极开展汉藏佛学的比较研究。近年来,藏传佛教的研究,特别是藏传密教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无疑可以有力地推动汉传密教的研究。藏传密教是现存所有密乘佛教传统中最全面、最正宗的传承,也是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传统,而它与汉传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往人们更多地从印藏佛教的角度来理解藏传佛教,忽视了藏传佛教中所包含的汉传佛教的因素。
事实上,藏传密教的来源和早期发展或也部分地涉及汉传密教的成分。近年来,敦煌汉、藏文佛教文献研究的进步表明,汉、藏密教曾有互相影响和交融的部分。譬如,藏传佛教中的观音菩萨崇拜传统的形成或与汉传佛教中的观音崇拜传统有相当大的关联,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中与观音崇拜相关的文本有些显然与汉传佛教中的同类文献有类似之处。
不仅如此,藏传密教的形成和发展最初与敦煌有密切的关系。藏传佛教的密乘传统主要是在后弘期形成的,而其最初发源和发展的主要地区并不是吐蕃本土,而是以敦煌为主的中国西北地区。
最初的藏传密教文献皆出于敦煌地区,从吐蕃帝国于9世纪中的崩溃到西夏兴盛的12世纪,藏传密教于西域地区(今日中国的大西北地区)广泛传播、蓬勃发展,可以说藏传密教传统部分就形成和发展于西域地区,而其中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和它对汉传佛教造成的影响均毋庸置疑。
尽管和尚摩诃衍和他于吐蕃所传的汉传禅宗顿悟教法曾深受后世藏传佛教史家诟病,甚至被妖魔化,使得汉传禅宗教法在藏传佛教发展历史中的影响被后人忽视,但实际上藏传密教中的一些重要的修法,如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等都可能与和尚所传禅法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禅密同源之说或并非纯属空穴来风。此外,藏传密教修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气、脉、明点的修法,以前多被人与汉传道教的修法联系起来,甚至有人因此得出了道、密同源的结论。
事实上,我们很难将藏传佛教中的这些密修仪轨与道教中与其相类似的修法等同起来,或者断定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有渊源关系,即使它们之间有明显的相同之处。
因为藏传密教中的这些密修方法都有其明确的印度渊源可循,它们大都有传自印度的文本可依,故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例如,藏传佛教中的“大手印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教法和密修体系,其中有显教的成分,也有密修的成分,[34] 其中显教的成分或与汉传禅宗佛教有一定的关联,而其密修的部分,即其修法之精髓《那若六法》(Narō chos drug)中的修行部分,或有与道教的某些修法相类似的成分。但不管是显教的大手印,还是密教的大手印,我们在印度佛教文献中都能找到其源头。
同一种文化、宗教现象出现于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之间不见得一定有历史的渊源关系,不见得不是你传给我,就一定是我传给你。它们也可能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发生和成长起来的类似的文化和宗教现象。但是,对印、藏、汉所传密乘佛教传统中的这些现象作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无疑是推动密教研究进步的一条可靠的道路。
藏传密教在西域和中原地区的传播曾经对汉地密教的进一步流行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这些年我们对黑水城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如前所述,如果按照藏传佛教对密教的四大部类分法,那么汉地出现无上瑜伽部密乘经典的翻译是在宋代,当时著名的译师施护和法护等人至少翻译了属于父续的《密集》和属于母续的《喜金刚》等大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的密典。但是,由于他们的这些译本本身质量不高,其中还有大量的删节,令人难以卒读。而且,由于唐代汉传佛教中的密教传统未曾接续下来,汉地佛教徒缺乏理解和修习这类密乘修法的传统和背景,故它们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较大的关注,更谈不上流行,所以它们对汉传佛教中密教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是,近年来我们陆续发现了一批自西夏、至蒙元、到明代所翻译的无上瑜伽部密教经典,其中包括《喜金刚》、《胜乐》、《三菩提》等本续及其重要释论和修法的汉文和西夏文的译本。这些汉译密教文献的发现和对它们的研究,有望帮助我们彻底改写汉传密教的历史。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的大部分典籍和修法,及至明初早已经在汉地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它们不但吸引了大量西夏、蒙古和汉族的信众,而且也对汉传佛教造成了冲击。元、明两代汉族士人对藏传佛教的尖锐批评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它们对这种激烈的冲击的回应和抵抗。更值得一提的是,汉传佛教也并非对藏传密教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相反早在元朝初年汉地就已经出现了显密圆融的尝试,出现了将汉传的华严教法和藏传的密教修法同时并举,圆融如一的努力。[35] 总而言之,藏传密教在西夏、蒙元和明代传播的历史应该是汉传密教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传密教的历史应该把属于无上瑜伽部的藏传密教传统自西夏时代开始在广大的西域地区和中原汉地传播的历史吸收进去,把它作为汉传密教史的一个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