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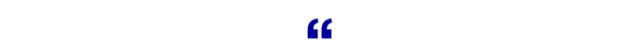
她喜欢这种被包裹的感觉,温软绵实,这从子宫带来的记忆,让她有种虚幻的安全感。


1.钻戒
李万山坐在出租车里,手肘搁在半开的车窗上,手里的香烟半明半灭发着幽微的光,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准备随时发动攻击,他对着窗外一点拨,几片烟灰便追逐着夜风嬉戏打闹去了,他又把烟送到嘴里,猛吸了一口后,一股白烟顺着呼吸的节奏喷在手机上,屏幕里那张让他血脉贲张的颜靓奶大的比基尼美女图片立刻就蒙上了一层朦胧,他用手一挥,氤氲缭绕的烟雾像受惊的麻雀四散逃窜。
他把眼睛从屏幕上挪开,看向窗外灯火通明的温泉酒店,复又瞄了下手机,状态栏里那个芝麻点大的数字刚刚又跳了一格,已经是晚上十点四十了,他疲倦地搓了搓脸,叉掉了浏览中的图片网站,正犹豫要不要给那个女人打个电话,手机立刻心灵感应般发出一声叮铃,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APP推送的资讯,是一条短信。
看了下号码,正是之前坐他车的那个女乘客发来的,对方告诉他可以回去了。
半小时前,李万山开车从市里送一个年轻女人来到这家远郊酒店,女人很漂亮,化着妆,打扮得时髦亮眼,跟他在“图片网站”上看到的那些性感尤物差不多,这样漂亮的女人,大半夜一个人去郊外酒店,不用问也知道她是来干嘛的,不过这些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只是一个开出租的,只要客人肯付钱,去哪儿都不干他的事。
退出信息,李万山轻笑了声,掐灭香烟,把手机放进储物盒里,扭动钥匙,发动汽车从酒店前边的草坪上离开。从这里回市区大概要四十分钟,明天就是国庆节了,长假前的这一夜很有可能会堵车,一旦开堵到家恐怕就得到后半夜了,他又想起了另一件事,下午的时候,女儿打电话告诉他,今晚可能会从学校回来过节,原本他还在想要是时间赶得上的话,自己就开车过去接她,一来安全,二来又能省一笔出行费,现在看来只能让她自己搭车回家了。
车子像一头孤独的鲸,扎进了风烟弥漫的夜色里,离身后孤岛似的远郊酒店越来越远,路灯照耀下,依稀可以看见远处大片的城乡接合部景象,因为远离市区,这一截车流量并不多。风从半开的车窗外鼓进来,温柔而缠绵,像一只女人手触摸着他裸露的皮肤,撩拨着他的思绪,一阵清凉从毛孔渗透到四肢百骸,通体舒泰。
估摸着开了十几分钟,两侧景致逐渐有了变化,一幢幢跟风而建的高楼彻底被低矮的民宿所取代,农田和树影不断延伸拉长了夜的边界,他减缓了车速,调转方向盘准备从前边的水泥路直接斜拐走高速,驶过岔路口,车灯照射下的路面出现几道不规则的车胎滑痕和一些车里常备的小物件,李万山心里一个警觉,粗略地往地上扫了一眼,那几道鬼爬似的痕迹纠纠缠缠消失在几十丈远的洼地里。
李万山脑子里闪过几个念头,作为一名老司机,直觉告诉他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犹豫了几秒,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靠边停了车,拿起手机,打开车门,踩着狰狞的滑痕向前走去,几秒过后,在手电筒圈起来的区域里,一辆四脚朝天的黑色小车浮出了水面,犹如一只被雷劈死的巨龟。
李万山不由吸了口凉气,呆呆地注视了几秒后,蹲下身,从草堤上跳了下去,踏着簌簌作响的杂草枝杆,来到那辆四仰八叉的轿车前,借着手电筒的光,他重又审视了一下出事的轿车,并不是多名贵的轿车,但也不是自己这样的家庭条件能承担的。
他走到一旁,用手电筒对着车厢照了照,这时,一张布满血污的脸像拉盖中奖了一样跳出来,是个年轻男人,约摸三十来岁,斑斑血迹在白T恤上洇散开宛如雪地里盛开的红梅,李万山明显感觉到心跳加速起来,出于救生的本能,他轻轻喊了两声,无人回应,他想这人多半是没命了。
他后退了两步,拿起手机准备报警时,一下又犹豫起来,那些被讹诈的社会新闻成堆成堆地在脑海里涌现,这一个电话打过去,要是运气背的话,保不齐明天出现在新闻里被网民围观的就是自己,趁着犹豫不决的几秒,他再次打量了一下车主,不看还好,这一看他彻底打消了报警的想法,男人胀鼓鼓的裤袋里一个神秘的磨砂盒子调皮地露出了半个头。
李万山放下手机,怔怔地看着那个磨砂盒子看直了眼,看着看着他的手就不自觉地伸了过去,稍一用力,那物件便发生物理位移来到自己手里,打开盒盖,李万山眼睛迅速被里头的东西点亮了,定眼一看,竟是一枚星子般的钻戒,一看克数就不会少,要是真货,他即使几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啊。
收好手机,李万山打定了注意,攥着小铁盒从原路返回,心里惊慌如鼓,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害怕。来到车旁,他不无心虚地朝附近张望了一眼,周遭无人无车,这无疑给了他下定决心赌一把的勇气。
引擎声在耳边响起,李万山抬头看了眼澄明的天空,今晚的月亮可真圆啊。
2.偷情
杨存手扶着方向盘,背靠在座驾上大口喘气,白格纹的杰尼亚衬衫被汗水浸得通透,像吸过水的贴纸粘在后背上随着呼吸起伏,阵阵眩晕感伴随蜂鸣般的脑噪声袭来,让人有种灵肉剥离的错觉。
他胡乱地抹了把汗,尝试着把车门打开,结果推了两次都没成功,该死,他的手还在不住地发抖,像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过了几分钟,他再次推了推紧闭的车门,“咔哒”一声,这次门开了。杨存挪动身子,从冲斥着酒精气味的狭小空间里出来,走到裸露的公路上,清冽的月光下,他看到自己的影子仍在不停颤抖,致命的危险已经过去,与死神吻肩而过的后怕却仍盘踞在心头。
风摩挲着树叶,云块在穹顶之上漂移,汗液蒸发带来的凉意像一桶冰水贯头而下,让他瞬间清醒了不少,理智再次占据大脑,双眼像探灯一样有目的性地朝附近扫视起来。
他向前走了几步,单调的叩击声听起来有些刺耳,左前方是一片洼地,倾斜的泥坡上爬满了杂草,那辆刚才险些与他相撞的黑色奥迪车就躺在下面,四脚朝天,毫无动静,他吸了吸鼻子,一股混杂着汽油、草汁、淤泥甚至血液的古怪气味逗留在四周,让他感到一阵恶心。
他连忙蹲下身,坐在草堤上干呕了一阵,除了一点胃液,也没呕出什么东西,与此同时,手机响了,在裤兜里,突兀得像来自某个异空间,他喘了口气,手伸进去掏出手机一看,是他的情妇辛娟打来的。
他凝视着屏幕中心那个不断变换颜色的名字,手指一滑,接通了电话。
“喂,我到酒店了,你过来了吗?”
一个年轻的女声钻进耳朵,甜腻腻的,带着一丝讨好的意味。
他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兴趣索然道:“改天吧!我今晚有事......不过去了。”
发生这样的事无疑是扫兴的,他开始有些懊悔起来。
“哦。那好吧。”
女人有点失望,但迫于身份,终究也没多说一句。
挂断电话,杨存心情愈发变得焦虑沉重,他把手机放进兜里,起身朝四周看了一眼,迅速朝自己座驾走去,下车前他有想过报警的,可就在刚才他临时改了注意,如果报警的话,酒驾撞车先不说赔偿拘留那些让人头疼的事,至少自己找小三的事情也要暴露了,搞不好事情闹大了还会牵连到自己公司......以上种种,都是他绝不愿看到甚至想都没想过的事。
别无选择。
那么。
逃吧!
钻进车里,扭钥匙,踩离合,挂挡,轰油门,一气呵成,听到引擎声响起,杨存感到心安许多,还好只是撞坏了保险杠,发动机并没有问题,前轮卷起朵朵泥花,憋着劲儿从积水的泥坑里倒回到公路上,打了个颤儿,座驾上的手机跟着振了振。
十点五十五,他看了眼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就是国庆节了,这个时候回去,该编个什么样的谎话给老婆听呢?
3.指路
迎面开来的一辆奥迪车打着远光灯,刺得钟小军一眼的满天繁星,他拿手挡了一下,五官一拧组成一副嫌恶的表情,心里早已开骂,奥迪车忽然停在他旁边,车窗玻璃徐徐降下,一个年轻男人从里面探出脑袋,朝钟小军招了下手。
“嘿,哥们。去宁野苑怎么走?”
男人梳着油头,戴着墨镜,露在车外的半截手臂文着一个巨大的佛头,由于皮肤拉伸过度,导致宝相庄严的佛像此刻看上去像是凶残的般若。
钟小军显然没有反应过来,等他睁开眼时,最先看到的不是那个男人,而是自己映在奥迪车锃亮外壳上的身影,干干瘦瘦的,样子有点猥琐,跟眼前这个有着两块菠萝一样大的胸肌的男人截然相反。
男人见他发愣,又问了一遍。
“问你话呢,哥们。到宁野苑怎么走?”
语气还好,不至于让人生厌。
钟小军忽然自惭形秽起来,像偷盗被人抓了个现形,不自觉地把手插进裤袋,上下打量了男人一眼,心里那些鬼鬼祟祟的促狭念头开始冒出来,他定了定,抬起青筋浮凸的手臂指着反方向道:“哦。看到前面那个牌牌没?往那个方向开,大概二十来分钟就到了。”
男人隔着墨镜冲钟小军点了点头,似乎并没怀疑,升起玻璃,车轮滚动,往他手指的方向开去。
等车子开远,钟小军收回了目光,脸上挂着恶作剧达成的狡黠笑容,继续在街上溜达,他已经失业小半年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常状态下每天除了吃喝拉睡就是四处游窜,逮到机会就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如果不是一个礼拜前辛娟突然提出分手,他还准备继续游手好闲下去。
说起这事,钟小军心里就有一股暗火,作为被分手方,他不仅被迫承担了接下来可能长达数月找不到工作的风险,还在全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女友指着鼻子骂成了一文不名的混蛋,更可气的是,他事后才知道,那个死女人早就已经找好下家了,那场在谩骂和哭闹中收场的分手,不过是她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说起来前女友的劈腿对象他还见过,三四十岁,开着跑车,打扮得人模狗样,应该是个小企业家,看起来就跟刚才被他捉弄的那个男的差不多......
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个街区,一辆公交车的锐叫将他的思绪拽回现实,他边走边拿出手机看时间,十点半了,再有一个多小时这一天又过去了,对于即将来临的国庆节,钟小军内心可以说毫无波澜,所谓的长假对他而言就跟平常一样,不值得留意,也没什么好精心安排的,他的生活不会因为这几天假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但对困居都市的上班族来说,这绝对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狂欢盛宴,受欢迎程度仅次于春节,汹涌的人潮和彻夜不熄的霓虹灯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放眼望去,随处可见嬉戏打闹的小情侣以及他们浮夸表演式的争吵,还有一簇一簇来不及看清面貌就很快消失的人群和他们正在进行的不知是离别还是重聚带来的肢体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