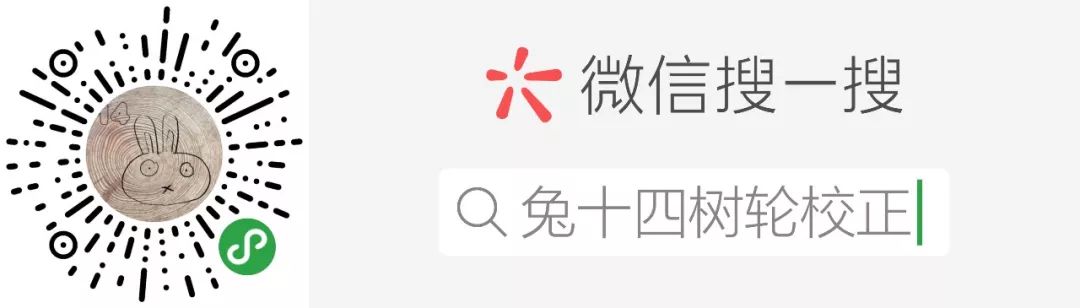你好,这是本兔的第
83
篇推送。
一个人摸爬滚打了两年多,本兔也
终于约到别人的稿件了!
本文来自我优秀的师弟
宋殷
同学,原文上下篇发表于
《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2015年64期和66期
。
有幸拜读过,洋洋洒洒四万字,阐述了残留物分析的发展历程和技术细节的方方面面,旁征博引,极尽详细。
本公众号得到作者授权转载,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看到并与我们讨论。
由于原文较长,特拆分为六篇连载推送。
现在您看到的是第六篇,包含原文的第六-八章。
六、有機殘留物分析在中國的介紹和應用
最早在中國引入殘留物概念的是陳星燦先生在1998年10月11日的《中國文物報》上發表的《遺留物分析能告訴我們什麼》
[137]
,這之後呂烈丹先生
[138]
、楊益民先生
[139]
、關瑩
[140]
、周昱君
[141]
等分別從殘留物的整體上和石器上殘留物以及藥物殘留物上進行了綜述。值得注意的是,呂烈丹先生首次在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檢測了石器上的植硅體和澱粉粒,從而使得該報告成為國內首部包含殘留物分析檢測的考古報告
[142]
。
經以上諸位先生的努力,國內考古學界對於殘留物分析這一概念有了基本認識,但是對於殘留物分析研究的實施仍有較大難度。首先,殘留物分析方面的專業人員匱乏。由於殘留物分析的對象涉及植矽石、澱粉粒、血液、蛋白質、動物毛髮、DNA、脂肪酸、有機小分子等,這需要分析者具有相應的知識儲備和具備技術分析能力和技術條件,而這些在現有的科技考古人員培訓中都是難以全部獲得的,其導致的結果必然是每個研究者專攻一項。這樣的研究一方面在基礎理論和實踐方法上大力引進西方技術手段,另一方面和國內的考古學界合作多傾向於個人所專業的狹小領域,很難綜合、立體而全面的揭示古代人類活動行為。其次,國內考古學界缺少對將殘留物分析系統引入考古學界的深入分析。中國的考古學界仍然缺少從發掘設計就將殘留物分析考慮在內并包含有殘留物分析和相關研究的報告與論文撰寫。殘留物分析的研究者們多為了獲得材料而往來與工地和實驗室之間,缺少對於考古學問題和實踐過程的關注與思考。相比而言,國外的考古學界早已將氣相色譜-質譜聯用法(GC-MS)作為研究考古問題的一種方法
[143]
并廣為考古學家們所了解,這也是與國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有機殘留物基礎研究和將其向考古學領域推廣分不開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有機殘留物分析領域,相關高校和科研院所對其關注度依然有限
[144]
,
[145]
。崔品對可能影響脂類分析的各種因素進行了探討,得出取樣、溶劑提取和洗脫過程中需要將樣品與有機環境(如塑封袋、報紙、醫用塑料手套、未重蒸兩遍的有機溶劑和非去離子水等)嚴格隔離的結論。同時,崔品對滲入陶片內壁的殘留物進行試分析但沒有獲得理想結果(檢測出的殘留物含量很少),於是轉而檢測土壤中的有機殘留物并嘗試通過其檢測結果揭示古環境的一些信息
[144]
。周昱君利用頂空進樣法和超聲波提取法對蚌埠雙墩春秋一號墓出土的彩陶樣品進行了有機殘留物的分析和提取,但實驗過程中遇到了可能來自取樣包裝等的污染問題且未檢測出可對應植物種屬的標誌性化合物而只是得到了屬於植物類的脂類分子
[145]
。
由以上兩項研究我們可以看出,排除污染是從取樣、提取到分析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同時,與國外針對陶器上的殘留物蓬勃發展的趨勢不同的是,國內對於從陶片上檢出殘留物仍然較為困難(檢出量太少),是今後開展陶器上的有機殘留物分析的一大難點。
七、前景與展望
理查•埃佛謝德(Richard P. Evershed)在他2008年發表的著名的《考古學中的有機殘留物分析:考古生物標誌化合物革命》綜述中列舉了8項有機殘留物分析的未來發展方向,現將其翻譯如下:(1)利用軟電離方法發現高極性或高分子量生物標誌化合物;(2)通過使用選擇性離子或選擇性反應檢測技術提高檢測生物標誌化合物的靈敏性和選擇性;(3)在生物標誌化合物的特定化合物的穩定同位素研究中加入氮、氘和氧的同位素;(4)將生物標誌化合物分析融入到放射性碳測年中;(5)更高程度上與分析技術融合來提供有機殘留物定性和定量的組成;(6)增加實驗考古工作來增加我們對於有機殘留物形成和保存方面的認識;(7)增強有機殘留物的信息與其它考古證據的融合;(8)統計上有意義的大量系統抽樣,積累數據庫
[146]
。
鑒於有機殘留物在國內的一些應用實例,我個人認為如下幾點是國內進行有機殘留物分析的學者們需要注意的問題。
第一、關注陶片上的有機殘留物分析相關研究。陶片是史前和原史時期考古學研究中出土最多的遺物,對於陶片的研究也是考古學研究尤其是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如類型學研究、產源研究、製作工藝研究等),對於陶片上的有機殘留物分析也應該引起中國考古學界的重視。在中國考古學憑藉陶器類型學方法樹立了各地的年代標尺之後,陶器的生產和流通成為了學界關注的對象;但是在有著悠久飲食文化傳統的中國,通過有機殘留物分析復原古人宴飲過程和飲食習俗將是未來陶器研究中的重點。在進行陶器上的有機殘留物研究之前亟需我們對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域的陶器質量有一個總體評估,以估計不同陶質的陶器可被檢測出的有機殘留物含量,否則在確立陶質這一標準之前任何對於陶器上有機殘留物的分析都只能是“盲人摸象”。
第二、關注可能應用于考古材料分析的高靈敏度的檢測技術方法。由於可確定動植物種類的生物標誌化合物本身在動植物體內含量就有限,經過加工殘留在工具或容器中的這類化合物的含量就更加微乎其微。若要檢測出這些有著判斷動植物種屬價值的化合物,必須在從取樣、提取和分析中每個環節都盡力做到提高樣品中殘留物的提取效率。因此,研究者們需要對比不同的提取和分析方法以具有針對性的確定適用於一類生物標誌化合物的檢測方法。
第三、注重科技考古學者和考古學家之間的交流。由於有機殘留物分析的取樣環節需要在清洗和拼對陶片之前進行,與考古學家之間的溝通交流和對發掘過程各環節之間的調整就成了科技考古學者進行有機殘留物分析必須涉及的問題。另一方面,考古學家尤其是動植物考古學家也要向進行有機殘留物分析的學者提供完整的考古背景信息(如對動植物遺存的分析結果),以幫助後者縮小研究所要關注的動植物種類範圍。
八、餘論
通過綜述考古有機殘留物分析的研究方法,筆者發現外國學者在進行這一研究時有一定的特點。由於在埃及、兩河流域的文化傳統中小麥等植物類食物的烹調方式多以烘烤為主,很難留下殘留物分子,而多留下澱粉粒等微觀殘留物。而這一文化傳統中肉類的烹調有可能利用陶器,故而西方學者多研究動物脂肪酸以確定所烹調的動物種屬。此外,對於葡萄酒和乳製品的研究也反映了這一區域文化的飲食傳統。這一現象提醒我們在利用有機殘留物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國國內的考古材料時需要從本地的飲食文化傳統入手。
從陶器類型學的角度看,鼎、鬲、甗等炊煮器可以烹煮多種動物,這其中不同型的陶鼎、陶鬲或陶甗是否用於烹煮不同類的動物種類可以通過脂肪酸比值法的方法揭示出來。比如在商時期陝西周原地區發現的“高領袋足鬲”和“聯襠鬲”是否被用於烹煮特定動物即可以通過這種方法解決。此外,生活在中國的古人對於發酵這一食物加工技術有著悠久的傳統。由於從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期發現有大量的陶容器,這些陶容器是否都是用來盛酒或水的,何時出現醋和醬,釀造這類物質的工藝如何,如果結合一定的微生物學知識,這類問題都可以通過有機殘留物分析方法解決。
何種陶器用於何種用途目的的使用只是利用有機殘留物分析方法解決考古問題的第一步。通過和考古學家的合作,科技考古學者可以利用這一技術方法在一個較大的時空範圍內解決烹飪技術的起源和擴散傳播等問題以及是否存在和陶器群不完全重合的“烹飪群”(烹飪群在此指不同區域使用相同烹飪技術如醋醬的使用而組成新的飲食文化圈)。
然而,在大規模使用這一方法之前考古有機殘留物分析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需要對大量陶片樣品進行長時間的分析測試且所有陶片出土後不能和裸手直接接觸。對於需要在短時間內確定所發掘出土陶片的陶器群面貌和文化性質的考古工作者來說,考古有機殘留物分析方法不可避免的會淪為“點綴”性的工作。因此,從事這一分析方法的科技考古工作者需要深入到發掘第一線且需要配備可攜式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GC-MS)。同時,檢測時間也需要縮短,這需要科技考古工作者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經歷來“研發”最方便、便捷、可行的現場檢測方法。此外,由於脂肪酸可提供的資訊有限,且不是所有陶片樣品均可檢測出結果(有機分子殘留物的檢出存在概率性),考古工作者不太可能通過寄希望於這一方法得到百分之百可信的所烹飪的動物種類資訊,而需要將分析結果與動物考古的鑒定結果比較得出結論。
作為在國內剛剛起步的分析方法,筆者認為對發酵產物的分析研究將是未來中國科技考古界在這一領域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即對被吸附於陶片上的發酵產物進行實驗考古和埋藏學研究。
参考文献
[137] 陈星灿:《遗留物分析能告诉我们什么》,《中国文物报》,1998 年10月11 日.
[138] 吕烈丹:《考古器物的残余物分析》,《文物》,2002年第5期,83-91頁.
[139] 楊益民:《古代殘留物分析在考古中的應用》,《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20-25頁.
[140 ] 關瑩、高星:《舊石器時代殘留物分析:回顧與展望》,《人類學學報》,2009年11月第28卷第4期,418-429頁.
[141] 周昱君、張居中:《藥物殘留物分析技術的考古學應用》,《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158-163頁.
[14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桂林甑皮巖》,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第646-651頁.
[143] Andrew Jones, 2001,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scientific practic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4] 崔品,《脂類物質分析技術運用於考古學的方法探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3月.
[145] 周昱君,《蚌埠雙墩春秋一號墓出土彩陶器有機殘留物初步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5月.
[146] Evershed, R. P., 2008, Organic residue analysis in archaeology: the archaeological biomarker revolution,
Archaeometry
, 50(6), 895-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