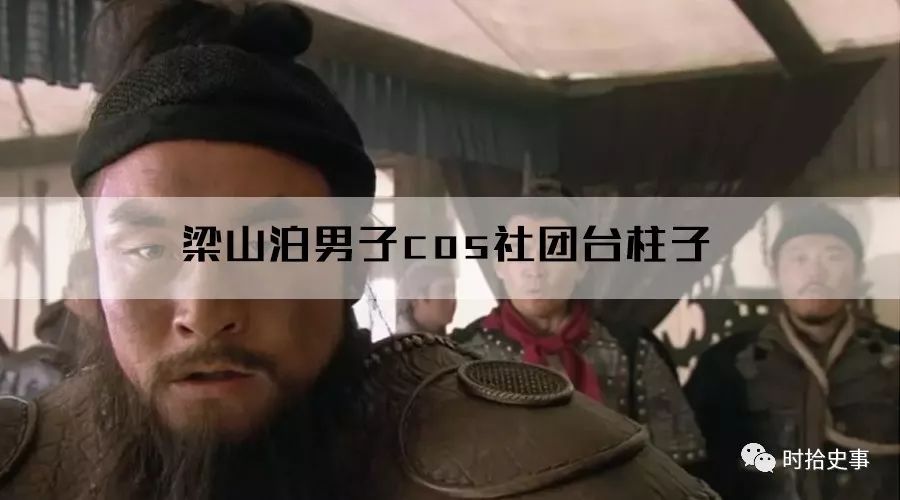宋代周密撰《齐东野语》有专门的一节名为《避讳》,读过之后,感叹于古人“讳”网越织越密,有为之蹙额,为之可惜、也有为之拍案而笑的地方。

避讳之举在殷商之前是没有的,到周代才露出端倪,而到秦才成为一项制度。
秦始皇名政,由于避讳,每年的正月改为征月,而在秦代凡颁布新法端正法度,也被说成“端直”法度。
自此而往,避讳成为各代一项重要的制度,且越织越密。
避讳首先避的是尊者的讳,也就是避皇帝及皇帝先人“讳”
。
人名、官职、普通事物,包括自然界的山山水水,不能有与皇帝及其先祖名字相同的字。
大臣们的名字中的字有与皇帝名字中的字相同的,当然也要改!
别说改名字,如果大臣姓氏与皇帝的名字中的字相同,还得改姓。
唐代宗时期,因为名字中出现豫或与之相同读音的字,大臣苏预改名为苏源明,唐宪宗名“纯”,当时名字中含纯或与之读音相同的字的大臣还不少,统统都得改名:
韦纯改名为韦贯之,韦之纯改名为韦处厚,王纯改名为王绍,陆淳改名为陆质,柳淳改名为柳灌,严纯改名为严休复,李行纯改名为李行谌,崔纯亮改名为崔行范,程纯改名为程弘,冯纯敏改名为冯约。
改名还好说,还有普天因国君的名字改姓的,五代时,晋高祖名石敬瑭,因此敬这一姓氏要改,都被改成了文氏、苟氏,一直到后汉才恢复。
不仅本朝当时的大臣的名字要改,就是著书历史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的名字也要改。
汉景帝名启,因此《史记》司马迁在写到微子启的时候,改成“微子开”,不仅微子启,庄子也改了一把名,因为东汉明帝名庄,因此老、庄这一组合在当时变成了“老、严”。
不仅是事物,连官职也得避皇帝及其先祖的讳。
隋文帝的父亲名杨忠,因此官职中凡郎中的都得改,侍中改为侍内,中书改为内史,殿中侍御改为殿内侍御。
设置侍郎的时候,不设置郎中,御史大夫也不设中丞,以侍书御史代替中丞。
唐太宗李世民时,“民部”也因避讳改成“户部”。
为避讳,一些寻常事物的名称也得改。
大家都知道的是因为汉吕后名雉,因此,我们现在说的野鸡,才没有一直按照汉之前的叫法叫为“雉”,当时“雉”改为“野鸡”是避吕后讳,但也就流传下来了。
而因为同样的原因流传下来的事物的名称还有不少:
南北朝时梁武帝小名叫阿练,因此当时被称为“白练”的绢布也就因避讳改成了“白绢”,现在说“白练”未必人马上知道,但说“白绢”却是人人都懂的。
还是因为唐代宗,还是因为他名叫李豫,要避讳,当时的薯蓣改名了,改成了薯,也叫山药。
如今山药人人都知,说薯蓣却在未必每个人都知道。

山的名称有与皇帝名字相同的字怎么办?
改。
邦郡、城邑、县治的名称与皇帝的名字有重字怎么办?
还是改。
汉文帝名恒,因此,整个国家要讳“恒”字。
当时的恒山也就改为常山。
魏愍帝讳业,因此,当时的建业也就被改为建康。
隋炀帝名广,因此,国家也就要讳“广”,当时的城邑广陵也就被改为“江都”。
唐玄宗名叫隆基,因此隆州改成了阆中,隆康也改成了普康。
唐代宗名豫,豫章因此被改为金陵。
唐宪宗名纯,淳州因此在当时改成了栾州。
一开始避讳避的是皇帝及其先人的名讳,但因避讳和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对有权势者尤其是有大权势者也要避讳:
避太子的讳,避皇后的讳、避诸侯的讳,乃至还有的要避皇后娘家的讳。
三国吴太子讳和,因此和兴改名为嘉兴,唐高宗太子讳弘,尽管被武后鸩杀,但被追尊为孝敬帝,因此当时的弘文馆改成了昭文馆,弘农县也改为恒农县,时大臣李含光本姓弘,改姓了李,当时的曲阿弘氏全部改为洪氏。
唐武后讳曌,因此当时的诏书被改称为“制书”,大臣鲍照也改名为鲍昭,同时,皇后的先人也逐渐享受这一荣宠,唐武后的父亲讳华,因此华州改名为太州;
宋章献太后的父亲讳通,因此当时的官职通直郎改为同直郎,通州被改为崇州。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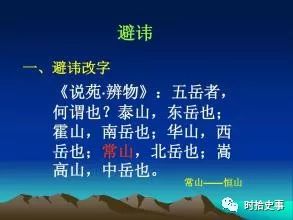
当然,不只是大臣为皇家避讳,有时,皇家也考虑褒奖大臣为大臣“避讳”。
书载:
后唐的时候,大臣郭崇韬的父亲名弘,因此弘文馆被改名为崇文馆。
宋太祖建隆年间,慕容彦钊、吴廷祚被任命为宰相,但慕容的父亲名章、廷祚的父亲名璋,因此代表宰相职务名称的“同为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同为“二品”。
古时,当然有一种避讳还是蛮有情怀的,那就是避贤者讳。
如,颍州在宋时有浩然亭,当时,被官员改为孟亭,在歙县有任昉寺,任昉村,也被官员改为任公寺、任公村,为贤者讳,不直称先贤的名字。
但纵观历史,避贤者讳温情的温度毕竟有限。
避讳的寒风越刮越紧,其发展犹如一张网,历史越往后,网织得越密。
不仅要为皇家避讳,还要避诸侯、大臣的讳、避长官的讳、避大臣的家讳,避讳也产生了不好的后果。
由于避讳,历史上也发生过许多让人叹息的事,最为著名的是诗鬼李贺,因为父亲名为“晋肃”,“晋”与“进”同音,因此在当时讲究避讳的情况下,被人抓了把柄,李贺一直难以参加进士的考试,尽管有韩愈等为之辩护,自身也才华横溢,但终究无缘登科。
李贺的事还是小的,至少他损失的是身外之物,而有人为避讳之事,还丢了性命。
书载后唐天成年间,卢文纪为工部尚书,郎中于业来参拜他,卢文纪因为自己的父亲名嗣业,于业的名字犯了卢文纪的家讳,卢文纪没有见他。
于业因此忧郁畏惧,生病了,得了抑郁症,一天晚上,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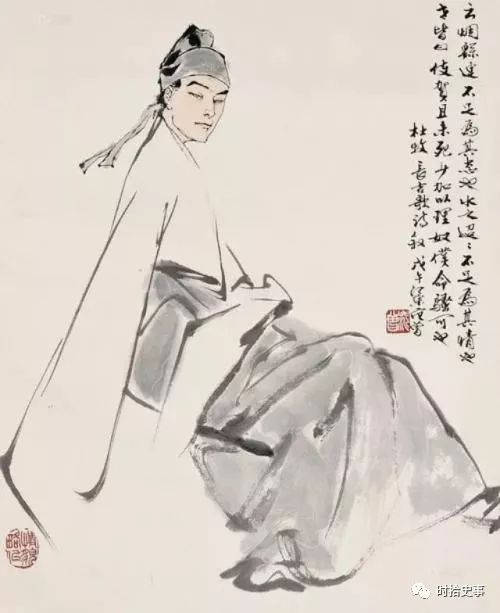
有因为避讳自杀的,当然也有不鸟避讳的。
宋钦宗宣和年间,徐申对于自己的名字看得很重,“自讳其名”。
在常州任知府的时候,一名县令来汇报工作,开口就是“已三状申府,未施行”。
县令说工作已经三次汇报到了州府,但没有得到施行的批准,县令是来催着办事的。
徐申听没听进去县令的催促之音,不敢肯定,但“申”字他听进去了,这是可以肯定的。
于是,他责备县令,“君为县宰,岂不知长吏名,乃作意相辱。
”怪县令应该避自己名字的讳,不该提“申”字。
没料到,县令是个驴脾气,不鸟他这一套,反击他说:
“今事申府不报,便当申监司、否则申户部、申台、申省、申来申去,直待身死即休。
”说完,做个大揖而退。
不让县令说“申”,不料县令一口气说了七个“申”,还加一个谐音的“身”字,当时,徐申的心情和表情可以想见,但也拿县令毫无办法。
回到本文的标题,也源自一则故事。
北齐的时候,有一名名叫熊安生的人,通报自己的名字想拜见大臣徐之才、和士开。
看到熊安生的名字后,徐之才、和士开四目相对,因为徐之才讳熊、和士开讳安,熊安生一个人的名字触犯了两个人的名讳,因此,两人将熊安生称为“触触生”,在场大臣无不大笑。
古代“讳”网越织越密,犯“讳”犹如社会上的一个个“井坎”,人们即使尽量小心,但也难免会陷进去。
可以想见,在古代,出现熊安生这样的“触触生”绝不奇怪。
参考书:
中华书局《齐东野语》
作者:耒耜读史,读史多年,其间,有所学、有所感,也有所悟,历史浩淼,将继续读下去!
图片来源于网络
喜欢本文/作者,文末赞赏一下表达支持吧!

本账号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账号
点击图片阅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