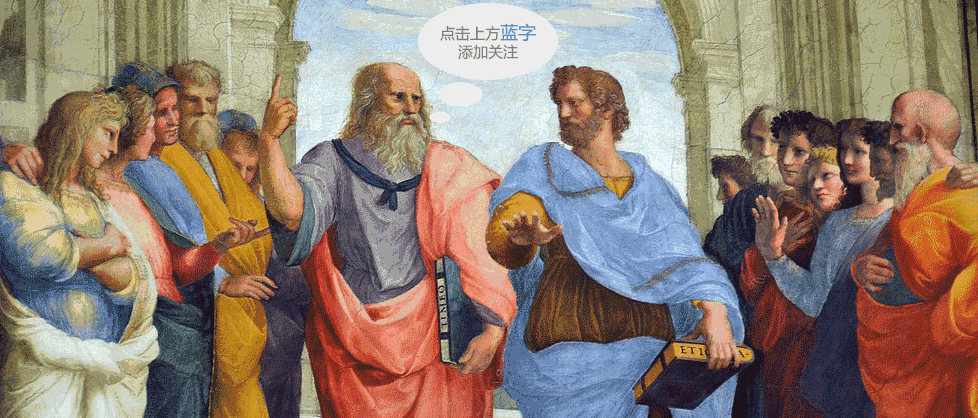
绝对精神的喜剧与自我意识的悲剧
本文选自《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编译者前言

一
在欧美学界,随着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研究的兴起,科耶夫作为跟两位思想家均有密切来往和深刻对话关系的思想家,也逐渐受到重视,研究文献日见增多。由我承乏编译的这个选本,便是围绕科耶夫的
“拉丁帝国”理念,搜集相关研究论著而成。
“拉丁帝国”是一个跟国际政治有关的理念,科耶夫提出这个理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是在他写给当时法国政治领袖戴高乐的建言书《法国国是纲要》里面(科耶夫的不甘寂寞和用世野心人所共知——据伯林说,他其实也给斯大林写过人民来信,但结果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在这份颇具纵横家气息的建言书中,科耶夫对当时的国际格局做出了判断:苏联和美国作为两个巨大的政治实体,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学和国际法理念所约定俗成的“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两个可以对全球施加影响的“帝国”。尽管“冷战”和“两极对立”之类名词的出笼还得再等些时日,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所有国家最终都得在这样一种格局之下,在两个“帝国”的勾心斗角之中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和前途。科耶夫对当时亚、非、拉正如火如荼的、以民族为名义的法理独立运动究竟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他给戴高乐开出的应对方略却是,法国不可以再固守民族国家的旧梦,她应该利用自己在拉丁诸民族(主要包括法兰西、意大利和西班牙)当中的领导地位,利用罗马天主教所塑造的共同精神和文化资源,同时也利用自己在二战之后即将从德国获得的巨大经济优势,联合相关的欧洲国家建立一个拉丁精神取向的“拉丁帝国”,以此来跟苏联所主导的斯拉夫—苏维埃帝国和美国所主导的英美帝国分庭抗礼,瓜分世界的统治权。即便是听传说,人们也都知道科耶夫是所谓“普遍均质国家”理论的炮制者,实际上也是当今世界正在流行的各种或精巧或拙劣的全球化理论的重要源泉。——什么是普遍均质国家?这是科耶夫对未来世界人性状况和生活景观所做的一种全面设想,1930年代在巴黎讲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时候首度提出,后来又在成书于1943年的《法权现象学纲要》里面全面充实。这种国家,如果用一种漫画或者科幻的手法来说就是这样:如果地球可以切割,如果恰好有一个人(实际上,科耶夫认为这个人就是自己)手里有那么一把刀能够切割地球,那么,他就可以不必在乎历史上或者现实中所存在过的或者正在存在的任何界限(比如今天所存在的国界和所谓的族群认同),随兴之所至地从任何一个地方切下去,然后再从另外一个他喜欢的地方切下大小相等的另外一块,再将这两个部分对换。结果他会发现,普遍均质国家状况下的人们,除了可能会存在的自然性差别之外,比如语言不通(或许到时候全球就只用一种语言了——如果考虑到科耶夫在构想拉丁帝国的时候曾经说拉丁诸民族之间的语言,只要学会其中一种则另外各种都可以很容易学会这点,那么,如上的推理科耶夫应该也是同意的)或者面目陌生这样一些自然性的原因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不会存在任何困难。到时候人们会发觉,自己原先头脑里面所保存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忘记,都可以毫不困难地被现实环境改造。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固守的,思乡的泪水或许会有,但只要他能够找到一个无毛两足的动物,他马上就会找到“交流”的伙伴。因为在这种国家里面人与人之间将不会再有任何本质性的差别,人们将不会再遇到真正陌生的东西。——地球的空间将被完全地均质化,跟某片土地相结合的历史、传统、文化和风俗等等,都可以被迅速切割,迅速被重新排列组合。
这个科幻传说也可以有另外的表述版本:让那个操刀的超人现在变成一个可以随意摇撼地球的超人。假设他一手抓住太平洋,一手抓住大西洋,把地球像筛糠那样用力摇晃;如果人还没有被第一宇宙速度甩出地球,那么这些可怜的小沙粒也会被甩开原来的位置,跟原先所有的环境,比如朋友,家人(还有家人么?),同学和朋友等等告别。等他从昏厥当中再次醒来的时候,他会发现周围都是陌生人,但
“最爱陌生人”,因为到时候我有十足的把握可以确信,我在这个陌生人的头脑里面不会发现任何我不熟悉的东西,发现我们彼此之间已经“缘定三生”,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握手言欢。
除了上述空间意义上的均质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均质化。科耶夫指出,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时候,人是一种在被将来所规划的现在当中生存的存在。也就是说,历史中的人还是有创造力的,他还会用将来的不确定性超越现在的给定性,从而也超越自身存在的给定性。但在历史终结之后的普遍均质国家,因为历史在本质上已经被完成,所以《旧约
·传道书》中所说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必将在去宗教化、最人性化的意义上成为现实,“将来”将不会对人们再有任何的吸引力。那时候的运动,便是日复一日地重复人类已经走过的“圆环”。——在1955年5月16日致施米特的信中,科耶夫说:
现在,我相信黑格尔完全正确,我也相信,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拿破仑之后,历史已经终结。因为,说到底,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
“新式的、放大的和改进版的”拿破仑而已[La République une et indivisible(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Ein Land, ein Volk,einFuhrer(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希特勒犯下了那些您在第166页(接近中间的部分)里面描述得非常之准确的错误:也就是说,如果拿破仑在他的那个时代可以做到希特勒这个程度的话,无疑是足够的。但不幸的是,希特勒做这些事情是远在150年之后!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带来任何从本质上来说是新颖的东西。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只是一段幕间休息。
战争以及战争的可能,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时候乃是让意义得以维持的根本手段。每一次有意义的战争,既是对现实的汰洗,也意味着人类的重生。但在拿破仑之后,所有的战争都将被虚无化,它的意义也将最终被淘空,人们没有能力证明一种价值比另外一种价值更高尚,也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为某种连自己都犹豫不决的理由而拿起枪杆。也就是说,均质化的时间状况让人们没有办法对未来寄予希望,也没有能力再为任何某种理由所许诺的将来而流血。所有许诺人类以新将来的战争,都将被证明为
“虚空的虚空”。——当人们发现战争本身是无意义的循环的时候,抛弃战争、普遍均质的时间观念也将成为必然。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普遍均质的哲学,如何跟
“新拉丁帝国”的梦想调和?——这篇建言书的主人公,在两年之前杀青的《法权现象学纲要》里面还在说他不但要依法治国,还要依照法律治理地球,要用由三个人参加的法律情境来取代两个人面对面时的政治决断。——但同样还是这一个人,在这封勾勒拉丁帝国蓝图的建言书里面,却偷梁换柱地把关键词由“法权”换成了“政治”。细绎这篇建言书,几乎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在两年前的《法权现象学纲要》里面念兹在兹地引为假想敌的、施米特式的“政治”语言。——跟所有把历史任由自然来融化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虚无主义牌的普遍均质国家理论不同,这篇建言书充斥了关于正确、历史、传统、拉丁帝国的昔日辉煌这类如果放在《法权现象学纲要》的语境里面将会被肢解得七零八落的字眼。一言以蔽之,在《法国国是纲要》里面,历史还没有终结,政治也还有价值,哪怕是残余的价值。
邀买君主信任,最简单也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把如果不听从自己见解可能会发生的后果说得骇人听闻。在这点上科耶夫也不例外,且看他在建言书中提出的、法国正面临的两个任务:
——一方面,在苏联人与英美人之间可能要爆发的战争到来之前,必须要尽最大努力确保实现中立;
——另一方面,在苏联之外的欧洲大陆,在和平期间,保证法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对于德国的领先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目的是关系到血腥的政治厮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中间手段即预想之中的拉丁帝国,自然也不能不政治:
在十九世纪仍然非常强大的民族国家,正如中世纪时候的封邑、城市和主教区不再是国家一样,也正渐渐地不再是政治性的实体,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作为当前政治实体的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所需要的基础比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所能呈现出来的更加广阔。为了能够在政治上生存下去,现代国家的基础必须是一种
“广阔的、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帝国性的’联 盟”。
如果有谁不幸提前两年看到了《法权现象学纲要》(有趣的是,这部科耶夫自己感到满意的著作,在他生前并没有出版),而如果有谁又不小心把《法权现象学纲要》当成了
“科子晚年定见”,那就真的是南辕北辙了。且看科耶夫对跟自己提出的最终方略极端近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评骘意见:
另一方面,
“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则确信自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即政治实体正在从民族国家移向人性本身。
···而国际主义的疏忽则在于,如果离开了人性,它没有办法看到任何一种在政治上能够存在下去的东西。它同样也没有办法揭示出帝国这样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实体,而这种实体作为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或者说国际性的集合体,恰恰就是人们在今天所看到的政治实体。如果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一种政治实体,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人性也仍然只是一种抽象。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国际主义在当前还是一个“乌托邦”。现阶段的国际主义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才认识到,如果不经历帝国的阶段,从民族国家是不可能跨越到人性的。正如同德国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与自己的意志相反,如果不经过封建的和民族国家的阶段,是不可能达到帝国阶段的。已经抛弃了民族国家的、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精神,在通过人性被体现出来之前,必须要栖息于帝国当中。
也就是说,国际共运史之所以没有达到整合人性的目的,要害在于它妄图不经历政治而直接达到
“人性”。既然镜鉴在前,法国之不能“非政治”、之必须讲政治,也就成为情理中事。像下面这样的耸听危言,科耶夫说了不止一遍:
因此,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法国放弃独立的政治存在,也就是说,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那么,她不仅会丢尽拉丁
—天主教文明的“脸面”,而且还会丢尽自己的脸面。
也就是说,在《法权现象学纲要》里面被顺理成章地作为基础、作为目标的
“人性”,在建言书里被无限期地搁置了。如下在建言书里面在在可见的痛心疾首的言论,跟施米特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开始的、对于虚无主义政治学和德国无决断的政治状况的批评比较起来,何其相似
:
但是,更加贻害无穷的是,非政治化(
depoliticization)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攫取了法兰西民族的心脏。因为毫无疑问,后者的衰落(这一点没有谁会提出异议,因此再加赘述也没有什么意义——并且也只能徒增烦恼)是与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萎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萎缩所呈现给世人或者说向世人所表述出来的面相,就是法国丧失了一种现实、明朗而有实际效力的政治意志。因为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加以否定甚至没有办法视而不见的事实是,去年,昨天——甚至还有今天——的法国,已经没有一种清晰而明确的政治理念,或者她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一种理念了。现代的法国人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自己的思想意识当中,都是在作为一个“资产者”在生活,而不是作为一个“公民”而生活。他在行动和思考的时候,都是一个“私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个别的”利益对他来说是最高的或者说是唯一的价值。他首先是“自由的”,或者说首先是“自由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因为他再也不想受制于国家“普遍”现实性的负累和要求,也不想受制于国家用来主张和保护自己的那些手段。
但回顾《法权现象学纲要》,科耶夫的矛头所向,便是要想办法融化他其实很早就读到的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当中的中心主张:政治便是划分敌我,便是坚定地说某些东西是永远的,是唯一正确的,并且为了这个永远和这个唯一的正确,要敢于血战到底。
——但彼处的科耶夫却说,一旦普遍均质国家成为现实,施米特的理论整体上就会成为真正的过去,就会失去价值。
因为在《法国国是纲要》里面全面接受了施米特的政治观念,所以,科耶夫对于施米特的赞同就不仅包括总体性的政治概念而已,还渗透到许多施米特曾经有所论列的细节。换句话说,科耶夫在真正开始跟施米特的交往之前,虽然未必读过施米特的所有论著,但是因为接受了施米特关于政治问题的根本立场,他也就必然接受施米特在很多直接问题上的遗产(或者说与这种遗产暗合)。
首先,《法国国是纲要》当中所看到的国际格局、所确定的三个帝国,说到底也就是施米特以各种方式谈论了几十年的
“大空间”观念。虽然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在细节上、在瓜分地球的“大空间”的地理构成上随着历史境况的不同前后而有变化,但有两条最基本的见解前后一贯:一是,法理性民族国家没有办法从规范法学的立场来认识,这种国家的“法理主权”,在当代世界技术和经济的总体景观之下,必然要依附于那些能够在“事实上”左右地区局势、参与世界瓜分的“大空间”的“事实主权”。或者简单点说:全世界能够拥有法理主权的国家可能有几百个,但拥有事实主权的国家则可能寥寥可数。主权既然说到底就是打破常规进入非常状态,那么,研究事实主权实际上也就是要研究在适当的条件下吞并某些民族国家,使之服从于拥有更大事实主权力量的大空间。二是,施米特极力反对空间被操刀的巨人或者摇撼地球的巨人虚无化,在他看来,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地理空间,都是不可析离出来而抽象地加以认识的匀质空间,而是那种跟某个人群、跟某种独特的历史、传统、律法等等一一对应的本质性空间。——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把这套理论如果用科耶夫的语言加以翻译,就是拉丁帝国的理念。
其次,科耶夫引以为拉丁帝国立国精神的天主教,跟施米特用来对抗自由民主现代性的罗马天主教精神也若合符节。
施米特早年曾经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册子《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译本收入刘小枫主编,刘宗坤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9月,页57—112),对于这个小册子的政治用心,论者曾经指出:
要解读这部看起来不难懂的小册子并不容易。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对自由民主现代性的形成及其问题作了经典研究,支配了
20世纪学术思想诸多重大的问题意识。施米特从新教伦理的对立面——天主教政治伦理来看待自由民主现代性的形成及其问题,在解释继承了罗马法传统的天主教政治形式时,明显与韦伯相对。研究施米特的这篇文本,对于现代性的形成及其问题的理解,将会出现一片截然不同的景观和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刘小枫:前揭书《编选说明》,页2)。
也就是说,施米特为罗马天主教招魂使之与现代新教伦理的比对,其实也就是利用罗马天主教的形式来对抗被韦伯所揭示出来的现代性政治伦理。并不是说韦伯本身的分析没有道理,而是说这个分析所显现出来的那个事实本身
——即现代性的政治伦理以及这个伦理所依附的形体即英美的政治取向——必须要从政治上加以反对。但其实施米特在宗教上所反对的不止是新教而已,如果考虑到他在1920年代开始逐渐显露出来的反苏俄的政治倾向也结合着对于东正教传统的严阵以待,则上述对罗马天主教的标举其实也就等于是为欧洲政治形式的精神支持寻找助力和标的。
科耶夫有没有读过施米特的这个小册子还有待于证实,但他在《法国国是纲要》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对于新教以及被新教所附体的政治实体即英美帝国的反对态度,却跟施米特的想法毫无二致。首先,科耶夫跟施米特同调,把韦伯憋在心里但没有明说的、新教与英美帝国的重合关系明白地揭发了出来:
一方面,人们很容易就会把德意志和英美诸国进入近代以来的巨大飞跃解释成是新教世界里面教会与国家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的结果;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从本质上讲起来是
“资本主义”的英美帝国或者说德意志—英美帝国,直到今天仍然受到新教教义的巨大鼓舞。(有些社会学家甚至在新教当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源泉。)
就跟科耶夫很明白地告诉戴高乐的一样:今天所谈的新教云云跟纯粹宗教的问题没有关联,这是十足的政治问题,因为科耶夫所看到的三大基督教支派的思想和精神层面的版图,跟帝国间的政治和地理意义上的版图其实是重合的:
在正教传统的斯拉夫
—苏维埃帝国和受到新教启示的英美帝国和可能存在的德意志—英美帝国之外,还必须要造就一个拉丁帝国(Latin Empire)。只有这样,一个帝国才能够与已经存在的那两个帝国处于同样的政治水平,因为在帝国独立性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她自己就能够支撑一场可能的战争。并且,只有通过将自身置于这样一个帝国之领导者的位置上,法国才能够保持其政治上的,从而还有文化上的特殊性。
而就事实来说,新教从一开始就是依附于英美世界的,而这个世界目前正在将德意志世界也纳入进来。正教教会虽然看起来已经脱离了俄罗斯帝国,但它实际上又找到了正处于创建过程之中的斯拉夫
—苏维埃帝国。至于天主教教会,可能过不了多久也就没有办法抵制拉丁帝国了。
如果不把天主教的精神跟拉丁帝国的肉体相结合,如果任由文化成为游魂而又不做一番认真的
“招魂”工作,则不但拉丁帝国的肢体将成为不折不扣的植物人,而从宗教文化这一面来说,脱离了政治依托,摆脱了政治保护的拉丁天主教文化,只会成为装点和谈资。因此,拉丁帝国不但要保种,也要保教:
在这个帝国的内部,法国非但不会发扬光大,反而还要受制于得到英美集团压倒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支撑的英美帝国文明
——这种文明从其现代形式上来说基本上是新教式的,也是“德意志式”的——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蛛丝马迹,已经可以从看着来自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的电影和小说长大的法国年轻人的身体和道德方面,隐约地辨别出来。因此,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法国放弃独立的政治存在,也就是说,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那么,她不仅会丢尽拉丁—天主教文明的“脸面”,而且还会丢尽自己的脸面。
——《法国国是纲要》跟《法权现象学纲要》之间所存在的上述矛盾该怎样解决?
二
在《黑格尔导读》和《法权现象学纲要》里面,科耶夫非常喜欢用这样一个说法:某个现象
“从现象上来说”如何如何,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或者“从现象学家的角度”(诸如此类)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换句话说,科耶夫毫不讳言,自己所看到的那种现象,并非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而自己所具有的那种眼光,也未必是所有人都能够具有。在历史终结之后,所有人都将变得同样聪明或者同样不聪明,但在历史结束之前的最后时刻,却有那么一个人比所有人都聪明。这个人的婴儿版是黑格尔,而他在20世纪的成人版,科耶夫尽管没有明说,但其实意思是清楚的:就是我科耶夫!
1955年5月2日,科耶夫在读到了施米特的讨论“攫取”(施米特对战争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称呼)绝不可能随着生产和分配方式的解决而被最终解决的论文《占有/分配/生产:一个从Nomos出发决定每种社会经济秩序诸基本问题的尝试》之后,曾经写信给施米特,有过如下的意见:
1)“从本质上来说”(当然是从拿破仑以来)不会再有任何的“攫取”存在(所有有关的企图都已经失败了);
2)“对于我们来说”(即对于“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来说),现在所有的只是“生产”!
3)但是——“对于意识自身来说”(比如对于美国/苏联来说),“区分”还是存在的。
关于这三条回答的详情,收入本书的美国学者霍斯的《欧洲与世界新秩序:科耶夫与施米特的
“大地法”遭遇的教益》有某种分析,关于《法国国是纲要》,霍斯也有某种意见,但这位《法权现象学纲要》的英译者没有谈到的问题是:《法国国是纲要》和《法权现象学纲要》之间的差别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法国国是纲要》在前而《法权现象学纲要》在后,那么,人们可以说,前者是作者的少壮之作,后者则是作者的老成之作;但是在为普遍均质国家开创镃基的《法权现象学纲要》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政治已经消亡之后,再来重提政治的问题,这之间的翻云覆雨,该如何解释呢?难道历史又要重新开始一遍?
如果考虑到我们在这里所说到的,科耶夫一直都自视甚高,将自己视为终结历史的
“智者”这点来说,如上的矛盾似乎便有了某种线索,也就是说,科耶夫认为自己作为“精神”、作为“绝对知识”,是高于作为意识而存在的具体国家的“政治”的,也就是说,科耶夫认为自己相对于政治、相对于某个具体国家的关系乃是上对下的关系,是智者对愚民的位置,是启蒙者对受教者的位置。因此,上述矛盾除了应该从概念的角度加以疏通之外,还必须要参照科耶夫两面三刀的用心和一龙一蛇的行迹来摸索。
科耶夫出生在
“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理论上应该是俄国人。但革命后的俄国大学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子弟而拒绝让他入学,他不得不亡命法国,此后的大部分生涯也在法国度过,并且也是为法国度过。但上文已经提到,即便到了法国之后,科耶夫其实也没有断绝跟俄国的联系,他甚至还给斯大林写过人民来信。——我对这封信的内容很感兴趣,可惜今天已无从考究其中的详情,可能被克格勃的官员冷笑着丢进了字纸篓里面也说不定。但据伯林说,这封信跟俄国国策的选择有关,我可不可以大胆假设,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俄国国是纲要”?在这个纲要里面,科耶夫提醒斯大林说:你要小心美国,小心欧洲,你要强化你的内政,也要注意跟东正教合作,以便建设一个可以跟美、欧鼎立的斯拉夫—苏维埃帝国。——这是我异想天开么?我倒觉得从《法国国是纲要》里面,是可以找到证据的,那就是,与平常可以看到的离开了母国便对负我的母国一切都穷极恶语中伤之能事的“人之常情”不同,科耶夫对斯大林从政治的角度给予高度的赞赏。并且,他并不认为这个斯拉夫—苏维埃帝国和拉丁帝国之间有着高下之别,因为它们都是帝国,都是人类走向绝对知识或者精神所预见的那个前途的准备。——再让我们问一个问题:科耶夫在流亡的时候选择法国,这是“必然的”么?也就是说,这是不是因为法国跟科耶夫之间有某种本质性的、需要用生命来证明的关系。我觉得未必,而如果机缘凑泊,科耶夫流亡的下一站是英国或者美国,他成为与拉丁帝国或者斯拉夫—苏维埃帝国相对立的英美帝国的智囊,应该也不是太过离谱的推测吧。科耶夫没有祖国,也不需要祖国。因为既然他的着眼点乃是全球性的普遍均质国家,他唯一需要考虑的,便是自己应该如何“道成肉身”,通过一个国家机器让自己的规划找到寄托。因此,在这个自比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看来,自己寄身于何处、选择何种语言,跟道德毫无关联,或者,即便有关联,也没有必要考虑。因为,既然绝对精神是人类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现实的对立、界限等等,就没有哪一条是不可跨越的。
既然绝对精神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那么从自身学说的角度来说,科耶夫显然也没有恪守
“学术道德”,1955年5月16日,科耶夫致信施米特告诉他说,所有目前表现为对立的界限都可以泯灭:
我非常高兴我们对所谓的现代
“国家”想法是相同的。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尽管如此您仍然还能够谈及一场即将到来的政治—军事“冲突”。对我来说,莫洛托夫的牛仔帽才是未来的象征。
在这封信里面,科耶夫从政治的最终消亡出发,赞赏了施米特许久以来切齿不已的苏俄。这还不算完,
1957年1月,科耶夫在施米特的关说之下,到杜塞尔多夫继续贩卖自己的历史终结哲学,这次科耶夫更是当着施米特的面,皮里阳秋地赞赏了美国:
我想说的只是,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从来都没有办法理解人们到底出于什么理由反感美国。因此,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总是会在这当中看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偏见的东西。但也有可能我是错的。
其实,科耶夫的如下说法,可以看成是他对施米特政治理论的定论:
除了关于时间的问题之外,我赞同您的所有观点(对于其中那些才华横溢的东西来说,我无话可说,您本人当然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您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过去是正确的,但现在却不再正确了。
话还是要说回来,当科耶夫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的身份乃是法国政府的公务员,他的事业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事业;也就是说,这个公务员正在从事的工作,还是《法国国是纲要》里面对戴高乐说过的那些。说得再白一些(用黑格尔式的哲学语言来说):以《法国国是纲要》为代表的科耶夫的一系列用世作品,是科耶夫穿上政客行头之后、化身历史情境中的
“自我意识”之后的语言;而《法权现象学纲要》则是科耶夫面对少数哲人的窃窃私语。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目标;而尤其重要的是,前者当中的那个我,对于自己正在做什么事情有非常清醒的自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