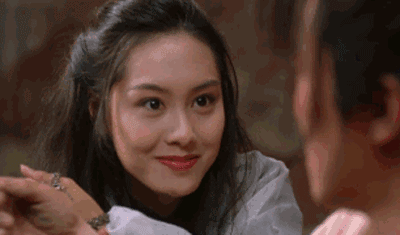「
你喜欢的是我的外表,还是我本人?
」
「万一我毁容了,你还爱我吗?」这是我们让小莉问过的两个问题。为了找到满意的回答,小明头疼不已。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有更多问题等着折磨小明呢。
◇◆◇
Part 1
等我们老了,你还会爱我吗?
如果小莉真心喜欢小明,那她大概问过「等我们老了,你还会爱我吗?」小明必定回答「当然啦!无论多老,我都是爱你的!」这个答案通常算是合格了。毕竟,未来不可知。问「还会不会」,无非是要对方此刻的态度。态度肯定也就足够了。但作为恋人,小莉有着异乎寻常的好奇。「用态度糊弄我是不够的!」于是她问:「你怎么知道的?你看见未来了吗?」对于未来,小明通常不会怀疑。「明天下雨」、「后天是星期三」这些只要翻翻日历、看看天气预报就知道了。可是,小莉的逼问却让他哑口无言。「呃,未来这种东西,好像真是看不到呢…」

小明的困惑,亚里士多德早已预见。「未来不存在」,亚里士多德讲到。因为未来的一切都未曾发生。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比小莉要更加苛刻:「过去也不存在。」因为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也就是说,小明既不能回答「等我老了,还会爱你」,他也不能在小莉生气时说「爱过」。就连「现在」,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放过。现在只是过去和未来的边界。所以,现在也不存在。
亚里士多德本人并不接受上述结论。但小明的困惑至少说明了「时间」现象的脆弱性。我们平时都知道什么是时间。我们知道「明天是 deadline」,「是时候吃饭了」,「刷手机不能太久」。但只要眯起眼睛、投出怀疑的眼光,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看不到「时间」本身。借用极端经验论的视角,可以说我们只能看到当下意识中所闪现的种种性质。
关于
时间的非实在性
,当代最著名的论证来自 McTaggart。我们先简要复述一下 McTaggart 的论证,再考察两个相应的时间理论。
McTaggart 首先指出了两种刻画时间的方式:A 序列和 B 序列。
A 序列,是我们十分熟悉的「流动」的时间序列。这里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序列中的事件随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
2019 年的春节已成过去,2020 年的春节还未到来,且将会到来。我们所熟悉的时态,以及「即将」等关于时间的副词,正是时间 A 序列的特征。
B 序列则以「先于」、「后于」来刻画时间中的事件。
不管 2020 年的春节还有多远,它永远「后于」2019 年的春节。在 B 序列中,所有的事件都有着固定的时间。2008 年的奥运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它永远发生在 2008 年。2020 年奥运会还未到来,但它也将永远发生在 2020 年。
基于 A、B 序列,McTaggart 做出如下论证:
-
P1.B 序列作为时间序列,依A序列而成立。
-
P2.A 序列矛盾,不存在。
-
所以,时间不存在。
对于前提 P1,McTaggart 指出「变化」是时间的一个本质特征。一个完整的时间理论必须说清时间中的事物如何发生变化。小明曾经只有 1.4 米,用三年时间疯长到了 1.8 米。这三年中,小明经历了「变化」。你从前不会英语,刻苦学习后终于能谈笑风生。在这期间,你也经历了「变化」。如果一个框架不能解释其中元素如何变化,它也就不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框架。
McTaggart 认为,B 序列中的元素就无法变化。典型的 B 序列元素,如「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不会变得更近,也不变得更远——因为它仅仅处在和其他时间的相对时间关系之中。2008 年北京奥运会,永远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永远比 2012 年伦敦奥运会提前四年。甚至,2008 年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被固定在 B 序列时间轴的点上。埃蒙斯最后一枪射偏了,他就永远的射偏,再也没法更改了。

你说,不对呀!埃蒙斯可以重新振作,磨练技艺和心里素质。等他获得更好的成绩时,失误的经历就逐渐被淡忘。没错,可你这时已经采用了 A 序列的时间视角:埃蒙斯只是「曾经」很悲催,「今后」却可以走出阴影。
我们暂且假设 McTaggart 是对的。我们确实需要A序列来理解时间中的变化。P1 为真。可这又怎样呢?我们每天都经历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几个时态之间相安无事,世界从没宕机。McTaggart 则认为,世界宕不宕机是一回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指是否真实则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
如果一个事件属于 A 序列,它就必须「共同」属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毕竟,A 序列事件的特征无非「从未来靠近,经现在,坠入过去」。但这个结果却是矛盾的。
任何一个事件,都不能共同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
对此,你可以反驳:一个事件明明「曾经」是未来,「正是」现在,「即将」是过去。难道不能让过去、现在和未来属于三个不同的时态,各自安好么?McTaggart 说:不行!因为你这是在用时态概念重复的解释时态本身。想要恰当的解释 A 序列,就不能使用时态概念。总之,A 序列矛盾。前提 P2 为真。因为 B 序列依赖 A 序列,A 序列又不存在,所以,时间不存在。
我们至此可以帮小明想出一个回答:小莉你看,我说不清老了以后会怎样,但这不是因为我意志不坚,而是因为时间本身就不存在,所以你不能强求我……
假设小莉耐心的听完了小明的辩解,对 McTaggart 感到非常不爽。她于是反问:你不知道老了以后会怎样,因为时间不存在,那你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喜欢我喽?几周前我问过你这个问题,当时你还信誓旦旦搬出笛卡尔「我思」的确定性,拍着胸脯说你就是知道。现在怎么啦?
我们先不去想此时小明的脸色。事实上,除小莉外,很多哲学家也对 McTaggart 不爽。他们觉得 P1 和 P2 两个前提都很可疑。
McTaggart 的第一个前提 P1 认为
B 序列本身不是时间序列。这大概会让你的物理老师跳脚。每次物理老师讲解时间的时候,可都是画出一条名为「T」的时间轴啊。在这个轴上,每个点发生的事情都是固定的。「小莉在时刻 t
0
生气,朝方向 D 跑去,和小明初始距离为 N,速度为 V
A
。小明在时刻t
1
反应过来,朝 D 追去,速度为 V
B
。问:在时刻 t
m
,小明和小莉的距离多少?」你能算出来,是因为在给定条件下,两人每一个时刻的速度、位置都能确定。总不能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这个轴上处于哪个的位置,之不出「过去」和「现在」,就跟物理老师说「T 不是时间轴」吧?
很多人反对 P1 的原因,正是因为 B 序列恰好符合近当代物理科学对时间的理解。物理学不关心你对时间的感知,不关心你是不是「昨天」衣服穿不上「今天」减肥「明天」就瘦了。物理学只关心给定某物理状态后,能否算出「下一刻」的状态。我们不能因为时间轴上不显示「过去」、「现在」和「未来」,就认为它和时间完全无关。
认为 B 序列足以描述时间,甚至时间的本质无非 B 序列这一想法,称为时间的 B 理论。
我们刚刚其实指出,
时间 B 理论的核心优势,是它与当代科学之间的契合。
尤其,
相对论把时间看作空间之外的「第四维」。时间和空间并无本质区别。至于我们在时间中的位置,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并不带来任何特殊性。
你想,在三维空间中,我们是不是也常说「这里」、「那里」?而且,这些指示方位的副词,是不是也是针对你的位置而产生的?当你正处在 2019 年 3 月 14 号的时候,你的「现在」就是 3 月 14 号。类似,当你站在世贸天阶,看着一对对情侣趁白色情人节相互表白,你的「这里」就是世贸天阶。世贸天阶有什么特殊吗?嗯,也许它适合表白。但是它作为空间中的点,和其他点是完全一样、完全同质的。那么,你所处的 3 月 14 号,又凭什么非要和其他时间有本质不同呢?
至于「容不下变化」这个指责,B 理论者可以说:的确,时间轴中的事件(events)不变,但事物(things)可变。事实上,我们很少谈论事件的变化。埃蒙斯射偏了,就是射偏了。不管用什么时间序列描述,这个事件本身都不变。当然,你可以说它在 A 序列中「变远」了。但这不是变化的典型场景啊。所谓变化,是指你昨天胖了今天瘦了。是指一场战争开始了结束了。
经历变化的,不应是事件,而应是事物。
显然,B 理论很容易说明事物如何发生变化。设小明在 t
1
时跑的飞快,在 t
m
时跑不动了。这两个事件共同说明了小明的某种变化。类似的,埃蒙斯最后一枪射偏了,但紧接着和爱人撒了一波狗粮。这是埃蒙斯经历的变化。
这时,小明或许可以改口了。「等我们老了,我还会爱你的;虽然我对此缺少绝对确定的认知辩护,但它是可预见的、有意义的一句话:在我们老了的那个时间段内,小明还是爱着小莉的」。
小莉对此可能十分感动。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蹊跷。某个时间段内会发生什么,这不过是与我现在无关的事实。我期盼什么呢?又高兴什么呢?你不要觉得小莉太过刁钻。哲学家 Arthur Prior 也对 B 理论表示过相同的担忧。假设,病人经历了长期的折磨之后,终于痊愈。他高呼「总算熬过来了」。Prior 认为,根据 B 理论,痊愈不过是指一个四维空间中的延展者——疾病——其时间边界处于某一点。这相当于说一个篮球的边界如此如此。对这类事实,我们有什么可开心的呢?的确我们可以说一个篮球的边界光滑,入网清脆。但这种开心显然没法用「终于……了」来表达。
既然 B 理论有这么多缺点,我们就来看一看时间的 A 理论。
B 理论认为时间的本质是 B 序列,A 理论则认为时间的本质是 A 序列。
从 A 序列出发,我们很容易解决小莉最后的疑惑。「老了以后依然相爱」值得期盼,因为那是「将来」会发生的事。
McTaggart 认为
A 序列充满矛盾,A 序列中的事件「共同」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
之所以不能用「曾经属于过去」、「正属于现在」等表述来化解,是因为我们不该用时态概念重复解释时态概念。然而,A 理论的支持者可以说:如果时间本质上就是时态的,那它根本「无需」通过非时态的概念去解释。以非时态的概念解释时态概念,也将成为不合理的要求。
不过,仅仅不矛盾,还不能满足 A 理论的要求。McTaggart 之所以会想到「同属于」的困境,部分源于时间「从未来靠近,经现在,坠入过去」的模型。完整的 A 理论因而需要对时间的流动给出比较恰当的描述。
C.D.Broad 就提出了比较具体的
时间流动模型
。经本土化之后,其内容是这样的:想象在阅兵仪式上,队列很长很长,领袖乘敞篷车经过,一一招手。领袖经过的地方,「首长好」的口号响彻不绝。Broad 会说,喊过「首长好」的部队,是过去。正在喊的是现在。还未喊的是将来。这个模型的细节未必准确——比如,「首长好」似乎喊在领袖快来的时候最好,而不是领袖正在经过的时候。无论精度如何,「首长好」毕竟是全新的时间模型:不是从未来到过去,而是「现在」从过去到未来。

这个模型本身并未提出多少本体论主张。回想亚里士多德的那个问题:未来存在吗?过去存在吗?对此,「首长好」没有现成的答案。Broad 本人的理论称为
the growing block theory of time
。即,
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不存在。
未来事件的发生,是彻彻底底的「无中生有」。翻译成刚才的模型就是:喊过「首长好」的队伍存在,正喊「首长好」的队伍存在,没喊的不存在,根本不存在。(别问:这怎么可能?队伍都是撒豆成兵自己蹦出来的?撒豆成兵还有豆子呢!毕竟是模型嘛,肯定不严格。况且根据「彻底无中生有」的说法,这也不是不可能。)
目前最流行的 A 理论,不是 growing block theory,而是
当下主义(
presentism)
。当下主义认为,只有当下存在,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当下主义最好的尊重了经验主义的理论直觉。
反思一下,问问自己,这世上到底有什么?你的意识中有「过去」吗?没有,只有回忆。有「未来」吗?没有,只有预想。而所有的经验,都是「当下」的。所以,只有当下存在。
你或许嫌这个理论太严酷。不光当下主义,连 growing block 都很严酷。未来怎么会彻底的不存在呢?最理想的说法,难道不是让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存在,只不过现在是更特殊的存在?这样当然好。可问题是,我们怎么解释「特殊的存在」呢?存在真能分特殊和一般吗?存在不是选拔赛,不是在众多选手中找出最优的。存在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所以,我们也只得接受当下主义或 growing block theory,承认某一个维度——比如未来——不存在。
未来不存在的后果是什么?对小明来说,他终于找到了理由。「刚才你把我问懵了,但那不是因为我犹豫,而是因为未来根本不存在啊」。并且,小莉这时没法用「那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喜欢我」来追问。因为根据当下主义或 growing block theory,不存在的仅仅是未来。现在依然存在,小明也就能说「我现在喜欢你是真的哦,现在存在嘛!」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小明松了口气,就觉得 A 理论万事大吉。未来不存在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未来不存在,关于未来的命题就没有真值。天气预报将完全是在骗你。当你的导师或老板说下周有 deadline 时,你当耳旁风就好,不必在意……总之,
彻底的 A 理论者,是很难在世上存活的。
◇◆◇
Part 2
你说,我们是不是注定在一起?
除了未来,小莉也非常关心过去。如果跟小明是「八分钟相亲」认识的就太不浪漫了。两人注定在一起,因命运而相识,那才感天动地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注定在一起?」这个问题,小明回答过很多次了。每次都说「是」。可是他心里并不确定。他其实并不清楚「注定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苹果会落地」是什么意思,只要看着苹果落地,就知道这句话正确。可「注定在一起」又是什么?它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满足呢?
实际上,小明对「注定」多少有一些理解。「苹果会落地」是物理老师教的。而物理老师不光会画时间轴,也会告诉我们物理能算很多很多事情。正是因为物理的强大,
物理决定论(determinism)
才有那么多支持者——他们认为,
给定任意物理状态,后续的全部物理状态均可通过物理规律完美计算。
苹果会落地即是如此。手握苹果,松开的瞬间苹果一定下落。也许这就是注定的意思?所有的一切都注定发生?
小明准备把这个想法告诉小莉。但他知道小莉一贯刁钻,于是自己先开始反思。他忽然想到:根据物理决定论,一切都是必然的,我和小莉的相遇也是必然的。可当一切都注定后,注定也没什么了不起,小莉肯定是不开心的。至少,当她问「是否注定」的时候,她想的一定不是这么平凡的物理决定论。
实际上,物理决定论和小莉的期待明显不同。
根据物理决定论,一个事件 A 被「决定」,是因为此前发生了另一些事件 E,以及物理规律 N 对 E 的作用。也就是说,「一旦」E 因某种原因未曾发生,历史的进程将会彻底改变。此时,不再有任何因素能保证 A 依然发生。
你也许会说,决定论的世界里,这种「一旦」不会出现。但就算如此,只要决定论是一个恰当的理论,它就必须能允许我们「谈论」假设的情形——毕竟,谈论假设情形是日常生活及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一旦能谈论假设,我们就可以说:即使 A 是被事件 E 及规律 N 决定的,即使两者都不可改变,但「如果」E 未曾发生,A 也就极可能不会发生。
小莉显然不满意这样的结果。注定在一起,是要「无论之前发生了什么」都在一起的。就算错过了一个相遇的契机,也有第二个第三个契机等着他们,直到相遇为止。
比起决定论,
命定论(fatalism)
更符合小莉的内心所想。决定论的主要动机是为科学提供足够的施展空间。
命定论则以宗教为文化基础。想想阿波罗神谕的那些传说:一旦神谕被传达,结果就无法改变。所有反抗都会促成预言的实现。
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上帝全知全能。若上帝预知了某事,或决定介入某事,人类都无法更改其后果。
命定论究竟该如何表述呢?我们曾用物理状态及物理规律表达物理决定论。而对于什么是物理状态、什么是物理规律,我们有着基本的共识。相比之下,命定论需要哪些元素则并不清楚。至少,我们显然不能认为如果某命题 P 必然为真——「无论之前怎样」——则 P 是注定的。毕竟「2+2=4」也是必然为真的。无论怎么更改之前的历史,这个等式都不会变。但我们并不会说「2+2=4」是「注定」为真的。
神的介入似乎是命定论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了神谕,俄狄浦斯的故事将变得平淡无奇,弑父娶母的悲剧也只是源于巧合。通过神谕,俄狄浦斯的努力才显得徒劳。不过,神谕仅仅传递了神的信息,它本身不像引力一样作用于世间万物。俄狄浦斯「为什么」会弑父娶母,神谕本身并未说明。我们可以假设:要么,神从未介入,仅因「全知」而预见了未来;要么,神亲自介入,因「全能」而保证结果发生。无论根据哪种解释,典型的命定论都诉诸了相应宗教文化中的至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