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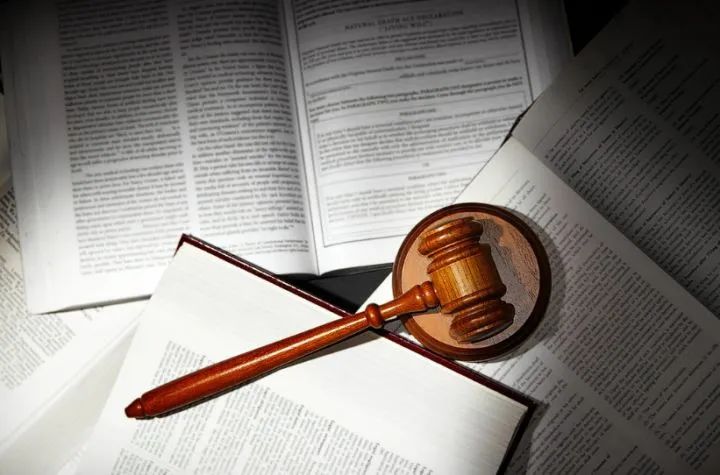
黄晖 万慧达知识产权
首发于《中国知识产权报》2025年1月17日刊
我国商标法立法之初基本是围绕商标注册展开的,1982年商标法中只有与质量管控有关为数不多的几个条款提到商标的使用,三年不使用的问题也只是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被提及。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商标法也不断细化和完善,商标使用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不仅已经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可以获得更多保护,而且不具有商标识别作用的标志经过使用可以取得显著性,当然,反过来不当使用也可以使商标丧失显著性。此外,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申请也不允许注册。商标使用的定义也从实施细则对撤销不使用商标的语境中逐渐普遍化,尤其是加入了“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要求,成为适用于整个商标法的核心概念,极大地丰富了商标法的内涵。
目前,第五次商标法的修改工作正在推进,围绕商标的使用,我们可以重点从确权和侵权两个维度来探讨适法以及修法的方向。
现行商标法在商标三年不使用可以撤销(“撤三”)的基础上已经增加了退化为通用名称的撤销理由(“撤通”),2023年公布的修改稿中又提出要增加“注册商标的使用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产地或者其他特点产生误认”的规定(“撤误”),形成“撤三、撤通和撤误”三者并行的撤销理由,这与大多数国家的商标法规定也保持了一致。而在考量这三个撤销理由时,确保注册商标能够“识别商品来源”,往往能在复杂的案件事实梳理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首先,就“撤通”而言,由于商标注册人自身行为或第三方的不当使用,商标偏离识别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原本是注册商标退化为通用名称的的情况不乏其例。商标注册人如果不能采取行动及时制止,商标就有丧失识别作用的风险,例如禁止将“老干妈”用作牛肉棒商品的口味名称,将“钛马赫”用作装修工艺名称,将“小香槟”作为起泡汽水名称,都属于这种及时维权的情况。欧盟各国甚至直接在商标法中赋予商标权利人有权要求词典出版社纠正错误释义,明确标注其为注册商标。这其实都是确保商标识别功能的当然之义。
其次,就“撤三”而言,通常情况下,商标取得注册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该商标具有显著性或识别性,识别商品来源因此也可以说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对于许可使用这种二元生产方式,即使在早期商标法之下并不被允许,但现代商标法已成功地将被许可人的使用视为注册人的使用,消费者已经不会苛求许可模式之下的商品一定实际来源于商标注册人。当然,在我国因为需要标注实际生产商,消费者对于实际的产源也可得而知。
但是,如果实际使用时,商标被作为叙述性词汇不当呈现,仍有可能被撤销。例如,欧盟法院在“百瑞木”案中就认为,商标在使用时被理解为是对成分的表述,而不是商标意义的使用。
同时,如果实际的使用没有遵循注册商标的人(主体)、物(商品)、志(商标)三者关系的正确绑定,仍然会产生错位的使用关系。例如,已有法院在相关案件中认为,由于甲公司并非将有关标志附加于商品上的主体,即便诉争商标标志与A公司通过甲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转售至中国的产品上所使用的商标标志相同,也不能认定该部分证据所涉及商标的使用为诉争商标的使用。
又如,有法院在另一案中认为,A品牌商品包装的背贴上虽同时注明了甲公司的企业名称,但甲仅以商品代理商的身份对外表征,在甲标识客观上一直被用作A商品的中文名称的情况下,消费者自然会将其与A品牌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通过甲标识,进一步联想到A品牌商品的良好品质、特色等附载在标识背后的商品品质、声誉等因素,不会据此认为甲品牌是甲公司作为代理商所使用或拥有的商业标识,而只会将甲公司视为是A商品或A/甲品牌的进口代理商。
换言之,即使注册商标的形式出现在商品上,还是有可能会被认为实际指示了另外的商品来源,从而被认为没有对商标进行过使用。而且,北京高院授权确权指南也认为“在标注他人商标的商品上同时贴附诉争商标,若相关公众不易识别该商品来源于诉争商标注册人的,可以认定不构成商标使用。”
再次,就“撤误”而言,虽然目前还是修法的一个尝试,但对于我们解开目前商标法执行过程中一些疑惑或许会有帮助。例如,目前对于关联公司申请近似商标产生冲突的仍然难以借助签订共存协议获得通过。更严重的是,一些最多属于叙述性即缺乏显著性的词汇现在却更多的被以具有欺骗性为由被驳回。基本的理由则均是万一关联公司投资关系有变或者所谓的叙述性成分并不存在,则将误导相关公众。但对于这些注册之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一旦有了“撤误”条款,实际都可以通过事后撤销来规制,而不必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撤误”程序正是通过对正确识别商品来源功能的保证,来避免提前过度反应。
商标侵权问题的核心在于制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所产生的误导混淆的后果。本来一般的审判思路应该是先判断是否构成侵权,再来判断是否存在抗辩事由,而不会先审抗辩事由,再审是否侵权。即使在被告明显构成商标法第59条第一、二款项下正当使用的情况下,虽不排除直接认定不侵权的可能性,但通常不会引发被告是否实施商标法第48条所谓的商标使用的讨论。
可现实情况中,仍会有不少法院会将第48条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现行讨论,直接架空了正当使用的分析。那背后的原因何在呢?问题可能出在商标法第57条的措辞上,因为该条第一、二项都将被告使用的对象定性为“商标”,而不是像TRIPS协定第16条第一款以及欧盟乃至香港地区商标法那样只要求被告使用的对象是一个“标志”。既然要求被告使用“商标”才构成侵权,那么法院将商标性使用作为侵权构成的要件甚至前提,似乎也无可厚非。
在某种意义上,商标法第48条对商标使用的要求实际虽然可以转化为判断一个标志是否发挥商标的识别作用的拷问,与商标法第59条相比,既可以说是从言异路,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抽象地讨论识别作用,仍不如具体地讨论一个标志是否在叙述商品的特征或实现商品的实用性功能。根本的出路应该还是只先审查被告使用的“标志”是否与原告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商品是否相同或类似,是否可能产生混淆,然后再讨论被告对该标志的使用是否有可能被解读为叙述性使用或功能性使用,而不必单独或首先讨论被告是否构成第48条的商标使用。
当然,鉴于商标赔偿救济乃至侵权判断中会涉及原告自身是否使用注册商标的问题,以上“撤三”程序中是否正确绑定人、物、志三者关系的审查仍然适用。换言之,如果原告或被告并没有让注册商标指示注册证上的商标注册人,原告形式上的注册商标实际不能被认为进行了使用,其诉讼请求也不应该得到支持。
总之,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是真正理解商标的保护对象的一把钥匙或试金石,对于我们正确适用商标法以及完成商标法第五次修改任务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