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伯格通过法国Teletel1的演变过程说明了技术的设计最终的形成,并不取决于普通的效率标准,而是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冲突和竞争过程。这一案例及结果给了芬伯格很大的启发,包括他后来“技术民主化”的观点及提出让公众参与技术的设计的主张等,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法国政府提出推行Teletel计划,原本是法国融入现代化的一环,法国政府通过该项目,意在:一是让法国公众感受到计算机时代的奇迹;二是打开国际相关市场。但在推进过程中,当时负责Teletel计划的法国电话公司于1981年首先4000台称为“小型电传”(Minitels)免费终端,之后10年,发放数量超过50万台。而公众收到免费终端之后,尽管他们拥有了可以从Teletel上获取大量数据资源的设备,但却很少利用,且对政府的这一计划表示普遍怀疑。直到1982年,有黑客通过系统修改把它改造为一种通讯系统,反倒即刻引起了公众的响应。之后,整个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发生了转向:人际通讯开始扮演重要位置。在此过程中,公众自身的“抗争”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非但没有按照政府所设想的计划去接受远程通讯业务的洗礼,而是人们自己发明和实现了新的技术使用功能,这是运行Teletel计划之初法国政府所没有想到的。
“在每一种情况下,技术系统都由科学-技术精英来构思和实施以回应它所喜欢的那套功能要求,但这种基于初始功能层次出发点或早或晚都会在思想上遇到来自拥有其他观念的公众的抵抗,抵抗采取的形式即是通过在它的边界上使之创新具体化,从而把技术系统合并到另一套功能要求中去……在现代社会技术基础的民主的重建中,这种具体化策略的扩展原则上是没有限度的。”(芬伯格, 2003: 280)按照芬伯格的解释,公众参与技术的设计,并不是技术性参与,而是价值、意义的参与。他认为,不只是技术精英及统治阶级,更重要的是“个体”,即普通公众也应该作为行为者之一,参与到技术的设计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了设计代表了多方面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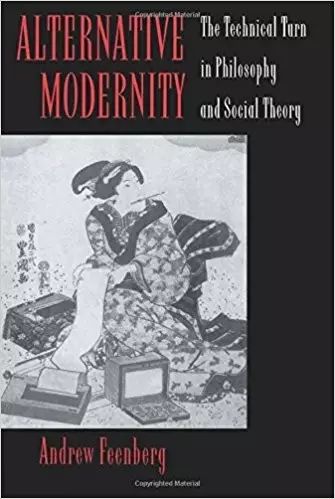
Alternative Modernity: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Andrew. Feenber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vised ed. edition (November 7, 1995)
而计算机技术的意义在于:一是它把个体整合进网络资源之中;二是提供给每个用户参与、互动的机会,融合参与者体验的空间和平台。任何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按照芬伯格的“工具化”理论,都应当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本质。第一层次被称作“初级工具化”,也即“去背景化”的过程,自然物先从原初背景脱离出来,作为技术客体被整合进技术系统,期间的互动、讨论或对抗多发生在与设计人造物功能的专家学者之间;第二个层次是“次级工具化”,如果说物体的重量、大小、形状等技术特性是其“第一性质”的话,那么物体的“第二性质”,如美学、伦理及文化价值等方面这时就嵌入进来,这期间争论范围拓展,将那些认为自身受到技术及其应用、后果和意义牵连与影响的团体也囊括进来。他们极力去形塑技术,促使由其技术本身造成的问题解决,这些团体所倡导的价值和解释性规范也就可以得到支持。
以上这两个层面的结合,便决定了截然不同于前代学者所着力批判的技术理性。芬伯格认为,技术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并非只有一条单向路线,它会受到有意识的社会控制,但只有更多的公众、社会群体参与其中,民主化的技术才有可能。而在此过程中,计算机技术及还在发展之中的计算化,承担了一个融合、沟通参加者体验的角色,生活世界的意义、价值借由行为者与计算机的啮合联动将反映在技术规则和标准之中。
而之所以提出以上观点,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今社会条件变化,技术科学并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所假定的独立的社会基础,而是一种附属的变量和其他的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在芬伯格看来,尽管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成功地复活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等级制的合理系统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但是他们却没有相应地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相反地,马尔库塞主张在技术发达的社会被如此成功地整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反抗唯有来自于社会的边缘,如少数民族、学生或第三世界等,而同时,这种边缘性反抗要依靠人们的反抗精神。
在芬伯格看来,尽管马尔库塞也提出让技术目的在机器设计和建造中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在它的使用中发挥作用,等等。但是,这些主张都太抽象和粗略,在如今技术的扩散日益加深、以至于个人和系统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的历史时期,这些思想很难与任何具体的实践相联系。在这种情形中,反抗必须是“内在的”,需要的是在系统的矛盾中做些什么,“目的并不是要摧毁我们被其框住了的系统,而是通过一种新的技术政治学改变它的发展方向”(芬伯格, 2003:40)。
与此同时,芬伯格注意到,尽管在当时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在种族、性别和环境等问题上都受到了左派的影响,但是能够出现的总动员却寥寥无几。相反地,微政治学实践,却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正是基于以上的种种认识,芬伯格提出了不同于马尔库塞等人观点的主张。在技术社会,尽管边缘性潜在的是每一个人生存条件的一种状况,然而,芬伯格认为,“这些网络自身又经历着由它们招的人类团体所引发的变革。在技术领域中出现的内在的反抗是新价值的重要承担者,正把一种新的形式加在技术体制身上。这些变革也许能够互相补充和互相依赖,改变发展的方向并消除恶托邦式的危机。”(芬伯格, 2003: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