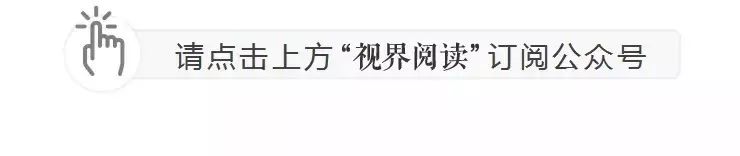
在荣格和弗洛伊德从美国回来的那个时期,他把弗洛伊德描述为“他生命中第一个真正重要的男人”。那是1909年,是萨尔茨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的次年。两个人都被邀请到马萨诸塞州讲学,而且同时被克拉克大学授予了法学荣誉博士的头衔。他在给妻子的信里写道:
现在,我可以在名字后面冠以L.L.D的头衔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激动?……弗洛伊德非常高兴,我也衷心地希望看到他这样。
在瑞士,荣格是一位成功的高级医师、作家以及讲师,而他却公开地支持激进的弗洛伊德。在那个时期,这种做法对于学术有着毁灭性的打击。
弗洛伊德,“在光荣的孤立下”,于世纪之交在维也纳创立了精神分析运动。而他在1905年发现的“童年期的性本能”使人们对他的名字产生了“极度的憎恶”。
早在20世纪初,荣格就读过弗洛伊德的创新之作《梦的解析》,进而“发现它是如何与我的想法联系在一起的”。他开始在他的著作里引用弗洛伊德的著述。1906年,在荣格将一本自己的著作送给弗洛伊德之后,二人的通信开始了。但是,在荣格写给弗洛伊德的第一封信里,也隐藏着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异。
对我而言,尽管歇斯底里症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性欲方面的,但也并不是唯一的。我对您的性欲理论也持有相同观点。
你的来信让我怀疑,你对我的心理学的尊重并没有延伸到我关于歇斯底里症和性欲问题的所有观点上。但我期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能够离我更近一些,比你现在所能想象到的更近一些……
次年,荣格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著作出版了。在序言的致谢词中,他承认“弗洛伊德杰出的发现使我受益良多”。尽管如此,他仍然强调“自己仍然能够维持非常独立的判断。”这件事情引发了两个人的第一次会面。会面的地点是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的家中。

我们在下午1点碰面,之后就是持续13个小时不间断的谈话。弗洛伊德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对我真正重要的人;在我到那时为止的经验中,没有其他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在他的看法中,没有任何一点是微不足道的。我发现他极其聪明、敏锐,总之他是卓越的。然而,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中仍然有一些混乱的地方,我还无法完全地理解他。
他关于性欲理论的论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他的话语并不能消除我的犹豫和怀疑。曾经有几次,我尝试进一步阐述我的保留意见。但每一次,他都将之归于我经验的缺乏。弗洛伊德是对的,在那个时候,我还缺乏足够的经验来支持我的反对意见……
总之,弗洛伊德对待精神的态度在我看来是高度可疑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一个人的身上或者在一件艺术品中,精神的表达都是为众人所熟悉的。但是,他却怀疑这些,并且暗示这些都是受压抑的性欲的表现。他把任何不能直接解释为性欲的东西都称之为“精神性欲”。我对此提出异议……以此推论,文化就只是一种闹剧,是受到压抑的性欲的病态结果。“是的”,他赞同地说,“就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对于无力抗争的命运的诅咒。”我绝不打算同意这种观点,又或者让它不了了之,但我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说服他放弃这个观点。
弗洛伊德开始把荣格视作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荣格也把弗洛伊德当成父亲一样的人物,尽管这种关系只存在了一段时间。19岁的年龄差距分隔了两人,并且他们渐渐地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冲突。
大多数时候,他们都通过信件进行交流。历时7年的通信中,大部分是在亲密地讨论科学理念、病人、同行、精神分析运动、他们的个人生活以及他们的个人关系。这是一封荣格希望在自己死后30年内不要公开的信件。在83岁时,他把它称为“对于我愚蠢的青年时代的一次不幸的、难以磨灭的提示。”信件揭示了他的人格和成长的许多方面,而在那个时期,很少有其他的信件被保留下来。
在他们交往的早期,荣格曾向弗洛伊德吐露了童年时期与家族中一位亲密的中年男性朋友有关的一段创伤经历。他也向弗洛伊德坦诚,这段创伤影响了他们之间的情感基调。
您的前两封信提到我在写作方面的倦怠……事实上,我以一种矛盾纠结的心态向您承认……我对您的憧憬中有一些宗教迷恋的成分。尽管它并没有真的干扰到我,我仍然感到它是令人厌恶的、荒谬的、可笑的,因为它暗示了不可否认的情欲成分。这种令人讨厌的情绪源自于一个事实:我在童年时,曾经被一个我所崇拜的男人性侵犯……
衷心地感谢您的来信,它对我产生了神奇的效果。您的称赞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那些我们无法回避的事情,幽默是唯一得体的应对方式。除非那些受抑制的东西战胜了我,否则,这也是我的信条——幸运的是,那种情况只会偶尔发生。
智力的激荡,发现的兴奋,共同的享受,没有任何事情会被隐瞒。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支持反映了他高傲的性情,他曾为弗洛伊德狠狠地训斥过一个刻薄的心理分析批评家。
“修特兰达”的冒险是奇妙的;当然,那个卑劣的混蛋是在说谎。我希望您能够通过您友善的态度来狠狠地嘲笑和驳斥那个家伙,使他陷入绝望之中,从而让他对于心理分析的有效性有一个持久的体验。我衷心地赞同您最终的判断。这就是那些畜生的本性。当我从他脸上读到猥亵的表情时,我真想一拳打在他的喉咙上。我真希望您能够向上帝一样告诉他,事实是如此的简单,就连他那母鸡一样的大脑都应该能够理解……如果我在您的位置上,我会用一种带有瑞士风格的打击方式软化他的流浪儿情结。
在1908年年末,以弗洛伊德关切的询问作为开始,荣格的孩子弗朗茨的诞生为他的家庭带来了一系列迷人的片段。

不,黎明还没有到来。我们必须小心地守护着我们的小油灯,因为夜还很漫长……与此同时,我期望命运能够再一次让你成为父亲……写信给我;这样我才能确信英雄的母亲一切平安;对于她的丈夫,她一定是比她所有的孩子都宝贵的,就好比方法一定比由它得到的结果有着更高的价值。
衷心地感谢您发来的祝贺电报!您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喜悦。生产过程很顺利,母子平安。
要感谢我4岁的女儿阿加特。在弗朗茨出生的前一晚,我问她,如果鹳鸟给她带来一个小弟弟的话,她会说些什么呢?“那样的话,我会杀了他。”她以闪电般的速度说出来,脸上还带着局促、狡猾的表情,似乎不希望自己被压制在这个情景中。孩子在夜里出生了。第二天清晨,我把她带到了妻子的床前。她很紧张,警惕地盯着脸色苍白的母亲,脸上没有一点高兴的表情,也不知道在那种情形下该说些什么。还是那个早晨,当妻子一个人发呆的时候,小家伙突然跑向她,把胳膊绕在她的脖子上,急切地问:“啊,妈妈,你不会死,对不对?……”
最后,在我的建议下,我的妻子向阿加特解释:小孩子在母亲肚子里的成长就像是花开在植物上一样……第二天,我得了流行性感冒躺在床上。阿加特带着一脸害羞,甚至有点吃惊的表情跑过来,“你的肚子里也种了一棵植物吗?”当这种可能性被排除后,她开心而且无忧无虑地跑开了。
这样的孩子是多么令人着迷啊!就在最近,阿加特当着她母亲的面,称赞她弟弟漂亮:“看啊,他有着多么可爱的小屁股。”
我的阿加特快乐地继续着她的发现。新颖而令人喜悦的解释已经产生了效果……她把一个洋娃娃塞在裙子下的两腿之间,只让洋娃娃的头露出来,然后大声地说:“看,孩子出来了!”然后,她把它慢慢地拉出来:“现在,它完全出来了。”只是父亲的角色还很模糊,只是梦中的一个主题。
我们仅仅是在听,尽可能地不做任何干涉。一个巨大的抗议声在今天早上出现了,“妈妈赶紧出来”“我要进你的房间”“爸爸在做什么?”但是妈妈并没有让她进入房间……过了一会儿,在我们起床后,阿加特蹦蹦跳跳地进了屋子,跳上了我的床,平趴下,像马一样挥舞和踢腾着腿并喊到:“爸爸是这样做的吗?这就是爸爸做的事情,是不是啊?”……我的同事鼓励我把这件事记录在年鉴之中。
在两个人中,弗洛伊德是那个更有通信需求的人。当一封期望中的信件没有出现时,他就会发一封急切的电报。1909年的荣格“处于一种极度的疲惫之中”,为了对一次迟发的回复进行辩解,吐露了几个问题,而其中一个更是牵涉了一位之前的病人——斯宾娜·史毕莱。
压垮我的是一个对我伤害巨大的心结:几年前,我花费了极大的心血把一个女病人从令人困扰的神经官能症中拉了出来;然而,她却用人类可以想到的最令人蒙羞的方式亵渎了我的自信和我的友谊。她独自挑起了一起卑鄙的谣言,而仅仅是因为我拒绝满足她生育孩子的乐趣。在她面前,我常常表现得非常绅士,尽管如此,在我相当敏感的良心面前,我并不觉得是纯洁的。正是这一点伤害我最深,因为我的意图一向是可敬的。与此同时,我也了解了大量关于婚姻的智慧,因为直到那时,尽管已经做了全部的自我分析,我对于自己身上一夫多妻制的成分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现在,我已经知道那个恶魔藏在哪里,以及如何去抓住他。这些痛苦的但是有益的内省对我的内在进行了残酷的自查,但是,也正是因为那个原因,我希望它能够保护我的道德品质,这将是我后半生最大的优势。我和妻子的关系也会因此获得巨大的保障和更深的进展。
在早期,他们讨论那个女人的时候都是以隐匿姓名的方式进行的,仅仅是把她当成一个“癔症病人”,一个“已经承认她最大的愿望是和我——一个能够实现她未被满足的愿望的人,生育一个孩子”的病人。
这是典型的移情现象,即病人把期望投射到了医生的身上;而在这个案例中,还存在另一种潜在的移情,医生把期望投射到了病人的身上——这是精神治疗的交互过程中的一个难点。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内心中较少暴露的一面也会浮出水面。在治疗结束后,双方的问题都没有被完全地解决,又或者,二人若即若离的关系会维系很多年。
直到我发现未曾预料到的命运之轮也开始转动,于是我最终断绝了和她的关系。当然,她开始有计划地引诱我,而我则认为这是不合适的。现在,她开始寻机报复。
史毕莱的信,以及流言都已经传到了弗洛伊德这里。他以自己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建议道:
这样的经历尽管是痛苦的,却是必须且难以避免的。没有他们,我们不能够真正地理解生命,也不知道我们在对付的是什么。我自己从来没有卷入如此糟糕的状况中,但有许多次我离它非常近,然后擦肩而过。
我相信,只有两点使我从类似的经历中得以逃脱:其一,我的工作所必需的冷酷;其二,我成为心理分析师的年龄要长你10岁。但没有伤害是永恒的。它们帮助我们进化出厚厚的保护层,帮我们控制“反移情”。毕竟,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这些女人在达到她们的目的之前,会用设想到的所有完美的精神表现来魅惑我们。她们所用的手段堪称自然界最壮观的景象之一。一旦目的达成,又或者相反的情况已经难以扭转,之前璀璨的星空就会产生令人惊奇的变化。
史毕莱发出的多封信件将弗洛伊德也卷进了此事。为此,弗洛伊德给出了更多父亲般的建议:“不要过度悔恨,也不用过度反应。”随着时间推移,事态渐渐减弱,荣格也卸下了肩上的重压。
关于史毕莱的事情,我有一个好消息向您报告。之前,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太消极了……前天,她出现在我的房子里,与我进行了一场大方得体的对话……她已经通过一种最恰当、最友好的方式把自己从移情的状态中释放了出来,而且也不会陷入复发的痛苦中……尽管我并没有屈服于无益的自责中,但对于自己犯下的罪恶仍然深感遗憾,因为对于病人不切实际的期望,我才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我曾经和她讨论过孩子的问题,我以为自己是在进行理论化的说教,但事实上这是潜藏在背后的本能。因此是我自己输出了所有的其他愿望,却完全寄希望于我的病人不要从我身上看到这些东西。情况变得越来越紧张,以至于继续保持这种关系的话就必然会以性关系收场。为此,我采取了一种并不能够被认为是道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我被自己的错觉迷惑,以为自己是她性引诱的受害者。我写信给她的母亲,说自己仅仅是她的医生,而不是她性欲的满足者,并声称她应当把我从这段关系中解放出来。考虑到这位病人不久前还是我的朋友,而且欣赏我满满的自信,我非常不情愿地向如同父亲一般的您承认,我的行为有一些无赖的作风。
然而,儿子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1909年是弗洛伊德和荣格关系的巅峰,也是他们关系的转折点。那年的春天,两个男人进行了他们的第三次家庭聚会,荣格和艾玛与弗洛伊德一家共处了5天。荣格的自传对此次拜访进行了描述,记录了两个人在最后一晚浮现出来对待通灵现象的态度差异。
我对弗洛伊德关于预言能力和超心理学的看法非常感兴趣。1909年,当我前往维也纳拜访他的时候,我询问了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但他具有的唯物主义偏见使他从一种非常浅薄的实证主义观点出发,拒绝承认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并且认为它们是荒谬的、无意义的,以至于我很难再对溜到嘴边的尖刻的反驳进行审查。而在很多年后,他才认识到超心理学的严肃性,并且承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
尽管弗洛伊德仍在讲述着他的观点,但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我的横膈膜是用铁做的,正在变红、发热、发光,并且拱起来。就在那时,紧挨着我们的书柜传来了很大的爆裂声,我们被吓得跳了起来,害怕书柜会倒向我们。我对弗洛伊德说:“瞧,那个就是所谓的催化的客观化现象。”
“它不是”我回应道。“您错了,教授先生。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现在预言,马上会有另外一声爆裂的响动。”果然,我话音未落,同样的爆裂声又在书柜中响起。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为何会如此的肯定。但毫无疑问的是,我知道那爆裂声一定会再发生。弗洛伊德只是惊讶地盯着我……这次事件引发了他对我的不信任。我意识到,我已经做了一些违背他意愿的事情。
来自库斯纳赫特的辩论仍在继续。荣格声明,那次拜访的最后阶段“把……我从您父权的压抑中解放了出来”,而弗洛伊德回复道:
非常奇怪的是,就在那个晚上,我正式地接纳你为我的长子,为你施以涂油礼……选定你为我的皇储和继承人。而你大概已经剥夺了我父权的尊严——此事似乎给你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并且和我从你的加冕仪式中获得的乐趣一样多。现在,如果告诉你,我对那次吵闹鬼现象的看法,我担心会重新回到父亲的角色。但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的态度并非你想象的那样。我不否认,你的故事和你的实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开始,我是倾向于接受其……作为证据的,如果那些时不时响起的声音在你走后不再出现。但是,自那以后,我又多次听到了声响。因此,当我考虑你和你特殊的问题时,它们并不会与我的思想产生关联,也绝不会产生关联。我的盲从,或者我相信的意愿,随着你存在时的魔力一起消失了;再一次的,出于一些我也不太了解的内在原因,让我相信这种现象的存在是非常不可能的……因此,我再次戴上了代表父亲权威的“角质架眼镜”,告诫我亲爱的孩子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因为,如果需要牺牲很多才能了解一些东西,倒不如不去了解……
而结果是,我将收到你对幽灵现象所做研究的进一步消息,因为你已经陷入使人陶醉的错觉之中,而你本不该一个人参与的。
但是,在那天晚上,对待灵魂现象的态度并不是他们之间的唯一分歧。
我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弗洛伊德对我说的话,“亲爱的荣格,答应我,不要抛弃性欲理论。那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信念,一个毫不动摇的堡垒。”……在一丝的吃惊中,我问他:“一座堡垒?抵御谁?”对此,他回答道:“抵御那黑色的泥潮。”这时,他犹豫了片刻,补充道:“来自神秘主义的”……正是“堡垒”和“信条”这些词汇惊醒了我……不再有什么是和科学的判断相关的东西了,有的只是个人权威的驱动。
正是这件事情击中了我们“友谊的心脏”。我知道,我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态度。事实上,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是指宗教和哲学——包括同时兴起的超心理学——所了解的关于心灵的一切。
6个月之后,两人从美国载誉归来。在旅途中,由于相信所谓的针对“父亲”的“死亡愿望”,弗洛伊德变得焦虑起来,在荣格面前展现了自己软弱的一面,类似的情形只发生过两次。这次旅行对他们的关系造成了又一次的打击。
我们每天都待在一起,分析彼此的梦。在那段时间,我做了很多重要的梦,但弗洛伊德并不能理解。我并不认为这能够反映什么,因为即使是最好的精神分析师也有解不开的梦之谜。这是人类的无力之处,而我从未因为这个理由想要中断我们对梦的分析。相反,这些分析对我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常有价值。我把弗洛伊德看作一位成熟且经验丰富的长者,在这方面,我则希望是他的儿子。但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给我们整体的关系重重的一击。
弗洛伊德做了一个梦,梦里包含的问题不适合公开。我竭尽全力对它进行解释。我还告诉他,如果他能够多提供一些私人生活中的细节信息,我就能够做出更多的解释。弗洛伊德对此的反应却是一个古怪的表情——一脸的极度怀疑。然后,他说:“但是,我不能拿我的权威去冒风险!”在那一刻,他失去了所有的权威。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件事也成了我们关系结束的前兆。弗洛伊德竟然把个人的权威置于真理之上。
两条激流正在荣格处汇聚。许多带有象征意义的谜一般的梦把他带到了心灵的更深处,一个他后来称之为集体无意识层的地方。结果是,他一头扎进了新的研究领域——神话学、考古学、基督教诺斯替主义、原始文化以及占星术,并且开始写作命运之书,开始考虑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
与此同时,这位成功的职业人士取得了更多的荣誉。在弗洛伊德的支持下,荣格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及其科学期刊的主编。在纽约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学之后,他被授予了荣誉博士头衔。《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的第一部分也出版了。
在弗洛伊德对荣格的家庭进行了4天的拜访之后,艾玛·荣格发现了二人关系中的不和谐之音。在她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写信给弗洛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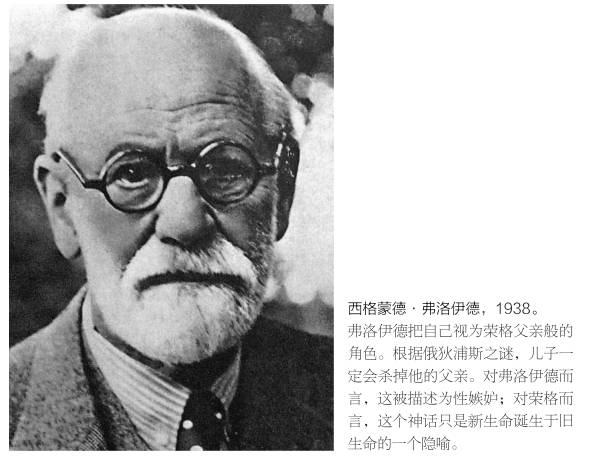
自从您拜访之后,我一直被一个念头所困扰:您和我丈夫的关系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既然如此,我希望能尽我所能去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多疑:不知何故,我认为您并不十分同意《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中的观点。您从来没有谈论过那本书,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们愿意开始对它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对你们两人都会有好处。或者,还存在其他的问题?如果是的,请您告诉我,亲爱的教授先生。因为我无法接受您如此的认命。我甚至相信,您的认命不只会发生在您真正的孩子身上……也会发生在您精神上的孩子身上。如果不是如此,您根本没必要认命。
您或许可以想象得到,您对卡尔的信任令我感到多么的兴奋和荣耀,但在我看来,您有时给予的太多了。您难道没有发现他的信徒比您需要的还多?难道一个人经常地付出不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回报?
为什么您会开始考虑放弃,而不是去享受您应得的名望与成就?
不,您应当高兴,应当饮下胜利带来的全部的喜悦,在您奋斗了如此之久后。不要以一种父亲般的感觉去思考卡尔:“他将会长大,而我必定衰落”;您应该以一个人类个体思考另一个人类个体的方式去思考卡尔。他像您一样,有自己的使命要去完成。
艾玛发给弗洛伊德的最后一封信显示了荣格婚姻关系的现状——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
衷心地感谢您的来信。请不要担心,我并非总是像上一封信中表现得那样沮丧和失望……通常,我总能走在自己命运的轨迹之上,能够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但有时,我也被内心的冲突折磨:我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不完全依附于卡尔。我发现自己没有朋友,除了少数无聊而且非常无趣的人,所有常和我们在一起的人其实只是想看到卡尔。
当然,女人们都很爱他;而和男人们在一起时,他们会立刻把我作为父亲或者朋友的妻子加以隔离。然而,我也有强烈的人际需求。卡尔也说,我不应该将焦点只放在他和孩子身上。但是,我到底该怎么做呢?由于我强烈的自恋倾向,这也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绝对不能和卡尔进行竞争。为了强调这一点,我常常在人前讲一些极端愚蠢的话……
您现在或许理解了,为什么当我想到自己可能已经失去了您的关心时会觉得如此的糟糕。我也担心卡尔或许注意到了些什么。至少,他现在知道我们在交换信件,因为他吃惊地发现您有一封信是寄给我的。但是,关于其内容,我只透漏了一点点。
一个会改变生活的抉择正在向荣格逼近。他要如何处理《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中第二部分的研究?他对这些研究的理解揭示了力比多概念和乱伦禁忌的多个方面,而这些理解与弗洛伊德观点的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