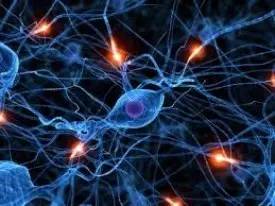本书的写作构想,在某个晚上如一不速之客翩然到访。它显然认为会盘桓颇长一段时日,而我知道有它做客家中会大损我的名声。藏宝图和密径是童年的玩意儿。成人学者看到未被发现的上古世界豁然呈现眼前,且海图、使用手册、指南一应俱全,必然怀疑自己脑袋是不是出了毛病。
当时我住在英格兰某山上的茅屋里,那山位于牛津西边,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诗中那位吉普赛学者(ScholarGypsy)活动的土地上。那里的环境就如孩童的奇幻世界,是历史秘密似乎如野生苹果树上结实累累的苹果般随手可得的那种地方。花园里除了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野餐残余物和发亮、降解的20世纪垃圾,还有烧过的燧石、经过熔炼的金属块、烧制粗糙的屋瓦。我在一棵枝叶缠绕的卫矛底下,找到一只铁器时代的小胸针,胸针上有3个同心圆构成的花纹,胸针的系针受腐蚀已残缺不全。住隔壁的农夫把几个纸箱的古物给我看,里面有用来磨碎东西的磨石、萨摩斯细陶器(Samianware)、罗马钱币,都是他在田里干活时犁出土的。
这个宁静的地方,名不见经传,却曾是繁忙的交通辐辏处。花园的一侧曾有一条马道,位于一条罗马古道(straet)的尽头。这条罗马古道沿着耸立于泰晤士河畔的石灰岩断崖,通往伯克郡丘陵(BerkshireDowns)和刻画于一处丘陵上、被称为"乌芬顿白马"(UffingtonWhiteHorse)的铁器时代巨型图案遗迹。花园另一侧则曾有一条未铺砌的道路从名叫巴布洛克海司(BablockHythe)的泰晤士河渡口往上攀升,而今此处既无桥梁,也无津渡。早在牛津这个地名出现之前,千百年来一直有人将牛只羊群从泰晤士河边往上赶到这两条路交会之处,那里是一片宽阔的草地,上有一泉水和一池塘。这是昆诺(Cumnor)村的前身,距后来才出现、在教堂附近的中世纪城区12分钟路程。较晚近才出现的园篱和停车位让人看不到此村前身的轮廓,但从楼上窗户望出去,仍可能看出它当年的形状。这个聚落距今太远,其布局未见于文献记载。有座铁器时代的山堡(hillfort),俯临这个位于泰晤士河冲积平原上法穆尔(Farmoor)一地的史前聚落,而一道险峻的土堤,以及使现代道路到此变成一危险大弯的圆形布局残迹,很可能就是这座山堡的遗物。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长期陷入历史幻觉状态,也就不足为奇。楼上房间那位教人难以拒于门外的访客,在打印成两张大纸的西欧地图上以一条斜线的形态现身。那时我一直在计划单车远征,走一趟赫拉克勒斯古道(ViaHeraklea)。赫拉克勒斯古道就是传说中希腊神祇赫拉克勒斯(译者按:Heracles,罗马人称作Hercules),从世界的尽头--伊比利亚半岛西南端的"圣岬"(SacredPromontory)--越过比利牛斯山和普罗旺斯平原,朝向如白色屏障的阿尔卑斯山的著名路线。这位英雄带着偷来的牛群前行,在西方世界最古老的路径之一留下传颂千古的足迹。他所走的路线,如今有许多路段只能诉诸想象,它只是一条把与赫拉克勒斯有密切关系的诸多地点串联起来的假设路线。这条古道通过南法的地中海岸时,有一些路段会变成小径,有时循着季节性迁徙牲畜的小路走,有时变成罗马图密善古道(ViaDomitia)和现代A9高速公路。这些实际存在且实用的路沿着西班牙东海岸往北走,在法国境内转向东北,最后蜿蜒通往意大利。但赫拉克勒斯古道,照其原来存在于神话中的路线,乃是直直一条线,就像把高山浑然不当一回事的神之子所走的路线。
这条横越大陆的斜线,有两点值得推敲。首先,如果把现存的那些路段朝两个方向投射,赫拉克勒斯古道就会循着同样的东北东方位延伸1600千米,抵达阿尔卑斯山的蒙特热内夫尔(Montgenèvre)山口,即凯尔特人所谓的马特罗讷(Matrona,"地母神之泉")山口。据说这是赫拉克勒斯砍穿岩石硬开出的山口。这仿佛是他从圣岬启程时,就带着某个古老的定位工具,借此得知他会在那个地方越过阿尔卑斯山。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乃是打印地图上出现熟悉的轨迹。许多上古文化,包括凯尔特人、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建庙、墓、街道时,若非让它们面朝至日初升的太阳,就是把它们建在与至日的旭日有某种几何关系的地点上--就罗马人来说,这样的作为只偶有一见。至日一年两次(6月21日和12月21日左右),在这期间,太阳升起、落下的地方一连数日几乎没变。我查阅了在线天文资料,发现两千年前,在地中海某纬度,赫拉克勒斯古道的轨线正是夏至时旭日的角度,或者如果观察者面朝另一方向的话,就是冬至时日落的角度。
这一重大的巧合一直无人察觉。或许它的壮阔格局反而实际上使它藏于无形,就连最不抱怀疑论的历史学家都会怀疑它的存在。但它还能导向其他如此多可证实的发现,让人觉得它似乎不时颇具主见,是来自另一世界,无意间被重新启动的机械装置。它造成的旅程往往要花掉数年,但开始才几个月,旅人就看出这条至日路径是人所刻意创造出来。德鲁伊特(Druid,凯尔特人的祭司或科学家)不管站在古道的任何地方,都知道沿着它的走向往西看,就是望向世界的尽头,那里除了怪物出没的海洋和亡魂地域,别无他物。往相反方向看,则是望向阿尔卑斯山和马特罗讷山口,太阳就是穿过那山口,回到活人的世界。
渐渐地,第三个巧合自行浮现。几年前,为《非典型法国》(TheDiscoveryofFrance)一书的撰写做研究时,我读到一个谜样的名词:梅蒂奥拉努(Mediolanum,今米兰);古凯尔特人把不列颠与黑海之间约60个地方都取了这个名字,其中包括意大利的米兰。它的意思近似"中央"或"中间处"的"圣所"或"神圣围地"。梅蒂奥拉努一词被认为与在其他神话里也可见到的一个观念有关:认为人类居住的世界是"中土",该世界的圣地与位于上层世界、下层世界的地方相对应。在古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神话中,相对应的词是Midgard,托尔金就用此词替《霍比特人》《魔戒》中的虚构世界取名。
1974年,有位名叫瓦岱(YvesVadé)的文学教授表示,凯尔特人根据一网络来组织这些"中间地",且把它们安排成每个中间地与其他两个中间地等距。1994年,巴黎-索邦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德·普朗霍尔(XavierdePlanhol)采用这观点,推断这一网络或许曾在日常生活或宗教上短暂发挥作用,但在早期阶段就遭扬弃。不过随意散布的点也会产生类似的结论,这个观点还有其他问题,本书后面会提及。尽管如此,这个地名还是让人好奇,特别是因为我探究这条路线所有高卢语(Gaulish)地名的词源之后,发现在赫拉克勒斯古道上或其附近,有六个地方曾叫作梅蒂奥拉努。
那之后,"巧合"出现的频率高得出奇。一个复杂、美丽的图案于焉浮现,它是根据太阳路径布局,辅以基础的欧几里德几何学。我在仿佛从某个奇迹似保存下来的文献里,开始看到现代欧洲的古代起源。那些名叫梅蒂奥拉努的地方,都属于这个大陆绘制地理方位的过程中一个早期且相对较混乱的阶段。从诸多地方体系不断孕育的混乱中,一个庞大的网络逐步形成。西方世界的地理被组织成一个由诸多"至日线"构成的格网,这面格网以最早的赫拉克勒斯古道为基础,具有经过精确测量以决定神庙、城镇、作战位置的经线和纬线。在更晚期阶段,高卢的一些长程道路被当成至日线的化身建造竣工;不列颠群岛也出现同样现象,且更为壮观。罗马帝国的喧嚷和好战淹没了对那一格网的认识,致使上古世界的奇观往往犹如从未存在过一般。
有几个月时间,我循着赫拉克勒斯古道和地图上的其他路线走,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用鼠标一再行走这些路线,而且速度想必就和真老鼠实际行走这些路线时的平均速度一样。10年前,没有数字地图和地图绘制软件,因此大概进行不了这样的虚拟旅行--而这也可以解释一般人都会有的一个疑问:"为何以前没人想到这个?"或许曾有人想以纸面地图做类似的事,但那么做的话,需要一票受过训练的助手和一张大小如飞机棚的桌子(还需要一架飞行器)。这趟虚拟考察的结果--和那些结果所激发的实地考察结果--就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读者若有耐心走完这趟路程,走过这路程中遍布碎石瓦砾的郊区,将会了解这张地图的独特之处,且有机会抢先检视说明这段路程之演变的一些例子。
这张地图的意涵非常特别,让人无法忽视,或者说,令人无法置信:除了在侏罗山区某湖附近找到的一面青铜盘上的阴-阳历(靠计算机之助才得以部分破解的阴-阳历),这是说明德鲁伊特科学与其成就的第一个证据,而且是可用数学验证的证据。事实上,它是史上最早的精确世界地图。这一跨大陆的神圣地理学杰作,以阿尔卑斯山外某处为一端往另一端延伸,最远似乎延伸至不列颠群岛,且说不定远至公元前4世纪时探索者马赛的皮西亚斯(PytheasofMarseille)所看到的那些北方偏远岛屿。在那些偏远岛屿区,海洋如肺一般起伏,与天交融为一。
定睛细瞧地图上的一连串线条,最后肯定会像算命仙在其茶杯里看出人的命运般,在地图上看出一个图案。对学者来说,不管从事哪种研究,激动兴奋之情是损友:愈是令人激动的理论,理论家愈是希望它为真。我努力想证明这理论站不住脚,为此又花了数个月。我离开那神奇的茅屋阴影,投入现代图书馆节能减碳的阴暗空间。耗费在另一个世界的时间绝没有白费,因此,即使这理论已被史实和考古发现打入冷宫,它仍会在令人失望中让人获益。但我愈是努力要证明它站不住脚,冒出的证据愈多。2009年10月,我读到洛桑附近某水泥矿山挖出凯尔特人圣所的考古发现消息,那是瑞士境内所发现最大的凯尔特人圣所。它位于埃克莱庞(Eclépens)附近,一座名叫穆尔蒙(Mormont)的山丘上。我看着德鲁伊特路径所形成的地图胚胎,图上数条与赫拉克勒斯古道一模一样的路线和经纬线纵横交叉,穆尔蒙山就位于其中一条长线上,靠近某个重要的交会点。
这时,我拟好写作大纲的口头报告,把构想告诉我的出版人,于是有了两次会晤。一次在伦敦波多贝罗路(PortobelloRoad)附近某个安静隐秘处的地下室,另一次在曼哈顿中城区某位德高望重之绅士的俱乐部里。公司总经理向我保证,俱乐部已检查过,没有监听装置。我描述了我的发现,要那些以把事情公诸于世为职业的人誓守秘密。我不是顾虑谁偷走我的构想,毕竟那构想不像数学等式或魔咒那么容易拿走:我是担心如果有人向外透露这个计划,大学不同学系里的友人和熟人会不得不佯称那无懈可击。
凡是以德鲁伊特和隐然有神秘秩序的地景为题写作的人,或凡是声称已在某个田野、街道、火车站或水泥矿山找到"中土世界"之太阳路径交会点者,都必然对他人的怀疑有心理准备。当中最简单的形式,会让人联想起"灵线"(leylines)。而且我不安地察觉到,命运的讽刺捉弄已使我住进一间名叫灵线度假小屋(LeysCottage)的房子里。"灵线"是1921年业余考古学家瓦特金斯(AlfredWatkins)所发现,或者照某些人的说法,由他捏造出来。他认为史前遗址和其他"古"遗址直线排列的布局,乃是新石器时代贸易商所走的"古老的直线"(OldStraightTrack)的残余。瓦特金斯深信那些直线原被称作"灵线",因为ley这个字(意指"草地"或"牧草地"的常见地名)出现在其中许多直线上。他的研究工作包含踩踏土地以探查古墓地遗址的凹陷程度。他使原本对英格兰地景的古代布局浑然不察的世人从此留意这方面的现象,且创造出让人乐在其中的寻找灵线的历史消遣,然而他把不同时代混为一谈,却令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感到厌恶。但经过90年愈来愈精密的勘查和挖掘,证明他发人所未发的想法很有可能有其道理:新石器时代的人绝对有能力辟建出那些经过精心校直的长程路径。
本书涵盖的时间(约公元前800到公元600年),始于新石器时代结束(约公元前1700年)将近1000年后。后人称之为凯尔特的那些文化,属于铁器时代(让人望而生畏的名称),而铁器时代也是精确工具、高速运输工具、作物轮种与土地管理、年轻人受知性教育、欧洲第一批城镇问世的时代。因此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凯尔特世界发源于要再往前推进好几百年的青铜器时代晚期。这两个时代都属于史前时代。史前一词被广泛用来指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时期;它也能用来指称从微生物开始在黏稠原生汤里活动,到60代前才出现的文明世界之间的任何时期。在不列颠,"历史"时钟直到公元前55年某个夏日早上10点,凯撒在肯特郡岸外下锚时,才开始滴答计时。来年,他带着水钟回到该地,测量英格兰夏日白昼的长度(比在欧陆长),结束了当地的史前时期,至少结束了英格兰南部的史前时期。
对某位法国考古学家来说,古凯尔特人并非"史前"人,而是"原史时代"人。他们称不上是我们所能见到、听到的邻居,但也不是没有名字、没有面孔、建造了巨石阵的缥缈人物。对凯尔特人来说,巨石阵是神秘的古迹。他们的著作未在罗马出版,未被分类收入亚历山德拉图书馆,但透过古希腊罗马的旅人,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习俗、信仰、时尚、饮食。他们的神话和传话,有一部分保存在诗里,为此后数代吟游诗人记在脑中,被外国作家记录下来。德鲁伊特禁止用文字表达他们的智能,但他们的社会肯定是识字社会,因为后人在凯尔特世界各地找到书写工具。就已死的语言来说,古高卢语生气勃勃,教人吃惊:一直有刻了铭文的盘、罐、硬币、咒符出土,而且这个语言虽在公元6世纪时已几乎灭绝,其词素却如尸体上的毛发继续在增长。
原史时代的欧洲居民,有一些人留下名字,为我们所知: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遭处死的暴君之子和高卢反罗马入侵行动领袖;狄维基亚库斯(Diviciacus),与西塞罗同时待在罗马城并曾在罗马元老院演说的德鲁伊特学者和外交官;卡尔提曼杜亚(Cartimandua),与入主不列颠的罗马人合作的布里甘泰斯部族(Brigantes)女王。我们知道许多他们城镇的名字,知道那些城镇的样貌。若有考古学家靠时光机回到铁器时代,还是有足够的能力被当作是古凯尔特人,尽管他只是个半文盲的凯尔特人,对凯尔特语汇所知不多,而且多半是特别下流的语汇。
通过肯定是学术史上最了不起的集体行动,考古学家对凯尔特人有了惊人广泛的了解,尽管如此,已遭遗忘的凯尔特人世界,却像是个并不存在因而谈不上被遗忘的地方。在法国,到处可见罗马统治的那段过去。在赫拉克勒斯古道某些泥土路段上,它被脚踏车胎辗得咔兹咔兹响;在颓圮的山堡边墙上,它侧身废弃物之间。在旧称卢格杜努姆(Lugdunum)的里昂,市中心的白莱果广场(PlaceBellecour)上,我于清晨交通高峰时候坐在混凝土长椅上。地面已被挖土机翻搅过再粗略弄平,以便整成新平面。一些橘色陶器碎片躺在自外地运来的红沙上,非常显眼。我弯身捡起五块古罗马陶器的小碎片,其中一块带有葡萄酒杯的罗纹,跟附近罗马帝国治下高卢文明博物馆(MuséedelaGallo-Romaine)所展示的酒杯很像。在我左边,隔着植有椴树的大道,我能看到高高立在索恩河(Sa?ne)旁上方的富维耶圣母院(Notre-DamedeFourvière)。凯撒《高卢战纪》的读者能轻易分辨此河与附近罗讷河(Rhone)的差别:凯撒写道:"有条名叫阿拉尔(Arar)的河,流经艾杜伊人(Aedui)和塞夸尼人(Sequani)的土地,流进罗达努斯河(Rhodanus),水流非常缓慢,教人看不出往哪个方向流。"这座巴西利卡式(译者按:一种古罗马的公共建筑形式,呈长方形,有中殿和侧廊)教堂的所在地,据推测原坐落着被称作奥皮杜姆(oppidum)的高卢人山堡,但这座存在于罗马时期之前的城市,如今已几乎荡然无存,因而无人知道卢格杜努姆的最早居民住在哪里。
那些以会毁坏之物为材料,而不像罗马人以石头为材料的部族,以及拿和脑部组织一样不耐用的东西来记录自己历史的部族,不可能被视为现代世界高度发展的先驱。今日高卢人对自己凯尔特先民的漠不关心可以理解。维也纳某博物馆的部门主任,在馆长决定不展示凯尔特金币藏品后向我解释:"他们输了(意指输给罗马人)。"留存至今的残片不受看重。存放在博物馆库房的金币,有一些是前基督教世界所留下的最美对象。总有一天,收藏家会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21世纪初期的拍卖目录看,遗憾生不逢时,未碰上用一台电视机的价钱就能买到上古艺术品的时代。
凯尔特世界比我们认为的还要近似我们的世界,但它发展的样式却属于一个大不相同的文明。古凯尔特人--据古希腊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Siculus)所述,特别是高卢凯尔特人--乃是最难懂的民族:"他们用寥寥数词和谜一般的话语交谈,大部分时候莫测高深、拐弯抹角陈述事情,明明用的是某字,表达的却是另一个字的意思。"凯尔特钱币、雕刻、武器、器皿上的奇怪象征符号,出自在德鲁伊特督导下工作且可能本身也是德鲁伊特的艺术家之手,这提醒后人凯尔特人制造的任何东西都有隐而不显的意涵,他们的秘密并非全部无法探明,因为他们谜语的解答往往就在可见的世界里。决意把探索的触角延伸到本书之外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凯尔特人按照他们神祇的形象所重造的世界,并非必然把人带离现在:"中土世界"存在,而且如今我们许多人就置身其中。
选自《中土世界:欧洲的古代起源》
责编:苏龄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