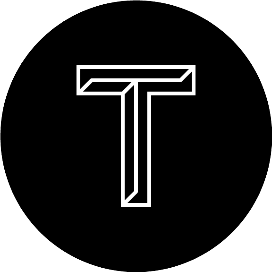或许,没有人比各大品牌幕后勤勤恳恳的设计师更了解时尚创意系统
(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
的运作规则了。在成长期,他们接受的职场培训是成为设计师,而不是普通员工 —— 这个过程让他们得以熟悉不同设计部门、产品分支的运作,进而随时随地辅助上级,完成设计作品。
然而,一旦进入现实世界的工作环境,面对堆积如山的障碍和强度时,他们的心理或生理上就一定会发生某些变化:有的因为职业生涯举步维艰,被压垮了创造力;有的在团队中遇到志同道合的前辈,灵感无限迸发;有的摆脱了「天桥骄子效应」
(The Project Runway Effect,指认为制作服装或创立品牌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开始逐渐正视期望与现实生活并不一致的事实。
即便压力如此之大,时装产业每年还是吸引着大量的创意工作者怀揣梦想,「义无反顾」地驰骋于各大时尚集团的声色场中。成文前,我向几位资深的人事主管咨询了当下设计师和设计师助理的就业情况。以 LVMH 集团为例,人力资源和协同管理执行副总裁 Chantal Gaemperle 表示,「由于缺乏熟练手艺人,集团的职位依旧极度空缺。其中,皮革工、珠宝匠等依赖手艺的职位都亟待填补。截至 2024 年 6 月,这样的岗位有 3 万个空缺。至于设计岗位,则处于『供过于求』的局面。」
据估计,每年毕业的时装设计专业学生约占该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 10%,能顺利进入一线品牌的机会却微乎其微 —— 在美国,服装设计行业每年必须腾出 1700 个工作岗位,才有可能跟上每年新生毕业的速度;而在意大利,有 47.5% 的时装公司表示难以寻觅到多边形人才。
插画师 Distinctor 为《T》中文版创作了这张
以人台为主要意象的插画。人台是时装设计的必需工具,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创意的人才过剩,另一方面则是鲜有人具备过硬的动手技能。在采访创意团队中的「幕后设计师」时,很多人都在试图厘清一个常见的误区,即名校毕业固然重要,但品牌在招聘过程中,更看重应聘者的天赋、性格、价值观、文化背景、工作经验和执行能力。这意味着无论你的大学专业是建筑设计或艺术研究,只要你能在面试时递上一本让创意总监觉得「匹配度」超高的作品集,再自信地陈述以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获奖情况,一切皆有可能。
「你能想象吗?在作时装设计师之前,我曾是个负责软件开发的工程师。整个转变过程花了我 15 年。」目前正在某独立时装品牌工作的 William 出于对艺术和时尚的热爱,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了法国的设计院校。「面对这条道路的最佳状态是无限的奉献精神,但共同信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记得当初自己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品牌,是因为我对各种想法的组合让创意总监认为,我是一个值得被培养的人。你可以理解为是强大的逻辑思维打动了他。」William 继续解释,「创作过程的基础方法就是研究。一个想法不经意间出现了,但大量的研究才会让它出彩。这是一种对完全沉浸于丰富项目并赋予其价值的痴迷。」
这条道路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永远不会与他人的道路雷同。William 会利用个人能力形成独特的创作模式,结合各种形式演绎来完成工作。「向上级表达创作想法让我想到了招标会。其实挺残酷的,一旦我的故事不能完全吸引他,一切努力就都『归零』。所以我需要在他提出大方向后,尽可能多地发散思维,去搜集更多材料。」采访时,我试图让 William 以平时汇报工作的方式解释 2025 春夏系列的设计思路。他从平面设计、Deep House 音乐、雕塑家 Richard Serra,聊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漫画、Ernst Bergman 的电影和意大利作家 Dino Buzzati —— 即使无法看到新系列的相关图片,我已然在他的文字描述中建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Luca 是一名常驻巴黎的设计师,目前供职于一家集团旗下的男装品牌。工作前,他已经获得了设计学士学位,并在某些大品牌实习过。「3 年前,我通过面试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1 年后,因为公司需要一个长期职位,我就正式签了合同。我从事这一行,根本没有任何人脉,而是凭借兴趣摸着石头过河。但我的个性很像一块『海绵』,在大学时期打好基础,用 Photoshop 绘制效果图,了解配饰的内外构造,并且在毕业典礼上向一些专业人士展示了毕业设计;入职后,很多同事和工匠都是工艺方面的专家,他们可以协助我把草图变为现实。」
然而,Luca 的幸运并不能代表大多数设计毕业生的求职情况。虽然会经历同样的程序,但在毕业季时,只有少数佼佼者会参加一场备受瞩目的时装秀 —— 由学校策划,嘉宾名单上有时尚「精英」,记者、买手、造型师,一切与时尚行业相关的人物都会到场。毕业秀可以为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帮助,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还能为新人提供被大品牌青睐的机会。
2023 年,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时装设计专业的部分硕士毕业作品在大型零售商上架,有的毕业生甚至获得了 LVMH 奖项或英国时装协会 NewGen 基金。每个人都幻想自己会是下一个 Alexander McQueen 或 John Galliano,无论是通过时装秀还是 TikTok 的病毒式传播,只要能被更多圈内人士关注,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就多了一分。
然而,即使顺利获得品牌的工作岗位,日后在职场中出现的困难也带着一丝出其不意的艰辛。「大量的配饰需要在佛罗伦萨完成制作,还有一些原材料的筛选离不开意大利人的帮助。但材料供应商和制作工人等基层人员的英语能力几乎为零,所以我得靠大量的肢体语言交流。整个过程相当滑稽。」另一位已经在时装设计行业工作 12 年的受访人 Julia 指出,这只是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毕竟她还可以靠 ChatGPT 翻译。但在说服上级以及与同事相处的过程中,总是潜存着更大的问题:「当我拿着相当充分的材料来展示设计时,其他同事也在现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个人风格,难免会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登上 T 台而在总监面前据理力争。我承认有时候会带有一点火药味,甚至是撕破脸。但团队越成熟,这种情况就会越少。」
滑动查
看 Bottega Veneta 创办的工艺与创意学院。
2023 年 10 月,Bottega Veneta 正式创办了工艺与创意学院
(Accademia Labor et Ingenium)
,力求借助学校招新,为品牌培养一批对手工技艺拥有不懈追求的未来人才。学生聚集于此,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工作坊和课程,向大师学习,以争取毕业后直接参与品牌的生产核心工作。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受访者 Valentina 作为已经从业 7 年的高级定制品牌的设计师,在入职之初,几乎不可能从高级定制开始做起。「我在一个裁缝家庭长大,9 岁起就开始跟妈妈学习针线活。我的理想就是为客户量身定制,毕竟一年制作 10 件作品,比制作数百件摆放在购物街的成衣,更能让我获得成就感。但现实总是很『骨感』,初来乍到的毕业生并不具备直接进入高级定制团队的资格。再加上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诸如 Bottega Veneta 的培训项目,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成衣部门的实习生熬到正式员工,再想尽办法通过作品来证明我有资格参与高级定制的设计。之后,当我如愿以偿,我又发现团队里有很多固执的老人,我需要不断地沟通才能实现设计稿。总之,整个奋斗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体制浪漫化了,没有一个当权者真正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任何行动,扶持那些努力且具有天赋的人。」
在与受访者的交谈中,不少人多次提及时装从业者的权利。其中一位来自高奢品牌的设计师表示,人们往往会把时尚圈的压榨讨论与第三世界国家收入微薄的服装工人联系起来,诸如《真正的成本》
(The True Cost,2015)
等纪录片都在试图揭开资本主义伪善的一面。但讽刺的是,却鲜有媒体提及无薪实习生或低薪设计助理的处境。
滑动查看纪录片《迪奥与我》剧照。
10 年前,纪录片《迪奥与我》
(Dior and I,2014)
讲述了 Raf Simons 为 Dior 创作首个系列的幕后故事,其中有一个让女裁缝表达观点的片段。她们描述了时装秀的壮观场面,尽管所有衣服都由她们亲自缝制,但在这场华丽盛会上,她们的存在感少之又少。6 年后,意大利人类学家 Giulia Mensitieri 出版了《The Most Beautiful Job in the World: Lifting the Veil on the Fashion Industry》
(2020)
一书,这是一部关于时尚产业及其从业人员的案例研究,以非常尖锐的方式掀开了整个时尚产业的暗面。研究过程中,她特别关注了年轻创意人员的工作条件,例如,他们的报酬往往是代金券或特卖衣服,而不是正式的薪水。
Mensitieri 的研究历时 4 年,收集了 50 个她认为受到剥削的员工案例,并表示,「尽管时装业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它被一个矛盾的规则支配,即一份工作越能积累声望,越能获得象征性和物质性的认可,它的报酬就越低。」在一个案例中,一位专业从事高级定制服装的裁缝师,月薪只有 800 欧元。多年来,时装产业并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太大改变,创意总监在时装秀谢幕时介绍整个团队,仍被视为一件稀罕事。甚至很多设计师只有在阅读过这本书后,才逐渐意识到自身目前的处境正是一种「被剥削」。
Me
nsitieri 出版的《The Most Beautiful Job in the World:
Lifting the Veil on the Fashion Industry》一书,
Aki 是受访者中的一名亚裔,曾在巴黎任职于某先锋品牌。毕业之后,他怀揣着一腔热血来到巴黎,虽然经受住了多次面试的求职压力和多年加班的工作强度,但最终还是在「低收入」这个因素上败下阵来。「我们确实有权利,能根据工作合同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然而,每当我们试图将这些规则和法律落实到日常工作,就总会被认为不够敬业或不够积极。」Aki 暗示的规则是对工作时长的评估。如果一个人试图平衡工作和生活,按点上下班,就不得不担心失去职位。「可悲的是,一旦你被淘汰,你就出局了。加上我是个外国人,需要工作签证才能在欧洲定居,品牌深知我们的短板,就会利用这一点变本加厉地剥削。」
「
和工作量相比,我们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周期很短,所以必须在有限时间内疯狂地完成任务。不配合的人是会被踢走的。」Luca 补充道,「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通常不会真正考虑合同中的内容和工作时间。这种文化导致了工作条件的不稳定。但说实话,我们其实也意识到合同中存在一些霸王条约,但因为炽热的情怀,就会选择性
地忽视。」
或许从一开始,你就被当成了一个可替代的角色 —— 即使是在学校,如果不夜以继日地工作,不牺牲残存的每一丝闲暇,梦寐以求的推荐信和工作就会花落别家。静奢品牌的设计师 Paker 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日常:从早 9 点工作到凌晨 2 点,一周 7 天。「我听说过中国的『996』,我想说,国外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你无法反驳,因为入职之初
(公司)
就已经告知我了。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奥林匹克运动员,必须心怀感激地跑到终点。」

当然,行业中也不完全是这样。得益于诸多工会的成立,有影响的人会团结在一起,批判行业的压榨。但无论如何,求人不如求己。比如另一位亚裔设计师 Yang 表示,他在加入现在供职的大品牌前,一直在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其他一线品牌做设计,以此磨练专业技巧和沟通能力。而在品牌 HR 发出邀约后,他也仔细确认了合同中所提出的条件是否合理,以便日后保障自身权益。
在与 9 位设计师交谈的过程中,总会不时提到「钱」这个字眼。诚然,大多数时装设计师都不具备什么经商头脑。虽然他们背后有品牌这棵「大树」作为依靠,但还是架不住市场部门的兴师问罪和现实生活在经济上的打击。
2023 年,时装撰稿人 Jessica Testa 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关于年轻设计师 Elena Velez 的文章中写道,Velez 的简历具备时尚圈所需的所有硬性条件:她在纽约和巴黎的帕森斯设计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之后又在伦敦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深造,获得研究生学历。毕业后,她创立了同名品牌,为此投资近 45 万美元。然而,她公开的财务状况却写着 9 万美元的赤字。Velez 不是孤例:她是一个以身试险的独立设计师,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大部分受访者的生活中。
「我发现整个时尚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好的家庭背景。比如,经济条件。你可能需要很多次实习 —— 我自己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就经历过三到四轮实习 —— 然后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且,大多数有色人种,尤其是移民,并不具备支持暂无收入的孩子在巴黎生活两年的能力。」身为有色人种的设计师 Nicolas 特意在采访前表示,想对有色人群在时尚圈内的生存状况表达一些看法。「我显然很幸运,获得了 7 项奖学金,所以我能够轻松应付实习生活。如果没有这些,我的职业生涯将截然不同,并且无法抓住任何机会。我希望将来的时尚圈将会有更多有色人群的参与,它需要更多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