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则西去世三年后,国家发布《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细胞治疗正式宣告破冰。
虽然该举措基于患者的呼声——迫切希望接受高质量的体细胞治疗,在支持医疗机构探索创新,让患者尽早接触到更为先进的癌症治疗手段。

但三年前魏则西事件阴影还未消散,而“备案后即可进行细胞治疗临床研究”、“转化应用可收费”等规定也让生物医药行业内尤为担忧:
如果细胞治疗的技术监管规范没有进一步完善,体细胞治疗领域的乱象恐怕并不会消失,魏则西事件也许还会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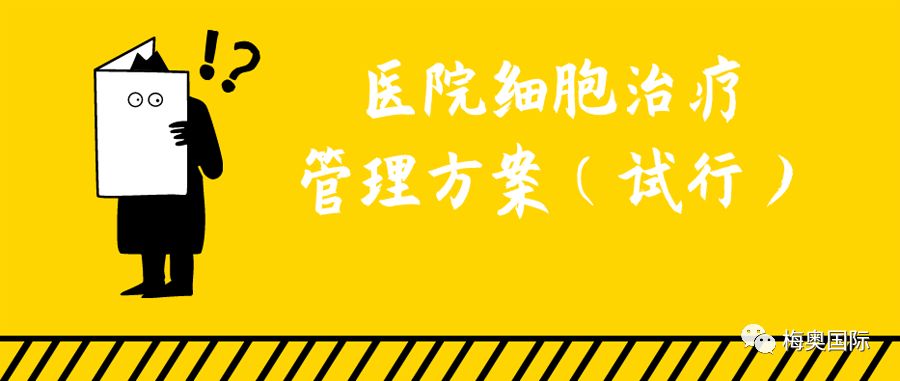
实际上,魏则西事件发生后,监管部门发布禁令,严禁销售未经测试的细胞疗法,尽管允许参与者不支付治疗费用的临床试验仍在继续。
北京世纪坛医院肿瘤中心的肿瘤学家任军表示,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因为在颁布禁令之前,有数百家医院在提供这些疗法,但多数并没有对处理细胞进行充分的培训,或进行充分研究以确保疗法有效,
他们只是打开设备从患者身上采血而已。
不过,此后医院就很难招募临床试验参与者,所以为了鼓励安全开发疗法,有必要制定新的、更明确的规则。
此次,卫健委提出的让细胞治疗转化应用规范化的草案新规与日本的管理模式颇为相近,新规中为可以开展细胞治疗的医疗机构设定了门槛:
只有大约1400家三甲医院,在证明他们具备处理细胞和临床试验的专业知识后,能够申请出售细胞疗法的许可证。
一旦医院获得批准,其审查委员会将监督试验性治疗的临床研究,参与者无需付费。如果委员会确定这些疗法是安全有效的,医院就可以开始出售这种疗法。
没有获得许可证的医院和公司仍然需要向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批准才能进行治疗,且仍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对照临床试验。
这些提议是控制实验治疗质量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北京医院生物治疗中心主任、癌症免疫学家马洁也表示:“这项规定将促进细胞治疗的创新和产业化,最终将使患者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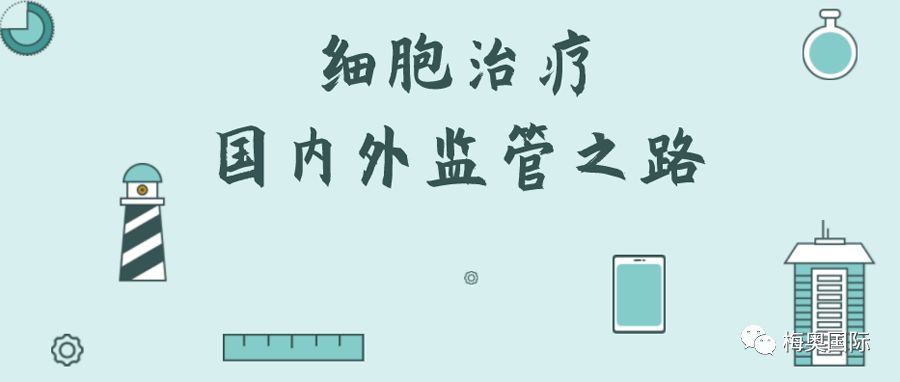
5月2日,国际期刊Nature杂志也加入了质疑阵营,发表的文章中引述了中外专家的评价,他们对新规之下细胞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表示忧虑。
细胞治疗目前在全球炙手可热,
不同国家对细胞治疗产品和临床应用的监管方式各有不同,但总体分为两条途径,一是作为产品,由药品监管部门进行临床准入监管审批,另一种方式则将细其作为一种医疗技术,由卫生部门进行监管,医院可直接进行临床应用。
在美国,细胞治疗产品就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进行分类管理,低风险类产品无需向FDA申请上市前的评估,但FDA对从事这类产品的机构进行定期检查;高风险类产品(体细胞治疗产品、Car-T产品等)必须按药品监管审批。
日本则采取“双轨制”,细胞治疗既可作为独立于药物、医疗器械的医学产品单独监管,也可以由日本负责医疗卫生的主要部门将其作为医疗技术监管,以确保其安全有效性。但作为医疗技术监管的细胞治疗,有效性均尚未得到证实,仅可在有资质的研究中心里进行研究。
其他亦有国家/地区制定了一些政策,如澳大利亚的特殊批准计划,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如病人身患绝症时,进行未经批准的细胞治疗。但澳大利亚癌症免疫学家Rajiv Khanna说,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而且是免费提供给患者的。
就我国而言,细胞治疗的监管之路是蜿蜒曲折的,2003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曾首次将免疫细胞制品纳入监管范围。但两年后,该局停止接受生物疗法的受理,使细胞疗法的管理成为一个“真空”。
2009年,原卫生部医政司发布《医疗技术临床管理办法》,则提出免疫细胞治疗属于第三类医疗技术,但试验管理方法仍无具体明晰的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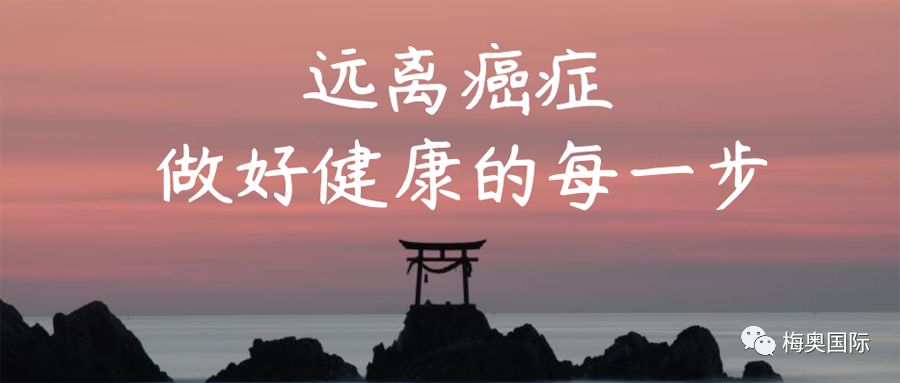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和对细胞治疗的监管,这种疗法一度在全国各地的医院流行。到2016年,许多医院特别是军队医院,会向患者推荐正在进行安全和有效测试的细胞疗法。任军估计,中国大约有100万人为这种手术付费,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癌症免疫治疗市场之一。

尽管由于诺贝尔奖,2018年的癌细胞治疗引起了狂热,但由于副作用,美国几位临床试验患者的死亡很快浇灭了这种热情。
世界各地的医疗监管机构已经放慢了批准免疫疗法的步伐。
虽然数百项细胞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但美国FDA只批准了三种这样的疗法,而中国则一项都没有。
另外,新规之下,医院集众多职权于一身——既是院内细胞制剂的研发人、使用人,又是生产人、销售人和日常监督人。企业研发者担忧,如果医院有了自己的院内制剂,只怕就不会愿意引进企业的体细胞治疗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