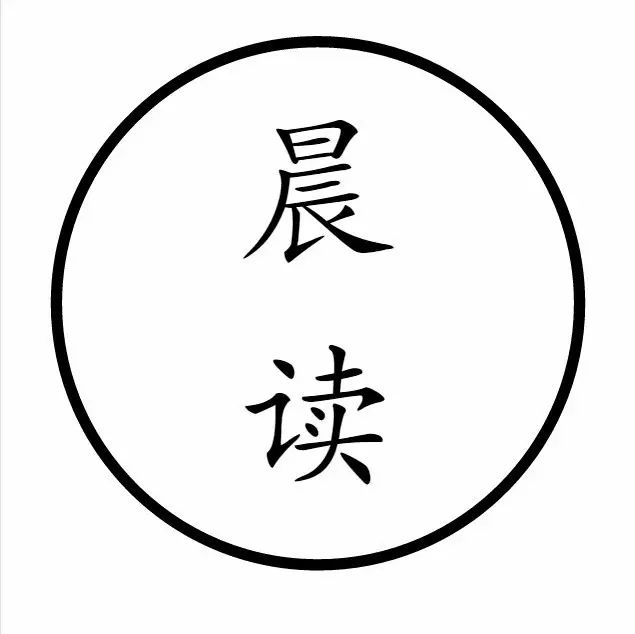本篇专题是我们团队关于低利率环境下大类资产配置系列研究的第五篇,本篇专题中,我们将视角转向居民部门,重点关注海外居民部门如何应对低利率环境、进行大类资产的配置。作为资金的主要供给方,居民的资产配置会直接影响社会资金的流向和相关资产价格。参考海外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判断低利率期间资产价格的波动。
对于非金融资产的配置,由于在美国(
2008
年)和日本,低利率周期均始于房地产泡沫破裂期,居民持有非金融资产的规模和占比总体呈现回落的态势。至低利率周期结束时(日本
2019
年,美国
2015
年),日本居民持有非金融资产的比例降至
37.8%
,美国则降至
30.2%
。与此同时,两地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显著上升。与此相反,在德国,居民持有非金融资产的比例在低利率期间有所增加,保持了以非金融资产为主的资产结构。
对于金融资产的选择,在利率快速下降阶段,海外居民对流动性、安全性高的资产的需求增加,普遍选择增配货币和存款,减少权益和投资基金类金融产品的配置。
而随着利率降至底部并开始长期震荡,居民在资产配置上的选择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美、日、德的居民均会每年配置一部分资产到存款和养老金保险,但日本居民选择配置存款类的比例长期高于另外两地。在美国和德国,随着股票市场企稳上涨,居民还倾向于主动增配权益类资产;而且在证券投资时,居民通常更加偏好配置股票和混合类基金产品。而在日本,即便
2013
年后股市开启长期慢牛,居民也很少主动增加对权益类资产的整体投资,还是更偏好货币和存款。不过,日本居民可以通过购买资管产品间接投资“出海”产品、增厚收益。
风险提示: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因素,国际环境的变化
本篇专题是我们团队关于低利率环境下大类资产配置系列研究的第五篇。
在本篇专题中,我们将视角转向居民部门,重点关注海外居民部门如何应对低利率环境、进行大类资产的配置。作为资金的主要供给方,居民的资产配置会直接影响社会资金的流向和相关资产价格。参考海外居民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判断低利率期间资产价格的波动。
参考之前专题系列的划分,我们仍重点对比日本、美国、欧元区的家庭部门在各自低利率周期中的资产配置变化。关于低利率的时期,我们将日本的低利率周期划定在
1991-2019
年,欧元区(包括德国)划定为
2008-2019
年,美国划定在
1930-1945
年和
2008-2015
年。
而且根据利率的下行速度和经济基本面的不同,这些经济体的低利率时期又可以进一步划分。我们将分为利率快速下降期和利率低位震荡期两个阶段,对居民的资产配置偏好变化进行对比分析。
在美国
2008-2015
年的低利率阶段中,可以将
2008
年全年划分为利率快速下行期,将
2009-2015
年划分为利率低位震荡期。
随着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风险不断发酵,美联储从
2007
年
9
月开始连续降息。到
2008
年底,短端利率由
2007
年
9
月的
5%
下行至
0%
附近,
10
年期美债利率也回落近
250BP
至
2.1%
附近。
2009
年
-2010
年,美国经济开始回暖,但复苏之路依然比较坎坷。美联储在
2010
年
10
月和
2012
年
9
月分别推出了第二轮和第三轮
QE
,带动长短端利率持续低位振荡调整。而后一直到
2015
年
12
月美联储加息,短端利率才开始逐步上行。

在日本
1991-2019
年的低利率阶段中,可以将
1991-1995
年划分为利率快速下行期,将
1996-2019
年划分为利率低位震荡期。
90
年代初,日本股市和地产市场泡沫先后破裂。为摆脱危机,日本央行转向宽松货币政策,从
1991
年
7
月到
1995
年
9
月连续
9
次下调政策利率,将贴现率从
6.0%
降至
0.5%
,
10
年期国债利率也从
6.7%
降至
2.9%
。
1995
年之后,贴现率就长期维持在零附近,
10
年期国债利率也维持在
2%
以下,整体利率环境进入低位震荡期。

欧元区
2008-2019
年的低利率阶段同样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2008-2009
年为利率快速下行期,
2010-2019
年为利率低位震荡期。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对欧元区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受此影响,从
2008
年
10
月到
2009
年
5
月,欧央行连续
7
次下调基准利率共
325bp
,从
4.25%
降至
1.0%
,短端的
1
年期利率也由
3.7%
降至
1%
。
2010-2019
年期间,在危机接连冲击后,欧元区整体经济增长乏力、通缩风险抬升,欧央行也重启了降息周期,并于
2014
年
6
月正式进入“负利率”时代,进一步压制利率表现。

美国
1929-1945
年低利率阶段中,
可以将
1929-1933
年
划分为
利率快速下行期,
将
1934-1945
年
划分为
利率低位震荡期。
1929
年美国加息刺破资产泡沫,股市大幅下跌,经济也步入衰退,为挽救经济和资产危机,美联储从
1930
年开始连续降低贴现率,短期国库券利率从
1929
年的
5.1%
快速下行至
1933
年的
0.5%
以下。此后低利率一直维持到
1947
年。

非金融资产:居民配置有何变化?
固定资产是居民资产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首先关注低利率期间,居民如何调整固定资产方面的配置,以及在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之间的选择。
2008
年低利率期间,美国居民持有的资产总量短期回落,而后持续创新高。
在利率快速下行期,美国家庭部门的总资产规模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而随着第二阶段,也就是利率低位震荡期的开始,总资产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
从结构看,这一回升主要受金融资产增长的推动,而
居民持有非金融资产规模的回落一直持续到
2012
年。
其中,房地产资产在非金融资产变化中起主导作用。具体来看,家庭持有房地产资产的占比从
2007
年开始明显下降,到
2012
年时降至
24%
,压缩了
6.5
个百分点,此后基本维持在
25%
附近波动。
与此相对应,金融资产的占比则呈现长期上升趋势,从
2007
年的
63.8%
提升至低利率周期结束时的约
70%
。
考虑到资产价格重估本身就会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结构造成一定影响,而这并不代表居民主动的配置选择,因此我们还需要结合家庭部门资金流量表,来分析居民的资产配置偏好。
根据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美国居民在
2008
年到
2011
年间主动购买住宅的金额相比前期明显收缩,而配置耐用消费品的情况则比较稳定。从
2012
年开始,居民资金流入住宅市场的规模又逐步回升,但到
2015
年低利率周期结束当年,主动配置的资金量仍没有恢复到
2007
年危机前的水平。
不过,居民选择配置金融资产的规模在危机后收缩更加显著,
2009
年主动投资额不到
2007
年的一半。
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资产规模变化也较类似:
利率快速下行期,居民持有总资产规模下降;而随着第二阶段的开始,总资产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不同点在于,在
1929
年
-1939
年期间,居民持有非金融资产,尤其是居住建筑物的比重有所增长,金融资产比例反而从
64.8%
小幅降至
62.7%
。
在日本,受非金融资产规模持续缩水的影响,居民资产总量长期上行动力偏弱。
根据日本家庭资产负债表,
1991
年进入低利率周期后,居民总资产规模就结束了
80
年代的增长趋势,从那时到
2012
年前,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
在内部结构上,金融资产逐渐“取代”非金融资产成为主导。
非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土地和住宅建筑的存量规模在
1990
年见顶,此后
20
多年直到
2012
年都呈现持续下行的趋势,到
2012
年非金融资产规模仅有
1990
年高点时的约
57%
。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的低利率阶段始于
1990
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时期,土地价格快速回落,导致居民持有的非金融资产,尤其是土地资产价值长期收缩。在日本居民持有的非金融资产中,土地资产占比最高,其价值变化起决定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期间包括住宅在内的固定资产规模在
1990
年至
1997
年间实际上还在继续增长,这为整体非金融资产规模提供了一定支撑。
相比之下,在整个低利率期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规模总体呈现缓慢上行的态势。到
2019
年低利率期末,金融资产规模已增至
1990
年的
1.8
倍左右。从资产占比来看,金融资产在居民资产中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35.4%
上升至
2019
年的
62.2%
,而非金融资产的比重则降至
37.8%
。这表明,日本居民的资产结构已经从以非金融资产为主转变为以金融资产为主。
再根据日本家庭的资金流量表,
1990
年以前,日本居民对非金融资产的配置调整表现为积极出售土地,特别是在
1985
至
1990
年间,日本地价的快速上涨引发了居民的大规模“卖地潮”。然后在房地产危机发生后,整个低利率期间居民卖地的倾向反而明显下降。这可能和其他部门购置土地需求大幅下行有关。
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
1990
至
1997
年间,日本居民并未减少对固定资产,主要就是住宅及其他建筑的投资。一直到
1998
年日本金融危机爆发,居民的住宅建筑投资才开始呈现逐步回落的趋势。
类似的结论也可以从日本的住宅新开工数据中得到证实:新开工数量在
1991
年经历了一次阶段性下降,但到
1993
年已回升至每年约
150
万套的高位水平。而后到
1998
年后,新开工数量才出现持续下降,标志着新开工中枢的明显降低。


相比之下,在欧元区,以德国为例,家庭总资产在低利率周期中整体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在第一阶段,即利率快速下行期间,由于股票市场短期调整,居民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和总资产规模均出现小幅下降。从占比来看,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从
2007
年的
40.9%
回落到
2009
年底的
39.6%
。而自
2010
年进入利率低位震荡期以来,金融资产占比转为缓慢小幅的扩张,非金融资产占比则有所下降。
然而,整体上看,居民持有非金融资产的比重相比危机前仍有所上升,这与美国和日本的情况都有不同。而且到低利率期末,居民持有的非金融资产依然超过金融资产。

接下来,我们对金融资产类别进行细分:各地居民如何在不同的金融资产间进行配置选择?在低利率周期的不同阶段,他们的配置偏好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利率快速下行阶段,居民部门持有的货币存款占比往往会快速提升,股票基金占比则通常回落。
例如,随着日本央行快速降息,从
1990
年到
1995
年日本居民持有的存款资产占比从
48.6%
持续上行至
51.2%
;股票和投资基金占比从
20.3%
降至
13.8%
。
2007
年
9
月到
2008
年末,美国居民部门持有的现金存款份额从
10.9%
升至
13.9%
;股票和基金则从
43.7%
降至
33.4%
。但在快速降息阶段过去后,多数地区无风险资产的占比就趋于回落或基本走平。
一方面,危机发生后,居民对高流动性、低风险资产的需求确实会显著增加。而更重要的因素或在于低利率初期,这些经济体普遍都经历了股票市场的较快下跌;股价回落本身就会引起权益类资产规模的收缩、其他资产的比重被动提升。


第一阶段,各地居民配置保险和养老金产品的比重也会上升。
不过区别于存款类资产,我们发现,保险类资产能够在更长时间内持续吸收居民的资金:日德、欧元区整体、以及
30
年代的美国居民都倾向于在整个低利率期,持续增加保险养老金资产的配置。

再参考居民资金流量的使用情况,
海外居民确实会在低利率初期,尤其是第一年时,显著增加对货币和存款资产的配置,同时卖出股票和共同基金资产。
另外,危机期间,居民主动配置债券等安全资产的动力也会明显增强,尤其在
2008
年美国居民投资金融资产时直接流入债券类的比例一度高达
74%
。



在利率低位震荡期,居民在金融资产配置上同样有一些相似的趋势。
比如,根据资金流量表,美日德的居民都会每年配置一部分可支配资金到货币和存款,且比例通常不低于危机前水平(图
19
)。对于债券资产,由于利率整体低位震荡,三地居民多数时候都选择减少债券资产的配置,表现为资金的持续净流出(图
21
)。
但在这一阶段,分化也逐渐显现。
比如,资金流量表显示,日本居民配置存款的比例长期高于另外两国,而且进入利率震荡期后,该比例还在不断上升;美国居民配置存款比例则在三者中相对较低,保持在危机前水平附近。
在股票和基金配置上,差异更加明显。美国居民在利率震荡期的配置积极性较之前有所提高,特别是在
2012-2015
年。相比之下,日本家庭在这一阶段很多时候选择赎回股票基金,转而配置其他资产。而德国家庭的风险偏好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资金流向货币存款和股票基金的比例皆处于两者之间。
因此,接下来我们需要分经济体进行分析,重点关注三地居民在较长的利率低位震荡期间各有什么特点?
两轮低利率周期的家庭资产负债表均显示,进入第二阶段后,美国居民持有股票和共同基金的比例就开始拐头回升。
差异点在于,
2008
年这一轮中,居民配置的股票基金比例从
2009
年的
31.5%
较快提升到
2015
年低利率周期结束时的
42%
,增长了超过
10
个百分点。股票和共同基金也成为此后美国居民金融资产中占比最高的大类。当然,居民持有股票基金比例的拐头向上,与
2009
年后美国股市的企稳是基本同步的。同期,现金和存款的配置比例则从
14.2%
降至
12.6%
,寿险和养老金的比例整体保持稳定。
而在
1933
年后,尽管居民的股票类资产配置也出现了企稳回升的趋势,但在利率低位震荡期间,持有比例始终未能恢复到
1929
年的高位。期间,持续增加的则是现金存款和保险养老金资产。到
1945
年,现金存款的比重已经升至与股票差不多的水平,都在
25%
左右。

从家庭部门资金流量表来看,
09
年以后,居民在股票和投资基金方面持续净投入资金,
尤其是在
2012
年到
2015
年间,累计净投入约
1.8
万亿美元(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占同期金融资产总投入的
34%
。而在
2008
年以前,居民资金经常是从股票和投资基金净流出的。因此可以看出,零利率时期,美国居民对股票和基金的投资意愿有所增强。
不过,尽管对股票和基金的偏好有所增加,从绝对量上来说,在此期间美国居民主动配置比例最高的仍是保险、养老金和存款。
对比几类资产,
2009
年到
2015
年间,累计流向保险和养老金的资金占比最高,约有
43%
;其次是货币和存款,占
32%
;均高于股票和基金类(
23%
)。这意味着,居民资产负债表中股票和基金资产占比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股价上涨带来的资产价值重估效应。

在选择投资产品时,美国家庭更偏好共同基金,而不是直接买股票。
对比主要投资产品,
2009
年以后,共同基金是居民资金最主要的流入项,占投资类产品总增量的
84%
,远高于直接流入股票的比例
22%
(
2009-2015
年)。
同时,受到零利率环境及股票市场逐步走强的影响,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每况愈下”:
2009
年到
2015
年期间,居民整体上选择赎回货币基金产品,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货币市场基金
Primary Reserve Fund
“破净”,引发了大规模的资金赎回。

如果进一步细分基金种类,到
2015
年时,美国居民持有的投资基金中,
54%
是股票类基金,比
2009
年增加了
9.7
个百分点。债券基金的持有规模也持续上行,到
2015
年底时约占到
23%
。相比之下,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则持续缓慢收缩。

在保险和养老金的选择上,美国居民显著偏好养老金产品,以间接分享市场的增长。
在保险和养老金产品中,超过
90%
的资金都被用于配置养老金权益,比例很高。对比其他两个国家,在
2015
年,美国居民持有的养老金占到整体金融资产的
28.6%
,明显高于德国和日本;而寿险和年金类产品的比例则相对较低。
在美国,相比于保险机构,养老金配置股票和共同基金的比例比较高。因此美国居民对养老基金的青睐,也反映了他们整体较高的风险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