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丽,话剧演员。
我希望能够一直在这个舞台上演戏,演死在这个舞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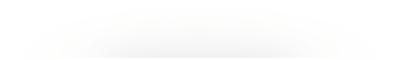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黄湘丽。
在进入孟京辉戏剧工作室的九年多时间里,我演出了各种各样的戏,话剧、肢体剧、音乐剧。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这三年我一直在做的一件最来劲的事情——独角戏。
2013年夏天,孟京辉导演把我拉到了一个角落。他跟我说,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你们组的其他三个成员家里有事要去处理,我知道你没有事,但是你不能闲着,要不你就开始自己排戏吧。
我跟导演说:“导演,我一个人怎么排戏呢?”导演说你应该尝试着一个人进行创作。我说我没有剧本。导演想了想,说:“要不你先试一下奥地利德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这样我就得到了一个剧本,开始了排练。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演过独角戏,我也不知道一个独角戏该怎么进行创作。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汇报表演都失败了。
导演说,这样不行,你得另外找一种方式进入剧本,要不然你写歌吧,作为一个优秀的话剧演员,你应该什么都会,包括写歌。
在导演的各种威逼利诱之下,我就开始尝试一个人写歌。有一个下午,我抱着吉他,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根本没有任何眉目。但是过了那三个小时之后,突然之间好像一扇门被打开了,我就迅速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
当我带着这首歌找到导演给他弹唱的时候,我觉得导演心里其实还是很欢喜的,但是他故意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说,接下来的五天我要出去玩,你必须在这五天里一天写一首歌出来。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就真的一天写出来了一首歌。导演听完了这些歌,他安静了一会儿,说:“我觉得现在你才进入了这个‘陌生女人’,我们可以开始排练了。”他觉得当我抱着吉他在那弹唱自己创作的歌曲的时候,就像剧里面的陌生女人怀里抱着她唯一的希望。
所以我们第一个独角戏是从音乐入手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除了音乐之外,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舞台上,大家会发现有一个独特的设置:舞台的左侧有一个厨房。
读过小说的人可能知道,原著里并没有厨房。有一场戏是陌生女人跟W先生共度一夜之后,第二天早上他们共进早餐。排到这一段的时候,导演说,我们应该真的在排练厅做一顿早餐。然后工作人员迅速地买来了各种各样的食材,锅碗瓢盆还有炉子。我就真的开始在排练厅里面煎牛排、烤面包、煎鸡蛋。
也就是说,最后在呈现的时候,观众坐在剧场里面看戏,除了有视觉和听觉的震撼之外,还会有嗅觉的感观。大家会闻到黄瓜的味道、柠檬的味道,还有红酒和牛排混合在一起非常强烈的气味。也有观众看完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之后在网上写:这个戏一定不能空着肚子去,因为实在是太香了。
2013年10月10号,首演的当天,我非常紧张,非常不安。以前,在开演之前,我们十来个演员会在一起喊加油,但那一天的首演,化妆间只有我和化妆师,我们默默地进行最后的化妆。
开演前的一分钟,导演走进化妆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哎,丽丽,剧场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我更紧张了,但是没有办法,我得一个人独自走上舞台去面对观众。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幸运,当我在舞台上第一眼看到所有观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我有一个更强烈的欲望,只有这一个更强烈的欲望,就是一定要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好好地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除此之外,我没有想别的。

首演结束后那一天,我们都特别高兴,因为那一天我超常发挥。在首演的当天下午,其实我们还在一直不断地改戏,我也在一直不断地错词。但是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一个字也没错。
到现在为止,《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已经演出了超过400场。我觉得这三年多的时间,每一天我都在饰演这个陌生女人。这个陌生女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每一天都在生长,她变得越来越饱满,越来越敏感,越来越丰富。
就像最开始有一段戏我是坐在床上,那段戏大概有六七分钟的时间。那一大段独白讲的是,“陌生女人”在有了W先生的孩子之后,觉得自己对W先生的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之后她又碰到过W先生很多次,可是W先生并没有认出她。
之前我觉得七分钟的时间太长了,我也找不到一种欲望去说这段词,所以那一段的呈现一直都不是很满意。在第二轮演出的时候,导演说我们得把这一段再重排一下。他说你得尝试用一种你之前从来没用过的方式去饰演这一段戏。
后来我们就找到了一种表面上看起来不在乎无所谓,但是内心深处却有着强大欲望这样一种感受去说这段台词。经过每一天慢慢地揣摩、练习,这一段越来越好。
到现在为止,这一段戏已经成了整场戏里面我最爱演的。每当演到这段戏的时候,我都觉得太自由了,每一句话我都爱说。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内心的变化,可能比那些显而易见的变化要更重要。

两年之后,有一天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我说我最近在读萨冈的《凌乱的床》和《你喜欢勃拉姆斯吗》。导演说那你读过她的《你好,忧愁》吗?我说我读过。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读的。后来导演让我在电话里把这个故事又重新给他说了一遍。他说这个故事可以作为我们第二个独角戏的剧本。
戏剧构作就去法国大使馆沟通版权事宜。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要排《你好,忧愁》的时候,非常吃惊。我们就想,为什么他这么惊讶,回来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小说还从来没被排成话剧呈现在舞台上。后来我们在进入排练之后,也知道了为什么没有人把它排成话剧,因为实在是太难了。
读过这个小说的都知道,书里面很多都是心理活动的描写,并没有很多戏剧冲突,戏剧导演一般是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剧本的。但是后来我们想,选择了这样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剧本,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看到别人没有看到过的风景,所以值得冒险。
然后我们就开始排练。第一次汇报的时候,导演中途就睡着了。看完了汇报之后他什么也没说,就打了个电话给票房。他说票房,《你好,忧愁》开票了吗?票房说我们开了,卖得非常好。导演挂了电话之后,看着我们,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即使我们想再换一个戏也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坚持下去。”

这样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星期。非常灰暗,不知所措。终于有一天,我演了大概一分钟我的一个想法给导演看。演完之后,导演说哎呀,我刚才有点恍惚,跑神了。你能再跟我说一遍你刚才干吗了吗?
我说导演,刚才是这样的,我就从这儿走到了那个沙发那儿,然后我拿起一杯水喝了,喝完之后我甩了甩头发,啪啪啪说了一段台词,然后我又回来了。
导演说,停,你把你刚才说的这些,一字不差地再跟我说一遍。我说,行。然后我就原封不动地把刚才说的这一段又说了一遍。导演说:“好了,我们找到方法了。”——用这一种把所有的行动都描述出来的方式。
开始用这种方式往下排的时候,好像局面一下就打开了,非常地顺利,最后《你好,忧愁》在舞台上的呈现也是。我们用了很多夸张的形体,加上很多声音装置,以及一种克制的表达方式。舞台有二十个独立的空间,加上蒙德里安的灯光概念,所以这是一出有着非常独特气质的独角戏。


《你好,忧愁》里面有一场戏,是一段五分钟的独白,是全剧的一个高潮。我通常会选择看一个观众,把那五分钟非常具有爆发力的台词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的眼睛全部说完。
我看见有的观众,他的头从中间移到了左边,然后又从左边移到右边,或者直接就低下了头。他在躲闪,他不太敢迎接我的目光。当然了,我也碰到有一些观众非常勇敢,他就跟我对视。
说这段台词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今天的观众太棒了,一动不动。在我说完所有台词之后,我发现他的内心就——唉,轻舒一口气。所以其实在剧场这个空间里面,会发生特别多好玩的奇妙的事情。
4月,在北京刚结束了我的第三个独角戏《九又二分之一爱情》的演出。这部戏一共演出了16场。在这16场里面,如果有观众买了两次票或者是三次票去看,每一场都不一样。
《你好,忧愁》到现在为止也演出了100多场了,加上之前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400多场,基本上,我是全年无休的。有观众就会说,你总会生病吧?你发烧了、感冒了、拉肚子了怎么办?会有别人来顶替你吗?我说,没有。如果生病了,我依然要站在舞台上。而且我还不能让观众看出来我生病了,我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最好的高度来呈现给观众。
我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昆明演出。我食物中毒,上吐下泻,当时连拉开窗帘的力气都没有。可是那天晚上我还要进行演出。
完成了那天的演出之后,我自己觉得,哎,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了,我必须要非常好地爱护自己的身体。因为我的身体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的,也属于观众和剧场的。

在我进入孟京辉工作室的第一年,有一天,是下午五点钟,我走进剧场去准备当天的演出。那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下午,当我从漆黑的剧场往化妆间走的时候,我只看到从化妆间投出来的一束光。
我看着那束温暖的黄光,突然一下子心里特别地幸福。我一下子意识到我是属于舞台的,我热爱这个舞台,我希望能够一直在这个舞台上演戏,演死在这个舞台上。
最后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保尔·艾吕雅的诗:《直接的生活》。这首诗也是跟我们的独角戏《你好,忧愁》有关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别了,忧愁
你好,忧愁
你镌刻在天花板的缝隙
你镌刻在我爱人的眼底
你并不是那悲苦
因为最贫穷的人也会微开笑靥
将你吐露
你好忧愁
温馨玉体的爱
爱的威力
你那喷涌而出的温馨
犹如没有躯体的妖魔
沮丧的面孔
忧愁妩媚的容颜。
谢谢大家。

陈珊妮 待办事项 |画壁画的嘚瑟型艺术家文那 | 李津 | 中国美色 | Tango | 田沁鑫 | 熊亮 | 林糊糊 | 徐昂 喜剧的忧伤 | 平如美棠 | 冯健男 九色鹿 | 青山周平 | 疯狂地爱上化学 | 五条人 | 摩拜单车 | 无人机的空中三百米 | 看不见的垃圾处理厂 | 虚拟现实元年 |
热门演讲,请点击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