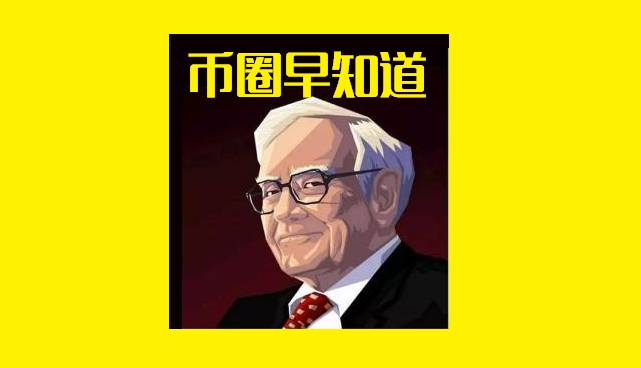正文
马塞尔·杜尚大概不愿承认自己是艺术家。
即便在很多人眼中,他几乎改写了上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从小便池的《泉》到多了两撇胡子的蒙娜丽莎《L.H.O.O.Q》,杜尚似乎一直在扮演着一个颠覆者的角色。不仅仅在艺术内部挑战绘画的固有权威,更直指艺术和美本身,不断突破并拓宽人们对艺术认知的边界。
“我的艺术就是某种生活,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当其他人打着艺术的名义,重建权威,禁锢心灵时,杜尚很自然地同他们保持了距离。很难讲,当时年纪轻轻的他是不是真的有自主的意识主动告别一切捆绑,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坚定地顺从了自己的心意。在杜尚那里,似乎没有一个叫杂念的东西,他不会摇摆,也没有迟疑。一旦对他在意的自由稍有侵犯,他就立马放下一切,维护自我的完整与独立。
马塞尔·杜尚(1887年7月28日-1968年10月2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提倡“反艺术”,对后来的行为艺术、波普艺术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作有《下楼的裸女》《泉》《大玻璃》等。
无论是杜尚被强行归入的达达主义,还是受其影响启迪的波普艺术,抑或之前艺术史上所有的手法流派,其实都还被圈定在艺术的框架里讨论问题。可在杜尚看来,如果艺术意味着不自由,意味着持守旧的边界,圈定新的权威,那么一定需要有人出来打碎这种艺术的幻觉。他拿现成品,拿蒙娜丽莎的胡子,拿反审美的机器,都想冲破这层迷障和捆绑。在他心里,真正值得追寻的只有自由,完全的自由。
这大概是杜尚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在乎的是自由,是态度,是观念,即便为此也承受争议。他毕竟不是百年难遇的天才,也不是振臂高呼的英雄。他更像是一个安静站在圈外,看到艺术谎言一旦形成泡沫就想去悄悄戳破的内敛男孩。为了不让自己沾惹上无谓的麻烦,他随和;为了不让任何人侵犯他坚守的自由,他冷漠。然而他仍然用一生时光给出了他人生最好的作品,“我的艺术就是生活”。
撰文 | 李佳钰
被拒绝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对马塞尔·杜尚是如此。
1912年,他的油画《下楼的裸女》被巴黎一个立体主义画展拒绝,让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与其他艺术家的分别,并因此开始独自探索并拓宽艺术的边界。1917年,他用一个白晃晃的瓷质小便池再次挑战艺术的底线,仍被拒绝。但这一次,他却让整个现代西方艺术的进程因为这个被命名为《泉》的小便池而改写。
杜尚的敏锐和超前,让他把他所处的时代远远地落在了后面。甚至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很难说自己离他的距离更近了一点。这种疏离并不完全来自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颠覆和激进——毕竟经过一个世纪的感知和铺陈,人们已经能够逐渐接受装置艺术以及现成品作为现代艺术的表现——而更深层次的,大概源于杜尚一直以来所坚守的自由。他要的是完全的自由,任何人和事都无法僭越的自由。对杜尚来说,“没有什么是要紧的”,艺术、工作、生活、家庭都不紧要,唯有自由。为了抵达这种自由,他节制了情感,放弃了欲念,躲避了责任,也拒绝一切让他感到捆绑的力量。
其实杜尚才是那个不断拒绝的人,他拒绝传统,拒绝艺术,甚至拒绝惯常的生活。而他所做的一切抵抗却又都是不动声色的。他默默地守在角落,注视着,质疑着,哂笑着,用他的态度和观念挑战并击碎既有的定见。他的温和、安静与他的冷漠、坚定一同守护着他,让他一生的时光成为他最后最好的作品。
拒绝美
摆脱传统的桎梏
杜尚1887年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布兰维尔镇,是殷实富足人家的孩子。外祖父生前醉心版画,让杜尚家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受到影响,一心想当艺术家。大哥本被父亲送去巴黎学法律,结果自己逃课转行画插画。二哥也在雕塑上极具才华,不久便紧随其后,弃医从艺。杜尚17岁时就离开家乡,去巴黎投奔两位兄长。他说那时自己显然还对“制造优美艺术的人抱着无知的热情”。更何况“艺术工作者”的身份还能让他缩短服兵役时间,由两年变成一年,这对生性爱自由的杜尚来说,是足够充分的理由让他得以延续这份热情。
所以杜尚也曾为此精进绘画,虽然几年过后就打定主意与之决裂。节点就是油画《下楼的裸女》,1912年,巴黎一个立体主义独立沙龙展曾拒绝展出这幅画,理由是办展的立体主义者们担心画中的运动感会引来未来派们的嘲笑,所以希望杜尚把画中的动感去掉,把立体主义的部分再加强。杜尚很是惊诧当时艺术团体的自我设限竟然狭隘到如此地步,“那时立体主义不过才流行了两三年,他们已经有了清楚明确的界限了,已经可以预计该做什么了,这是一种多么天真的愚蠢。”
晚年的访谈中,杜尚坦言这是一个意外的“契机”,“帮助他完全从过去解放出来”。在他看来,只因派别之争、名声之累,就让艺术受制于权威和传统,实在荒谬至极。更何况,这些自诩自由的艺术家们也曾为倡导革新奔走呼求,可为何他们刚刚冲破他者建造的樊笼,却又如此迅速地跌落自我设限的窠臼。
杜尚说他要的东西并不多,“棋,一杯咖啡,过好24小时”。
杜尚不明白,却也暗地下定决心。他一言不发坐上出租车,把画从沙龙拿回来,并告诉自己,“行啊,既然事情像这种样子,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去加入团体了——以后除了我自己不会再去依赖任何人。”如果说之前杜尚对传统的反叛还是无意识的,那么《下楼的裸女》被拒之后,杜尚知道,他要彻底告别这种生活,“从1912年起我就已经决定不再做一个职业意义上的画家了”。成名的欲念,好胜的冲突……这些艺术家们的诉求杜尚都不曾有。他很清楚自己得“离开这种环境”,宁愿去当一个图书管理员,或是法文老师,只要能自食其力就好。
现成品
开拓艺术的边界
所以他之后当真放弃画架和画笔,并在巴黎当上了图书管理员。战争爆发之后,他又去了纽约,靠教法文为生。杜尚不愿背负有重量的生活,他想要摆脱的不只是艺术,还有令人受限的一切桎梏。“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想做一些与过去全然不相干的探索,《大玻璃》就是其中之一。从1915年到1923年,杜尚在《大玻璃》上足足花了八年时间,通过类似机器的描绘方式,用线条和技术在透明的玻璃上呈现他想要的表达。
除此以外,他还发掘到了“现成品”这个摆脱艺术的重要手段。1917年的纽约,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独立艺术家展”,杜尚临时起意,匿名交了5美元的年费和1美元的场地费,便将他刚买的小便池送去参展。除了在底部的边缘签上假名“R.Mutt”外,这个被命名为《泉》的作品再也没有其他加工。这件作品被组委会投票否决参展并不意外,即便杜尚本人也是组委会成员之一。他虽然之后通过退出组委会以示不满,但仍然没有向外界透露马特先生的真实身份。
他倒是随后在一本艺术杂志《盲人》中匿名发表短文,表示对《泉》的支持,“马特先生是否亲手做成了这件东西并不重要,他选择了它。他把它从日常的实用功能中取出来,给了它新的名称和新的角度——给这个东西灌注了新的思想。”这段话其实也充分表达了杜尚对于艺术的理解。在杜尚看来,艺术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至多充当一个中介,在其中赋予自己的态度和观念。他在1957年一次“创造行为”的演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知道这个说法不会让很多艺术家赞同,他们会拒绝中介的说法,而坚持认为他们在创作行为中的见识所具有的效果——然而,艺术史则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肯定什么是杰作,而它的考虑完全不必顾忌艺术家本人的解释说明。”
杜尚的现成物品艺术作品《自行车轮》——一个自行车的轮胎被倒置于一把高凳上。
杜尚倒是提前预见了自己的杰作。只不过他对现成品的发掘并不是让人慢慢去发现它的美,恰恰相反,他想让人们对艺术,对美放下无谓的迷思。“事实上现成品被当做艺术品那样受到尊重,意味着我打算把它彻底带离艺术的企图没有成功。”他之所以把如此不雅的俗物置入所谓艺术的圣殿,就是想挑战陈旧的定见。囿于美其实也是一种受限。杜尚时刻提醒自己和人们,要对那些不容置疑的观念问问为什么。为什么仅仅取悦眼睛,而忘记关乎心灵?为什么艺术不应该追求心灵最终得到真正自由,而仅仅停留在受到视觉的撼动和冲击?杜尚用一个小便池为现代艺术炸开了个大窟窿,让我们得以窥见其中更为广阔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