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罗德·品特(
Harold Pinter 1930-2008
)
,英国剧作家,马丁
·艾思林在《荒诞派戏剧》中设专章讨论的一系列当代重要剧作家之一,二〇〇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品特创作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曾制造出令当时大量观众和剧评家困惑、愤怒,而又无以置喙的效果。
片段式、独白化,还有“品特式的”人物,很像作者为剧本积累的素材。
哈罗德·品特作 程巍译
我的眼神儿更糟了。
我的医生身高六英尺差一英寸。他的头发里有一缕灰发,一缕,就一缕。他左颊上有一块褐斑。他的两个灯罩呈卷筒状,深蓝色,底部都饰有金边。两个灯罩一模一样。他的印度产的地毯上有一处焦黑的烧痕。他的助手一看见女人,就戴上眼镜。透过窗帘,我听见他花园里鸟雀的鸣啭。有时他的妻子露露面,一身白。
关于我的视力,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话。据他看,我的视力正常,兴许正常得过分了。他看不出任何迹象,证明我的视力正在变糟。

我的眼神儿更糟了。并非我看不见。我确实看得见。
我工作顺利。我的家人与我相处融洽。我的两个儿子与我最贴心。我与妻子也还亲密。对全家老小,我都亲密无间,包括我的父母。我们常坐在一起听巴赫。去苏格兰时,我常带全家同行。我的小舅子有一次也随同前往,在旅途中帮了不少忙。
我有些业余爱好,其中之一是拿着锤子往木头里钉钉子,或用螺丝刀往木头里拧螺钉,或用各种各样的锯子锯木头,做一些什物,或变旧物为新用,或把那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东西派上用场。不过,当你的眼前出现重影,或你压根儿没看见,或有东西挡住你的视线时,要干这些活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的妻子很满足。我在床上施展我的想象力。我们做爱时亮着灯。我贴近看她,她也看我。早上她的双眼发光。我透过她的眼镜片看见它们在发光。
整个冬季天空都很晴朗。雨在夜里下。一到早晨,天就放晴了。反手击球是我的拿手好戏。隔着冷杉木制的球桌,我面向我的小舅子站定,轻握球拍,腕关节往里弯着,等着把球吊到他的正手,等着看他(满脸惊愕)急匆匆地接球,丢球,跌跌撞撞,甚是恼火。我的正手球欠些火候,不大得心应手。不出所料,他攻我的正手。房间里回荡着清脆的声响,球打在橡胶拍上的声音在四壁回响。不出所料,他攻我的正手。但又一次打得太偏右了,离我的正手还有一大截,而我的身体重心恰好偏在那边,正好可以施展我的反手抽球,使他招架不住,看着他跌跌撞撞,连溜带滑,还是丢了球。比分回回都差不多。不过,如今,当你看到乒乓球变成两个,或压根儿没看见乒乓球,或当球飞快旋转过来挡住你的视线时,玩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对我的秘书很满意。她挺有生意头脑,而且对生意感兴趣。她值得信任。她代表我给纽卡斯尔和伯明翰打电话,从没受过欺诈。客户们在电话里对她很是敬重。她的嗓音有说服力。我的合伙人和我都承认她是我们的无价之宝。当我们两口子和我的合伙人三个人约在一起喝咖啡或喝茶时,我的合伙人和我妻子经常谈到温蒂。他们一谈起她,两人都没有什么好话。
老是大晴天,在这样的日子,我拉上办公室的窗帘,好进行口述。我经常摸一摸她丰满的身体。她复述一遍,把纸张翻过来。她给伯明翰打电话。在她通话时(一只手轻轻握着听筒,另一只手平稳地做着记录),即便我抚摸着她丰满的身体,她也会一直把话说完。我眼睛上的绷带正是她给缠的,在她缠绷带时,我抚摸着她丰满的身体。
我不记得我小时候有哪点儿像我那两个儿子。他们异常矜持。他们似乎不受情欲的搅扰。他们安安静静坐着。两人时不时咕哝几句。我听不见你们,你们在说什么呢,大点声,我朝他们喊。我妻子也这么喊。我听不见你们,你们在说什么呢,大点声。他们年龄一般大。看起来,他们学业不错。但在乒乓球上,两人都是庸才。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已懵懂大开,充满情欲,善于辞令,生性敏感,而且眼神很好。他俩压根儿不随我。他们的目光在镜片后面显得呆滞,难以捉摸。
我的小舅子在我的婚礼上是男傧相。那时,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在国内。与我最要好的那位朋友按说是男傧相的自然人选,可他突然因生意上的事被叫走。他因此当不成男傧相了,感到十分惋惜。他早已为新郎准备了一篇辞藻华丽的赞美词,打算在婚宴上朗诵。我的小舅子当然不能拿着这篇演说辞照本宣科,因为它里面提到我和阿特金斯之间长久的友谊,而我的小舅子对我一无所知。他于是遇到了难题。他解决难题的方式,是在致辞中大谈他的姐姐。我至今保存着他给我的礼物,一个从巴厘岛买的雕花铅笔刀。
我对温蒂进行初次面试的那一天,她穿着一条绷得很紧的花呢裙。她的左腿不停地蹭着右腿,右腿不停地蹭着左腿。这些小动作都被裙子挡着。在我看来,她正是当秘书的料。她瞪大眼睛,专心致志地听我交代工作事项,十指平静地交错在一起,它们整洁、饱满、浑圆、红润、鼓凸。她显然极有悟性,而且好问。前后三次,她掏出一块丝绸方头巾,擦拭着眼镜片。
婚礼后,我的小舅子请我的爱妻摘下眼镜。他望着她的眼睛的深处。你嫁给了一个好男人,他说。他会使你幸福的。由于那个时候他无所事事,我就邀他在我的公司做事。很快他就成了我的合伙人,他的生意做得那么有声有色,他的生意头脑那么精明灵活。
温蒂的判断力,她的明晰,她的谨慎,对我们的公司来说,真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我的眼睛紧贴着钥匙孔,听着他们急促的喊叫。那条细缝甚是模糊,惟有他们起起伏伏的欢爱声回荡在我的耳鼓,那是极乐时的嘶嘶声和忙乱声。整个房间沉压在我的头上,讨厌的黄铜把手硌着我的脑袋,可我不敢扭动,害怕看见我的秘书在我的合伙人的大肚子上和毛丛上迷醉地扭动着身体,发出低沉的尖叫声和刮擦声。

我的妻子想知道我心底的想法。你爱我吗,她问。爱得很呢,我轻蔑地说。我会弄清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会弄清你说的是不是真的,说说看,你怎么证明这一点,还有什么能证明,还能拿出什么证明。全都是证明(我决定采取一种更巧妙、更有暗示性的计策)。你爱我吗,我反问一句。
乒乓球台上满是条状的污痕。我赢球心切。我的儿子们在看球。他们为我加油鼓劲。他们对我的忠诚一望便知。我被感动了。我又操起长久以来屡试不爽的打法和策略,弹,削,搓,推,使出浑身解数吓唬他。我凭感觉打球。我那两个孪生儿子使劲地为我打出的好球喝彩。可我的小舅子不是傻瓜。他一板接一板,板板都抽到我的正手的远角。我连溜带滑,踉踉跄跄,怔怔地望着他的球拍噼啪噼啪猛击,眼前渐渐空茫一片。
我的那些锤子在哪里,我的那些螺钉,我的那些锯子?
感觉怎么样?我的合伙人问。绷带缠得平不平?结打得紧不紧?
门砰地关上了。我在哪里?在办公室还是家里?我的合伙人出去时是否有人进来过?他出去过吗?这些拖曳的脚步声、吱吱嘎嘎声、长长的尖叫声、刮擦声、咯咯的笑声和喘气声,难道是我的幻听?有人在倒茶。粗硕的大腿(是温蒂的?我妻子的?她们俩的?是交叉着的,还是并拢着的?)支撑在尖细的高鞋跟上,微微晃动。我小口小口抿着茶。味道不错。我的医生热情地问候我。稍等片刻,老伙计,我们马上就拆绷带。来一块糖衣脆饼吧。我婉言谢绝。鸟儿在鸟澡盆里嬉水呢,他那一身白的妻子喊道。他们全都跑出去看。我的儿子们把什么东西碰翻了,或是撞倒了什么人?肯定不是。我还从未有幸听说过他们如此莽撞冒失。他们只是喋喋不休,咯咯地笑,起劲地与他们的舅舅谈着自己的作业。我的父母一言不发。房间显得很小,比我记忆中的要小。我知道每样东西都放在何处,每一样都知道。但房间的气味变了。也许因为房间里挤满了人。我的妻子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笑开了,笑了好一阵,就像我们婚后最初那段日子里她常进发出的那种笑。她为什么笑?有人给她讲了一个笑话?谁?她的儿子们?不可能。我的儿子们正在与我的医生和他的妻子谈着自己的作业。我马上就过来,老伙计,我的医生朝我喊。这时候,我的合伙人已经让那两个女人在近旁的一张诊台上脱了个半光。她们俩谁的身体更丰满可人?我早忘了。我拿起一只乒乓球。它很结实。我想知道他把那两个女人脱到什么程度了。脱的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或许,他现在正举着镜片观察着我妻子的圆滚滚的臀部和我秘书的圆滚滚的乳房。我何以能证实这一点?靠听动静,靠感觉。但这不可能。这一幕怎么可能在我儿子的眼皮底下发生呢?他们还会像刚才那样,继续与我的医生聊天,咯咯地笑?不会。不过,最好还是让绷带缠得平平的,结系得牢牢的。
只不过是幽灵罢了。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6年第2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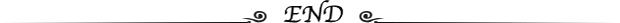
《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010-59366555
订阅微信:
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
[email protected]
投稿及联系邮箱
: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