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不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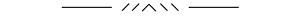
宗教与科学的相爱相杀
文 | 聂建松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实验科学的创始人,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他被马克思誉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实验哲学之父”、“近代自然科学直接的或感性的缔造者”。

他曾经写下了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科学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 Scientiarum),在其中他提出了人类认识上存在着四种“虚假的偶像”(Idola,中文翻译一般为“幻象”或者“假象”),分别是种族、蜗居、市场以及剧场。人们只有打倒这四种“偶像”,才能认识到真知识。
不过,本文并不打算给大家讲解一些陈年旧事。相反,笔者想要借着这“四种偶像”的理论,来谈一谈
“科普”的为难之处
——就笔者以及同圈子内的同仁们的交流来看,向群众们传播某个学科的内容,其实真是非常之困难。
但这并不是说就一定要教化大众,而是恐怕不得不承认这是大家普遍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
一、种族假象
什么是种族幻象(Idola tribus)?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为人类在认识上的固有缺陷。
笔者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布雷斯塔警长》(Brave Starr)。这里面的主人公布雷斯塔警长拥有熊的力量、豹的速度、狼的耳朵和鹰的眼睛——我们却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凡人,所以对于“超人”(或者说“非人”)如何看问题,我们实际上是无法完全理解的。
不过,这里笔者不是要谈超人的事情,而是要谈谈可能所有人都具有的一种有些俗气的偏好:面对未知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更喜欢“具体且形象”的表达方式。
大家一定都能回想起这样的场景。
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更喜欢图案;面对专业术语的时候,我们更喜欢自然语言;面对抽象的描写,我们更喜欢拟人的描写——
这当然是“科普”日常的必要手段,但是这些手段也必然招致一定的问题。
很多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的人一定都知道“波兰球”(Poland Ball),这种小球也被称为“万国球”(Country Ball),即用卡通球状的标志来代表一个个国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小球们都被“拟人化”成为一个个萌萌的小人物,国际关系则以小球之间的拟人式互动来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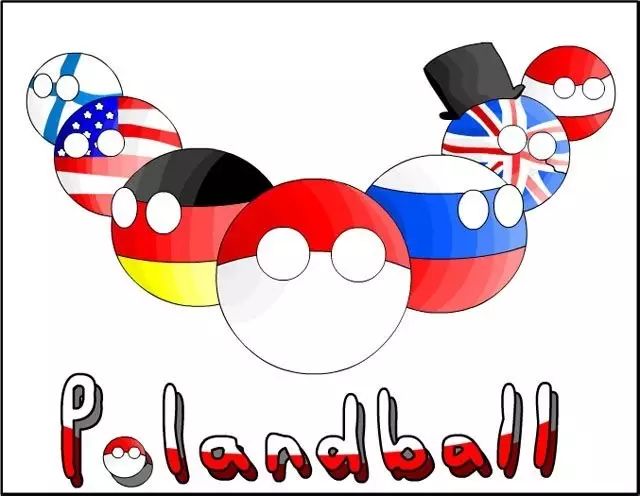
这种方法虽然令人喜闻乐见,但是也容易让人以“拟人化”的思路去理解一个本来“非人化”的事情——或许存在“国家气质”这样的玄学,但是一个政府实质上还是更接近一台无情运转的机器——当然,这个无情也不是说“残忍”,而是说,缺乏那种人类意义上的情绪。
有时候,自然科学工作者也会使用类似的词汇。比如,理查德·道金斯头两年写的那本畅销作品《自私的基因》。这就很容易让人们把本身不具有人类复杂情感的基因理解成为一种具有了人类情感的物质。以至于道金斯本人不得不在书的开篇要费笔墨重新解释,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自私”这个词。
自然界当然不止存在着采用“自私”策略的存在,也有很多生物采用了“共赢”或者“他利”的策略——如果把这些策略解释为更为高级或者更为隐蔽的“自私”,那么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复杂性。
而如果使用“自我保存倾向”这类的中性偏学术风格的词汇,又未必能吸引眼球吧?
所以,为了迎合普通的读者,一个科普作者也是不好做人的。
用一句俗话来说:说深了不是,说浅了也不是……把握这个度,挺难。
▍
二、 蜗居假象
什么又是蜗居幻象(Idola specus)?说白了,就是每个人的天赋、秉性和教育不同,导致了我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都会有角度和深度上的区别——隔行如隔山。
(在此,我没用更为传统的翻译“洞穴”,这容易让人误会是柏拉图的洞穴喻。实际上培根的意思更像是说,我们就像蜗居在各自不同的小小单元房一样,彼此无法沟通。)

那么,这在科普上又意味着什么困难呢?
实际上,就我观察,群众们其实对大多数的学科并不热心。这没有指责多数人的意思,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况——如果把知识分布的状况想象成一个“金字塔”,那么处于知识高处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可能是极少数。
因此,试图“科普”某个学科,实际上就是要求大部分人抽出一定时间来阅读和学习一个可能与他生活不太相关的内容。可人家为什么要抽出时间来接受“科普”而不去入坑某些游戏和二次元动漫呢?
在这个意义上,科普实际上总是面对的是“对此有些感兴趣的人”,而大概不能有普罗大众的希望——我写过关于“科学史”方面的些许微末文章,能有阅读冲动的人大部分是对中学历史课本中的相应片段感兴趣,但肯定也有好多人觉得
“这玩意有嘛用?都过去好几百年了……”。
倒谈不上“无用之用”这样宏大的意义。实际上,对某个学科感兴趣的人群,相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少数。科普的意义大概在于吸引这么一部分“相对多”的群体,为这些人提供一个晋级的台阶吧,而并非为整个社会提供“绝对多”的“科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群众们可能更感兴趣的是杨振宁的私生活以及“他当初怎么不回中国?”,而对他在物理学上的贡献和意义可能、大概、或许真的不太感兴趣。
▍
三、 市场假象
什么又是市场幻象(Idola fori)呢?说白了,就是我们日常在交流谈话(如同人们在市场之中一样)中所使用的“自然语言”缺乏精确的定义。培根以此来批判传统哲学中的一些“模糊概念”,比如“风水火地”这类自然哲学概念到底具体指什么?
不过,笔者倒并非想从这个角度出发,而是借着“市场”这个比喻来说明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嘈杂的“伪科学”或者“伪学科”的理论,
使得群众眼前如同一个叫卖声连天的“菜市场”一样
——很多“卖家”之所以获得关注,只是因为宣传比较“出位”而获利。
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承接上之前两个“假象”来看,实际上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么一个结论:在某个学科之中,处在“知识高处”的人与“缺乏知识”的人之间有那么一道“教育上的代沟”,而且不能指望大部分人主动迈过去这条沟,只能由少数人迈过沟来与大多数人沟通——这就是科普所要做的工作,使得大众中的一部分人或多或少地能够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然而,
如果某些人或者某些学说装作“从专业那边来的”怎么办?
因为大部分人缺乏相应的知识,群众本来就无法“
当机立断
”判断其人其说的专业性,只能被迫吃瓜看热闹。如果“制假贩假者”的叫喊声音大,并且恰好这东西又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那么群众几乎是会误入歧途——大家都会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
譬如,前些年福岛核辐射之后,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说盐(或者加碘的盐)可以防辐射,于是一场抢购食盐的风潮开始了。譬如,笔者幼时经历的全国上下的“气功热”,人们顶着铝锅和天线来接收“信息”,觉得自己闻到了某种莫名“香气”。譬如,当年谣传“打鸡血”可以健身。
这事情如今想来确实挺搞笑的,但是也提醒着这样一个事实:群众们最容易被菜市场上喊声最大的人所吸引,而他所贩卖的未必是真货/干货。
▍
四、 剧场假象
什么是剧场假象(Idola theatri)呢?说白了,就是说人们容易被思维上的“教条主义”所迷惑——就如同坐在剧场里看戏的观众,看到的都是条理分明,但却经过“设计”的“现实”。
培根的本意是在批判人们迷信权威,不过我却想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谈谈某些有意无意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也许不是被主动“设计过”的,但是大部分人自己把自己陷入了其中。

但凡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我国的教育制度是分文科和理科的,以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可谓经久不衰的“文科/理科”孰强孰弱的争论。那么问题来了,文科/理科到底能否说明全部分科?或者说,文理分科这玩意在高考应用以外,具有正确的意义嘛?
试举一例,按照高考的分科逻辑,请问经济学算是文科还是理科?
如果我们把数学工具当作理科的标准之一,那么经济学有资格就该算作理科的——甚至可以说,经济学中的“数学含量”可是超过化学的(即便是马克思也有数学手稿,虽然上面的一些数学观念有错误,但已经是当时能接触的较高的数学教育了)。可是如果按照研究对象而言,经济学研究的又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经济活动。
那么,就仅仅就刻板印象中的“文科”而言,譬如宗教学,很多人觉得这是在“天天念经”?或者谈到“中国哲学”就觉得是“之乎者也”的“通俗版国学”?或者谈到“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就觉得……什么思想的不是中国早有了嘛?
宗教学的一个必修科目是“科学与宗教”,这是“科学史”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哲学也有研究“中国传统博物志”的,也可以说是“科学史”的一部分;西方哲学更是经常会涉及到“科学史”的。
所以,哲学系就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只会读两篇文字的文科系了?可我们实际中的一部分工作正是某些人刻板印象中的“理科生的工作”!在国内的教育系统中,高考过后,大部分人都得重新接受“大学学科再教育”——就某个问题的专业认识而言,只跟你是否受过相应学科的专业训练有关,而跟多数人遇到的中学的那套文理分科逻辑无关。
因此,这套日常的学科“刻板印象”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人们基于中学分科逻辑的臆测,而这恰恰又使得“科普”某些科目变得十分困难。
如果说前三种假象,或许还能透过学科内部的“权威”站出来与大众沟通,进行一番化解。那么,这第四种假象恐怕则是植根在很多人心中的有色眼镜。正如,一个对青霉素过敏又偏巧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人——医学上还能开发些别的药物,可“科普”并非看病啊。
·END·
大家
∣
思想流经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见 · 价值 · 美感

※本微信号内容均为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转载将追究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联系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