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后的山,雾从林间升起,如烟似幻,行走其中有漫步云端的飘逸感,之而有已羽化登仙的错觉。在事后,小腿酸痛方才醒悟,自己仍在人间,匹夫仍是俗人。
苔藓铺满树下的泥土,在缝隙中,孢子仰着触角,有些自不量力也,也有些尽力而为。蘑菇长满了山谷……长满是我的想象,虽然蘑菇的繁殖速度有这个能力,但你要知道,喜爱山珍野味的人类,吃的速度更是不可思议。唉,吃和繁殖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一蓬悄然开放的粉紫色杜鹃躲在湿漉漉的大树后面,它那超越人工花市艳丽繁华的清冷色就这样悄悄地给了我重重的一巴掌。它不争不抢,死死生生,在这无人问津的角落里。我来了它就不再无人问津,“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此时它便有了意义。此时它便有了意义?意义?这真是一个大问题。那些大树、小树、杂草,横七竖八枯败的枝条,被白蚁啃断长满黄色小菌的树干,满山的落叶,泥土里的百脚虫,偶尔忽闪而过的白色长尾山鸡,天空叽叽喳喳的鸟雀,它们有意义吗?偶尔走过这里的你、我,山下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人,有意义吗?
我只是一团物质吗?那我不过是一具还没死去僵化,但必定死去僵化被大火烧成白色粉末或者被虫蚁啃成白骨的肉而已。难道肉团需要意义?屋子,小区,城市,国家,地球,太阳系,宇宙……肉团啊,你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微尘。
肉团令人沮丧!
意义是个广大到没有意义的问题。打我从娘胎里出来,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奔向死亡的过程。在生死之间除了满足基本生存,就是无休止地寻找意义(当然,如果生存和延续是意义的全部,也该是一件单纯而幸福的事),是像路边的一棵草,此生为了把种子铺满大地?是像溪里的一滴水,此生要回归最东方的大海?是像林间的鸟儿,此生为了把基因能够得以传递?我们定不只是一块行走的肉团,为此我们竭尽全力的去发现意义,发明意义。
越来越多的人说,其实最终没有意义,在折腾意义的过程里你也许陷入了自我假设和假设世界的臆想,通过把臆想具体化、逻辑化和神圣化,继而得到了内心的自恰与平和,这给人一种虚无感,我不认同。这自恰与平和就像一条直线,是一维,还有二维、三维,甚至四维、五维,低的维度永远无法想象比它高的维度,定是存在着那些超越理解的理解,而它不在我们思维的范畴内。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思维,让我们一直陷在思维里,熟悉它、接纳它、运用它,按照线性或非线性的思维逻辑去判断、推论和想象,这让我们有掌控感和安全感,但这同时也破坏了我们仅存的一丝丝超越的可能性,让我们发现不了或波澜壮阔或平白无奇但却实在的存在意义。
如何才能超越?我实在是不知道的,我知道
的
也仅仅是一些的不能超越。
当我很理智去写这些文字,全篇谋划布局,思前想后考虑周全,那我便堕入了限制,便无法超越。
当我说我在直抒胸臆,那我只是在欺骗,只是欺骗的手段略高明了些,当我的眼睛看向远方,你也不要轻易的就下判断说我的思绪也随之飘的更远。
在这雨后的山间,我想太多,已经不知道走到何处了。
我迷失在烟雾弥漫的山峦之中。
这时,一阵钟声传来,定是山间的寺院传来的,刚开始上山的时候我还想去寻这庙,但是走着走着,就不知在何处了。现在庙虽然看不见了,但这钟声,这雄浑的钟声定是穿破了重重阻隔,从不知在山间何处的庙里清清楚楚、连绵不绝的传到我耳朵里的。
我看不见那庙,我同样也看不见那钟声。只有走进庙宇才能感受庙宇,可站在山间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钟响,我都可以听到,听到这雄浑的令人心潮澎湃的钟声。
图片来自:JD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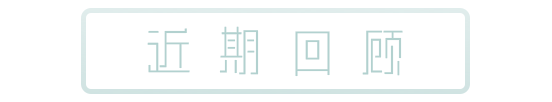
麦田里的光脚人
乞丐西天寻佛记
人的中心
一组特别的fo话/画
我是谁?我TM到底是谁?
在这沙尘暴里我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