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夏天,巴黎奥运会期间,乒乓球手倪夏莲又一次闯入公众视野。这是她参加的第六届奥运会,61岁的她在女单第一轮比赛中击败31岁的土耳其选手阿尔廷卡亚,其后在第二轮赛事中败给23岁的孙颖莎,止步32强。
她也成为“奥运史上最年长的乒乓球手
(之一)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全世界,任何年龄段的人、任何类型的人都可以打球。”
巴黎之行结束后,倪夏莲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她生活的卢森堡,遇到她的球迷兴奋地与她合影留念,而在她的故乡中国,人们不厌其烦地讨论她在赛场上的表现及其不设限的人生。
倪夏莲的乒乓之路始于7岁那年,16岁时凭借在第四届全运会上的优异表现“一炮而响”,从此进入国家队。在国家队的7年间,她与郭跃华搭档,获得1983年东京世乒赛混双冠军,三年后退役,1980年代末移居海外,辗转德国、卢森堡等地,最终加入卢森堡国家队和当地一家乒乓球俱乐部。
与乒乓球打交道的五十几年里,倪夏莲数度想挂拍,又因种种原因重返赛场。如今年至耳顺,她直言生活中有太多比乒乓球更重要的事,比如女儿和家人的健康。四年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她曾说“乒乓球不是生活的唯一”。2025年1月,我们重访她时,她依旧如此笃信。
2025年初,倪夏莲回到上海,参加活动、备战1月底进行的WTT新加坡大满贯比赛。然后是“欧洲16强”的赛事。至于再接下来,她不能确定,或许就像她常常挂在嘴边的“Never say never
(永不言弃)
”。
在2025年WTT新加坡大满贯赛中,倪夏莲展现了老将的坚韧不屈。混双比赛中,她与搭档姆拉德诺维奇以3-1战胜卢伟/高桥·朱丽叶组合,晋级16强,其中第三局轰出11-0的比分。随后他们以1-3不敌国乒组合林诗栋/蒯曼,无缘八强。女单首轮,倪夏莲与国乒选手钱天一苦战五局,最终以2-3惜败,未能晋级32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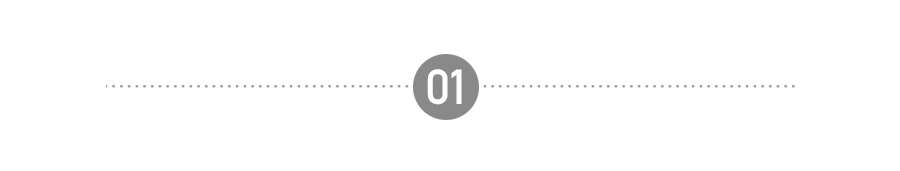
人生充满了可能性
南方人物周刊:
你说是为了不掉积分才参加WTT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现在分数和排名对你来说依然很重要吗?
倪夏莲:
不重要。这么多人都希望我打下去,我目前的决心也没有大到把这块球板扔了。既然如此,大满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有时间的话,我没有理由不参加。所以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打到什么程度是另一回事。
南方人物周刊:
就是不太在乎在赛场上的表现、但也不想完全丢掉的心态?
倪夏莲:
我在乎自己在比赛中的表现,但我的能力有限。我希望打得好一点,但能不能打好就交给上帝了。有的时候练得很好,也不一定在比赛中打得很好,如果练得不好,基本打得也不会很好。所以只能努力去练,争取打好。
南方人物周刊:
许多人通过奥运会认识你,年末我在社交平台看到一个有关女性力量的总结,其中就包括你。这几年里,你还在参加比赛,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鼓舞。
倪夏莲:
我希望通过自己在做的事情和大家分享,人生其实有很多可能性的。首先我是女性,也是一位母亲,我们女性就不要被身份限制住了。不要觉得我们不行,我们也有我们的特点;其次我是年长者,我们也不要被自己的年龄限制,它不是我们前进和学习的阻力。我们永远可以学很多东西,也可以向年轻的后来者分享经验教训,供他们学习。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成功,其实成功背后也有很多苦难,所以我们不要怕解剖自己,我很愿意和大家分享;然后我也是一位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所以不要给自己在地域上设限。人在不同的身份、位置和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定位。
南方人物周刊:
外界对你的期待会让你有压力吗?
倪夏莲:
我很感动大家给我的支持和鼓励,但是我很明白人是不能和自然斗的。我把人们对我的期待作为动力,尽己所能。
南方人物周刊:
你刚刚提到的种种不受限的想法,从什么时候有的?
倪夏莲:
有一个过程。人生就是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不要觉得老了什么都会了,老了也有很多迷茫和无知的地方。我的特点是喜欢想,赢球时想得少一点,输球时想得多一点。人生也是这样的,很多东西不知道就多学一点、多想一点。慢慢积累和思考,才让我醒悟到很多。没有人能从110伏的电压马上转换成220伏,都需要一个过程,但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好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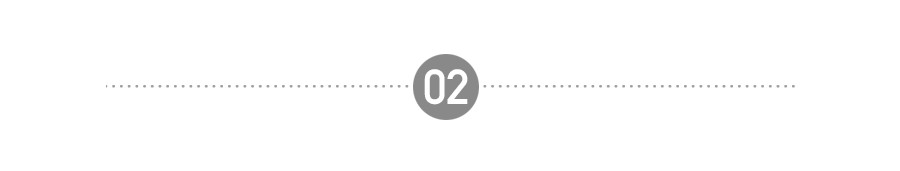
乒乓球不是生活的唯一
南方人物周刊:
聊聊2024年夏天的巴黎奥运会吧,你现在能想起的事情和时刻有哪些?
倪夏莲:
这次巴黎奥运我觉得表现得淋漓尽致了。首先我这个年龄能够赢一场球,几乎是破了奥运的纪录,从成绩上讲是很欣慰的。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想纪录这些事,既然有,就觉得很自豪。它也展现了我们中国人的乒乓球技术——连一个老奶奶都会打乒乓球,到现在还在吃老本。
那场比赛其实有很多值得总结的:我本来是以3:0的比分领先,被对手追到3:2。整个局势对我很不利,体力各方面都在走下坡路,但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不放弃,该攻就攻,不因为被追平而怯场,中间当然也犯了一个保守的错误。总体而言竞技体育就是有起有伏的,好在自己能及时调整心态和战术,把球赢下来——确实也是永生难忘的一场球。
南方人物周刊:
你在巴黎周期期间的体力、状态与东京奥运会相差大吗?
倪夏莲:
心态上都差不多,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大家都会很认真地准备,世界高手那么多,我能够赢一场就不错了,这次算是如愿以偿。当然如果没碰到莎莎,万一之后还有一点点机会呢?
(笑)
不过我也觉得,能跟世界第一打球挺好玩的。
南方人物周刊:
训练计划有变化吗?我看你在采访中说自己现在用椭圆机和跳绳代替跑步。
倪夏莲:
变化其实不多。椭圆机会跑20分钟到30分钟,锻炼心脏承耐力。也会做一些力量训练,锻炼腿部和手臂力量,还有腰腹和背肌——这些都是运动员必须具备的。
我现在练得比原来少一些,情况好的时候,就多练,没睡好的话,就少练一点,不强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考虑最多的是不能受伤和生病。从恢复的情况讲,每年都不一样,不会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这是自然规律,所以我总说人是不能和自然斗的。
南方人物周刊:
每天都会有训练?
倪夏莲:
很难做到每天训练,因为还有别的事情,乒乓球不是生活的唯一。我一般是根据比赛的情况调整,巴黎奥运结束后我休假了很长时间,也参加了许多活动。最近WTT新加坡大满贯比赛临近,天天要训练。最好的状态是能保持自己的身体素质,它是长期的工作。技术方面,我五十多年打下来,肌肉已经定型了。打球时,只要击球点在想要的位置就够了。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没有谁对谁错,
(现在)
我比年轻的球员练得少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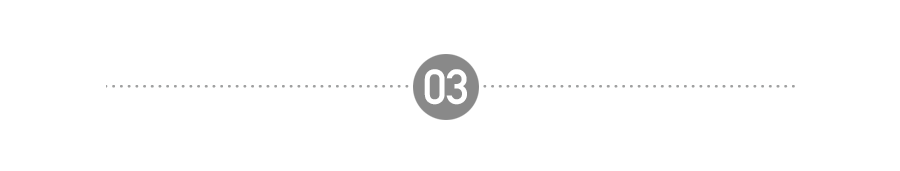
一切顺其自然
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这次魅力人物的主题是重启,对你来说,人生和事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启的?
倪夏莲:
我的人生有很多次重启。巴黎奥运结束后,我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算是重启。离开中国国家队到德国是重启,从德国到卢森堡也是重启。我生了两个孩子,也算重启。但我没有把它们看得很重,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人生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
南方人物周刊:
当初去异国打球时,遇到过哪些困难?
倪夏莲:
虽然大家现在都讲地球村,但三十多年前去的时候,语言还是很大的障碍,生活方式和现在也很不同。想父母了,不能打视频电话,越洋电话也很贵。吃的东西也没现在这么多,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会带来情绪问题,但这些都是小事,能不能赢球才是关键。我很幸运,一直赢球,心里才踏实,不然觉得拿这份工资有些愧疚。
另外一个有些困难的事情是,面对全新的环境,空气不一样,打法也不一样,你不知道对手是什么样的。后来到了卢森堡,都是男性球员,很难找到合适的队友训练。幸好我有扎实的基础,能及时调整,才取得一些成绩,没让他们失望。
南方人物周刊:
对于1980、1990年代的运动员而言,退役后常见的职业发展路径是怎样的?
倪夏莲:
和现在差不多。有的人进了单位,有人去读书,也有人至今在公司上班,或者出国。
南方人物周刊:
前阵子我写过一篇稿子,是说巴黎奥运会期间,一些欧美运动员被媒体曝出在成人社交平台OnlyFans上通过发布照片和视频获得收入,引发不小争议。你听说过这件事吗?
倪夏莲:
我不清楚具体的事情。就卢森堡和中国而言,在卢森堡做运动员的话,会比较辛苦,小时候要读书,成年后要上班,训练对手不多,经费也不多,国家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小。但在中国,运动员有陪练和教练,所有都是专业的,由政府保障。
我还听说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运动员参加比赛也要自己花钱。有赞助商的话还好,对于一些刚冒起来的球员,他们没有赞助商的话,只能自己想办法——这是他们在竞技体育职业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但等到退役时,西方球员的出路就比国内的运动员多,因为他们都有文凭,而我们的球员都是一心一意打球、搞专业。等到退役,需要重新再去读书。
南方人物周刊:
1986年退役后,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的?
倪夏莲:
当时我留在上海做教练,或是从事与乒乓球有关的工作也可以,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可以看得到底的生活。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有机会出去看看、体验生活也蛮好玩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我周围的队友出去了很多,对我冲击很大,觉得不出去好像就是没人要一样。我想证明自己对社会是有用的。就这么被推着走了。
南方人物周刊:
四年前你跟我说过,如果家里出现一些状况,一定不会再打。现在也这么觉得?
倪夏莲:
家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不只是独立的个体,也有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作为母亲的责任是不可替代和逃脱的,当然父亲也很重要。家庭和身体好好的,我才有可能去打。如果少了一样,就是我忍痛割爱、和乒乓球说再见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