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感恩至死
日本电影研究者,上海国际电影节日本电影策展人
在田山力哉与猪俣胜人合著的《日本映画作家全史》(社会思想社,1978)中,两位作者对牛原虚彦有一段善意的调侃文字:
「在派对、聚会之类的场合,如果是初次见面打招呼,这个人开头通常会先说『我是卓别林老师的第八个弟子』,然后再跟你谆谆开谈,『我现在虽然已经多少岁了,但仍然在不断学习,绝不输给年轻人。卓别林老师对我说过,人的价值90%取决于努力,只有剩下的10%是靠才能。』初次听到的人会被他这番庄重的发言击中肺腑,深感肃然,但是当你把这珍贵的名言五遍、十遍地听下去,耳朵就起老茧,把它当成耳边风了。有『过来人』告诫道,在牛原老师面前千万不可提往事。事实上,这个人年纪越大就越爱念旧,他又健谈,有声有色,简直堪比专业说书的。」

这段文字虽略显夸张,却透露出牛原对自己电影生涯的强烈自豪感,而他,也确有其自豪之资本。作为日本电影的元老之一,他地位显赫,从小接受精英教育,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的他,在草创期的日本电影界更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除了电影创作本身,牛原虚彦在电影的教育与国际交流上更是功勋卓著,而他与中国也有着深厚的情谊,早在二十年代就曾造访上海寻求合作,在战后亦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日本电影人,这些都将在文中详述。
牛原虚彦生于1897年,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是与电影一同诞生的。牛原家里是武士世家,祖父曾被选为皇宫守卫,父亲也是地方武士,但因在西南战争中加入了熊本部队而背上了「国贼」的骂名。
尽管如此,牛原的父亲仍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后在九州日日新闻社任活字铸造部主任,同时也是家里柔术道场的师傅。父亲平时喜爱读《春秋左氏传》、《礼记》等书籍,是个学究,牛原虽未继承武士的体魄,耳闻目染之下,倒也从小就颇为好学,成绩出色。
初中时,牛原考取了历史悠久的当地名校熊本县立中学济济黌(现为熊本县立济济黌高等学校),这所学校人才辈出,以「文武两道」为教育方针,在当时的日本教育界颇受重视,牛原入读期间,连中国的孙中山、黄兴、戴季陶等名士都曾去参观访问过。
初中毕业后,牛原又入读了当时赫赫有名的精英学校第五高等学校(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两位日本前首相均为该校校友),这所高中堪称进入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的跳板,而他之后也升入了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并顺利毕业。
在日本,对于这种一路接受精英教育的过程,有一个词称之为「Elite Course」,而按当时传统的思路,东京帝大毕业的顶级精英知识分子,理应从军、从政,或至少都是学者、企业家,但牛原虚彦却做了一个让当时的帝大教授与同学们都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投身电影界。

牛原虚彦(中)
日语中有一个词叫做「河原乞食」,何为河原乞食?戏子也。这是当时对歌舞伎等艺人的蔑称,虽然电影广受大众欢迎,但尚处于草创期的电影界,其社会地位仍是相当低下的,仍被这些精英人士斥为「河原乞食」,牛原此举当然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反感,因为本应跻身精英之中的他,居然选择了一份如此下贱的工作。
在这件事上,牛原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与反对,他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就读东京帝大期间,靠的是「肥后奖学会」的资助,这是一个专门资助熊本出身的优秀学生的基金会,毕业生必须向其运营委员会的成员与前辈做就职报告。
该学会的理事会成员,都是一些军队将领、政府大臣、大学教授、公司董事等当地出身的名人,对于一个欲做「河原乞食」的「败家子」,岂可容忍?最后还是学会会长细川护立侯爵谅解了他并出面干预,才最终放行,这位侯爵后来还资助牛原出国游学,在事业上给予其很大的帮助,被牛原视为生涯中最大的恩人。
那么牛原又为何要放弃大好前途投身电影界呢?这自然是源于他对电影的热爱,而这种热爱也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电影早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对于童年时代的牛原则不同,那是一种完全新奇的体验,并正好伴随着他的成长而逐渐发展,看电影成为了他最大的爱好与乐趣。

当时的日本,电影还不叫做「映画」,而叫做「活动写真」,而牛原他们这群人则将自己称之为「活动狂」,一个「狂」字,可见痴迷,无论学业多忙,有电影看绝不错过。来到影业兴隆的东京后,牛原的观影狂热症变本加厉,每周都流连于各大电影院。
后来细川侯爵的一位友人恰好是东京浅草(影院聚集地)某警署署长,在得知牛原酷爱电影后,便依靠关系让他能在几家电影院免费看电影,此举解决了牛原的经济负担,去影院的步伐也益发频繁了。除了看电影之外,由于牛原英文出色,文笔也很好,读书期间也会做一些与电影相关的翻译与文字工作。
早在老家熊本时,他就受开电影院的友人所托,编译美国电影资讯,也因此得以遍览最新的《Motion Picture Magazine》、《Motion Picture Classic》、《Photoplay》、《Universal Weekly》等当时流行的美国电影杂志,这让他积累了美国电影的丰富知识,日后得以兼职在杂志上写美国电影相关的文章。

《Motion Picture Magazine》
1920年,牛原拜在小山内薰门下,随后正式入职松竹公司的蒲田摄影所,学习摄影、剪辑等技术。前文提到,当时电影人社会地位不高,因此从业人员的学历也普遍不高,初入职的薪水是很低的。
牛原身为帝大毕业的高材生,在电影界实属凤毛麟角,公司虽不能给他有别于其他人的特别待遇,但考虑到他学历高,文笔好,正好让他写剧本,以稿费的形式补贴其收入,对于牛原来说,这也不失为一举两得的事情,既有外快拿,又能得到锻炼。
所以说,虽然他这个精英自愿屈身电影界做「河原乞食」,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的「高贵」出身也确实让他得到了不少特殊照顾,后来更是在世界舞台大展拳脚。
在写了几部影片的剧本以后,牛原加入了小山内薰创立的「松竹电影研究所」,并在研究所创业第一作《路上的灵魂》(村田实,1921)中担任编剧一职。

《路上的灵魂》(村田实,1921)
由于主持者小山内薰的留洋背景以及牛原丰富的外国电影知识,这部作品显然深受格里菲斯《党同伐异》的影响,尝试了交叉剪辑等手法。虽然影片最终的票房与反响并非太好,但其在艺术上的开创性尝试却不容置疑,亦成为早期日本电影史上一部标志性的作品。
牛原作为导演的处女作是研究所的第二部作品《山中暮色》(1921),副导演是后来亦成名导的岛津保次郎。可惜的是,这个研究所创立当初虽然雄心壮志,但仅仅只摄制了三部作品以后就因成绩不理想而解散,小山内薰退居松竹董事,牛原等人也纷纷重回蒲田摄影所。
此后,牛原在松竹拍摄了《断崖》(1921)、《为了生存》(1921)、《年轻的人们》(1922)、《噫无情》(1922)、《人性之爱》(1923)、《无花果》(1924)、《丰情歌》(1925)等不少影片,其中《无花果》拍摄过程中恰逢关东大地震而被迫中止,直到次年牛原重回蒲田才摄制完成。
在此期间,牛原第一次与中国发生接触。1925年,他远渡上海,带着他的日中合拍片计划来寻求合作,这也是他首次踏出国门。牛原的眼光可以说是非常超前的,如我在此前文章中所说,当时的日本电影界对中国电影一无所知。
川谷庄平也是差不多于同年来沪的,但他只是身为摄影师来闯荡谋生,三年后前来的另一位电影导演铃木重吉也纯粹只是观光,与中国电影业界并无接触,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日中合拍片则已经是川喜多长政于1938年制作的《东洋和平之道》(导演正是铃木重吉)了。

《东洋和平之道》(1938)
实际上,牛原在此之前就已经与中国人有过接触,他于1922年拍摄的《噫无情》这部影片就是以中国为舞台的,但仅限于住在东京与横滨的中国人给予指导,这次上海之行则正好是验证其中国想象的好机会。上海之行后,他又以切身体验拍摄了另一部以中国为舞台的影片《丰情歌》,这两部作品,都是早期日本电影中罕见的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
来到上海后,牛原陆续拜访了留洋派的陈寿荫、明星公司的郑鹧鸪、张石川、郑正秋等业界大腕,以及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等人,商谈合拍片的筹备。可惜的是,或许是由于当时内战波及江浙地区的原因,最终计划未能实现,而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受到了上海影人的热情款待,彻夜大啖中华美食让他感受到了同行的豪爽,从此也成为了绍兴黄酒的忠实爱好者。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收获,是与欧阳予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战前战后两人多有交往,1927年欧阳予倩造访松竹蒲田摄影所时,牛原也热情接待了他。

1927年,欧阳予倩访问蒲田摄影所,前排右起:岛津保次郎、牛原虚彦、欧阳予倩、龙田静技、葛见丈夫。
访问上海归来后的同年下半年,牛原立刻又得到了一个出国的机会,这次仍然是赏识他的细川侯爵慷慨解囊,鼓励他去好莱坞学习深造,对于牛原来说自然求之不得,于是他征求东家松竹的同意后,带着两部自己1925年的作品《象牙之塔》与《乃木将军》,于次年年初抵达好莱坞。
通过前辈上山草人的帮助,牛原每天都在联艺、福斯、米高梅等电影公司参观学习。在此期间,当时洛杉矶的日本领事大桥忠一将其带来的两部影片在好莱坞的一流影院内放映,并邀请了一批好莱坞影人进行观摩。
其中包括蒙蒂·布卢(Monte Blue)、黄柳霜(Anna May Wong)、雷蒙德·格里菲斯(Raymond Griffith)等明星,以及金·维多(King Vidor)等著名导演,当时的媒体亦有报道。毋庸置疑,这是在好莱坞的首次日本电影放映,比起川喜多长政自1929年起向海外输出日本电影的记录还要早。

蒙蒂·布卢(右二)
牛原在好莱坞的另一个收获,是师从过电影大师卓别林(Charles Chaplin)。他之所以能顺利被卓别林收罗,这要得益于卓别林的秘书,日本人高野虎市,此人给卓别林做了十几年秘书,深得其信任,以至于卓别林的司机,以及比弗利山庄豪宅内的佣人也都是日本面孔。
学习期间,牛原以摄影队助手的身份参与了影片《马戏团》(1928)的拍摄工作,并与当时恰在卓别林手下工作的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成为了挚友,这些都成为了他日后引以为傲的谈资。

《马戏团》(1928)
在电影之都深造了八个月后,牛原回到日本重入松竹,并以其与铃木传明、田中绢代的组合,炮制了《近代武者修业》(1928)、《他与田园》(1928)、《他与人生》(1929)等一系列卖座影片,奠定了导演地位。
但在1930年,由于与公司因作品产生纠纷,他离开了老东家松竹,再次抱着「学习有声技术」的目的远赴海外学习,这次则是前往德、法、英等电影技术发达的欧洲各国,一呆就是整整三年。
1932年回国后,牛原没有选择回松竹,而是进了京都的日活摄影所。在这里,他除了拍片以外,也凭借自己在欧洲学习的经验进行有声片的技术支持,在他的斡旋下,日活与西部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签了约。
公司第一部用西部技术摄制的有声片《别和爱情开玩笑》(青山三郎,1933),也是有他在内参与的。此外他还有另一份重要的工作,就是教育与培训,包括新人演员的训练、新人导演的录用,他都要负责。

实际上,牛原很早就已经执起教鞭了,这大概是由于东京帝大的高学历出身,在电影界一直受到学者般的待遇,教育工作自然也首当其冲。
早在1925年,松竹蒲田摄影所成立演员养成研究所时,牛原就与知名剧作家野田高梧等人同为教师,这个研究所学生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后来成为小津电影标志的笠智众。1929年,日本大学法文学部内成立了日本首个电影学专业,牛原又被聘为讲师,每周授课两次。
1934年,由于日活将其现代剧制作部门由京都搬至东京,牛原便离开日活,转而加入了位于京都的新兴电影公司旗下的高田制作公司,由于新兴是松竹的旁系公司,因此他可以说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老东家的怀抱。
在高田,牛原又一次充当了技术先锋的角色,在其执导的影片《急行列车》(1935)、《故乡之歌》(1936)中,首次尝试了将国产富士胶片用于剧情片拍摄,这一举动打破了进口胶片的垄断地位,对于日本电影耗材产业的发展有相当重要意义。
不久之后,高田制作公司倒闭,牛原则于1936年进了新兴电影公司,拍起了不少时代剧(即古装片),其中他最为风光的一部作品,是战时电影公司整合,新兴与日活、大都被合并为大映后,大映的创业作《维新之曲》(1942)。
这部作品真可谓是超豪华制作,拥有迄今为止都未实现过的梦幻般的顶级演员阵容。由于公司合并的关系,使得阪东妻三郎、片冈千惠藏、市川右太卫门与岚宽寿郎这四位「剑戟片四天王」会聚一堂,齐齐在《维新之曲》中亮相,而担任导演的正是牛原虚彦,可见其身为导演的地位还是颇高的。

阪东妻三郎
虽然在四位天王如何排名上颇费脑筋,但相信他的激动之情并不亚于在银幕上看到四天王齐聚的狂热观众。
1943年,大映的专务董事永田雅一找到牛原,告诉他上海准备要办一个「国际映画大学」,希望他以创立委员之一的身份前往上海,并表示这也是情报局的请求。
大映于1944年在上海制作了臭名昭著的日中合拍片《春江遗恨》(稻垣浩/岳枫),而这个计划正是永田雅一先行赴上海进行该片准备工作时,与汪伪政府文化部长林柏生以及中华电影公司高层商量下来的结果。

《春江遗恨》(1944)
实际上牛原早在1938年时就已曾再次到过中国大陆,但那次的经历并不愉快,他是受「爱国后方会」的委托,去拍摄汉口战场的纪录片的,结果战争的惨状令他颇为震动。
而这次,他则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前文已经提到过,他自在研究所担任小山内薰助手以来,在松竹、日活、新兴、大映这些公司,无一例外都担当着演员培训以及研究所的工作,而当时他也在菊池宽任校长的日本映画学校(并非今村昌平于后来创办的日本映画学校)做老师。
可能是长期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让他也觉得有在中国设立这样一个「传道授业」的电影学校的必要性。于是在1944年1月,牛原接受情报局的命令,满怀期待来到了上海。
牛原的直属上司是当时中华电影公司董事之一的不破祐俊,因此他的办公室也设在了中华电影公司内,并由几个在日本留过学的中国人(应为黄天始等)协助其工作。
随后他便开始了制定课程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他参考自己在欧美诸国学习到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积极研究中国的教育制度,以进行合理的调整。此外,牛原还想到了与自己交情很好的欧阳予倩,欲请其出山帮忙,但在当时的局势下,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欧阳予倩(右)
经过一番东奔西走后,牛原终于制定出了一个事无巨细的大学教育课程稿,不过可惜的是,随着日军的战局越来越不利,这个「映画大学」的计划最终未能得以实现,在友人的劝说下,为了生命安全,牛原于1944年12月中旬,带着遗憾离开了上海。
战后的牛原只拍了寥寥数部电影后,就完全退出了电影制作的前线,转而继续执掌教鞭,全身心投入到电影教育工作,以及积极的对外交流活动,摇身一变成了电影活动家。
教育方面,牛原于1950年被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专业正式聘为客座教授,开始了正式的校园讲坛生涯,1956年,他被提拔为专任教授,一直干到退休后又以讲师的身份继续执教,1975年起,他又出任日活艺术学院院长,直到1985年去世为止,始终兢兢业业,以培养日本电影人才为己任。
教书育人的另一方面,牛原也积极投身电影活动。日本最重要的一个导演组织,日本电影导演协会战前的成立与战后的重组,都少不了他的出力,而他也于战后重新成立时担任了协会的副会长。
同时,牛原亦频繁赴海外进行国际交流,他访问过无数国家,更参加过戛纳、柏林等大大小小的诸多电影节,与川喜多长政夫妇一样,作为日本电影的代表活跃于世界舞台。
1956年,他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之邀出任评委,与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等知名影人同席而坐,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日本电影人。

卢奇诺·维斯康蒂
1959年,他又受邀出任首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并于次年又继续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担任评委,这些成绩,都是对其作为一名优秀电影工作者的肯定。
在牛原的国际交流活动中,最值得书写的一笔,就是他与新中国的来往。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创立当初的干事之一,他于协会成立的前一年就实现了对中国的访问,也成为了战后首位访问中国的日本电影人。关于他的首次访华,其背后的过程还颇为曲折。
事情缘起于1955年6月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由于原来的人选突然有变,结果本在幕后的牛原被临时推举为日本电影界的代表去参加大会,毫无疑问,战前有过丰富海外游学经验的他也是最佳人选。
在这次大会上,牛原结识了苏联导演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夫(Grigori Aleksandrov),并受邀访问苏联。牛原在欧洲辗转游览后,来到了奥地利维也纳,作为取道苏联前的一站。

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夫(右一)
之所以选择维也纳,是因为当时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日本代表西园寺公一就在维也纳,通过他可以联系到中国这个除了苏联之外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既然都去苏联了,怎可以错过中国?
在维也纳,为了取得进入中国的许可,牛原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等待。他首先通过西园寺的帮助,直接与莫斯科的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以及北京的和平委员会取得了联系,但事情并非如他想象的那般顺利,苏联方面较顺利,但北京方面却始终不给回复。
无奈之下,牛原只得再次求助西园寺,在维也纳找到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刘贯一的夫人以及当时在维也纳工作的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得到回音,并于不久后从北京收到了刘贯一的电报:「欢迎访问中国,请速告知出发日期。」
得到官方通知后,牛原便赶往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国大使馆去领取前往苏联与中国的签证。在布达佩斯,牛原受到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参赞林耶以及书记官霍青的热情接待,并取得了当时一般日本游客根本不可能拿到的苏联与中国的入境许可。
苏联的参观访问结束后,牛原终于从莫斯科坐飞机抵达了北京。在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钱筱章、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钟敬之、导演吕班、外交家唐明照等人的建议与安排下,中方为牛原制订了一条经由北京、长春、沈阳、天津、上海、杭州、广州,从北到南的参观访问行程,以及相关研究座谈会。
行程中,牛原相继参观了北京、长春、上海的各个电影制片厂,以及北京电影学院等设施,受到了司徒慧敏、水华、袁小平、吕班、桑弧、赵丹、夏衍等各地中国影人的热情接待,并了解了新中国电影发展以及教育的状况,此行还让牛原得以与多年的老友欧阳予倩重逢,而欧阳此时已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
除了了解中国电影状况以外,牛原还注意到了当时有《二十四只眼睛》(木下惠介,1954)、《姬百合之塔》(今井正,1953)等四部日本电影正在译制,也让他对往后的中日电影交流充满了信心。

1955年访中时,在中戏前与院长欧阳予倩合影。
1956年,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日本成立,牛原成为协会干事之一,并于次年即1957年2月,亲自以团长身份带领日本电影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该团队成员包括剧作家八木保太郎、女演员岸旗江、男演员伊藤雄之助等,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并与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赵丹等影人展开了亲切的交流。
同年8月,牛原的身影又出现在了上海,这次他则是带着日本电影代表团来参加第一届亚洲电影周,影展期间,日本代表团团员与中国影人就中日合作以及中国电影代表团的访日等问题进行了商谈,牛原还在各国代表的推荐下,起草了一份《亚洲电影周各国电影代表团联合公报》,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后印刷分发。

1957年「亚洲电影周」期间,与各电影代表团畅谈。左起牛原虚彦、望月优子、哈马德(黎巴嫩)、进藤诚吾、Sukardi(印尼)。

1957年率领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在西花厅受到周恩来接见。

1957年率领日本电影界代表团访中。右起:文化部长茅盾、牛原虚彦、伊藤雄之助、岸旗江。
196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之际,牛原又一次得到了访问中国的机会,不过这次他是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员的身份前往。
一行人参观了天安门广场的国庆大游行,颇受震撼,而次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内3000多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让他们瞠目结舌。除了庆祝以外,牛原也与司徒慧敏、蔡楚生、凌子风几个老友叙了旧,并又去参观了北影厂。

1964年,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牛原以中日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成员身份访问中国。图为在天安门楼上。左起:中川一政、牛原、木村伊兵卫、白石凡、土岐善吕、郭劳为、中岛夫人、中岛健藏。
当然,有来就有往,接待起中国友人来,牛原也是分外热情。就在他1955年首次访华的第二年,老友欧阳予倩与梅兰芳等人组成的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他当然不能错过机会。
1962年,以司徒慧敏为团长的中国电影代表团首次访日时,牛原也出现在了接机的人群中。总而言之,在许多场合都能看到牛原热情的身影,这也让他成为了新中国电影人最熟悉的日本友人之一。

1962年4月,以司徒慧敏为团长、袁文殊为副团长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团一行11人访问日本。图为与部分团员合影(摄于Palace Hotel前)。左起:赵丹、牛原、秦怡、森川女士。
纵观牛原虚彦的一生,他导演的影片在艺术上显然远远达不到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等诸多大师的水准,实际上他在技术与创作理念上的突破要大于影片本身,如早期参与创作的《路上的灵魂》、试验国产胶片的《急行列车》、在彩色片上进行先锋性尝试的《虹男》(1949)等,其远见非普通导演所及。
而他对日本电影的贡献,更多是在教育以及对外交流方面,对日本电影人才的培养,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应该庆幸当年那个东京帝大毕业的精英毅然选择了做卑微的「河原乞食」,否则,也许政界只是多了一个平庸的政客,而电影界却损失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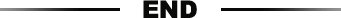
往期精彩内容
他是好莱坞历史上最伟大的歌舞片大师(四)
这是一代人心中最经典的日本动画,和高达、EVA齐名
这个人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电影摄影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