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文化纵横》公众号的一篇文章,主题为“公园北京”的现代性。文章探讨了北京公园的现代转型,包括公园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公园与近代知识分子交游集会的关系、北京公园的特色以及北京与上海在公园建设方面的差异。文章还提到公园作为现代建置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休闲游览的空间,更蕴含了保育身体健康、规范社会行为以及输入现代知识的启蒙价值观。
文章讨论了北京公园的现代转型,这些公园基于城市自身的属性各有不同。北京作为古都,其公园多以帝京遗产为基础,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意味。公园为所有人平等地提供了宜人的休憩与交往空间,并鼓励市民锻炼身体、规范公共行为、宣传现代知识。
公园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是近代知识分子交游集会的重要场所。新文学流派、文化启蒙运动、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的固定活动场景之一,便是北京那些王公贵族曾经嬉游的传统园林。公园为现代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文章提到近代北京与上海在公园建设方面的差异,虽然两座城市都有现代公园的出现,但上海出现了私园开放的潮流,拓展了公共空间。而北京则未能出现类似的现象,这反映了两座城市公共空间性格的差异。
↓ 进入公众号
点击右上角“...”设
置星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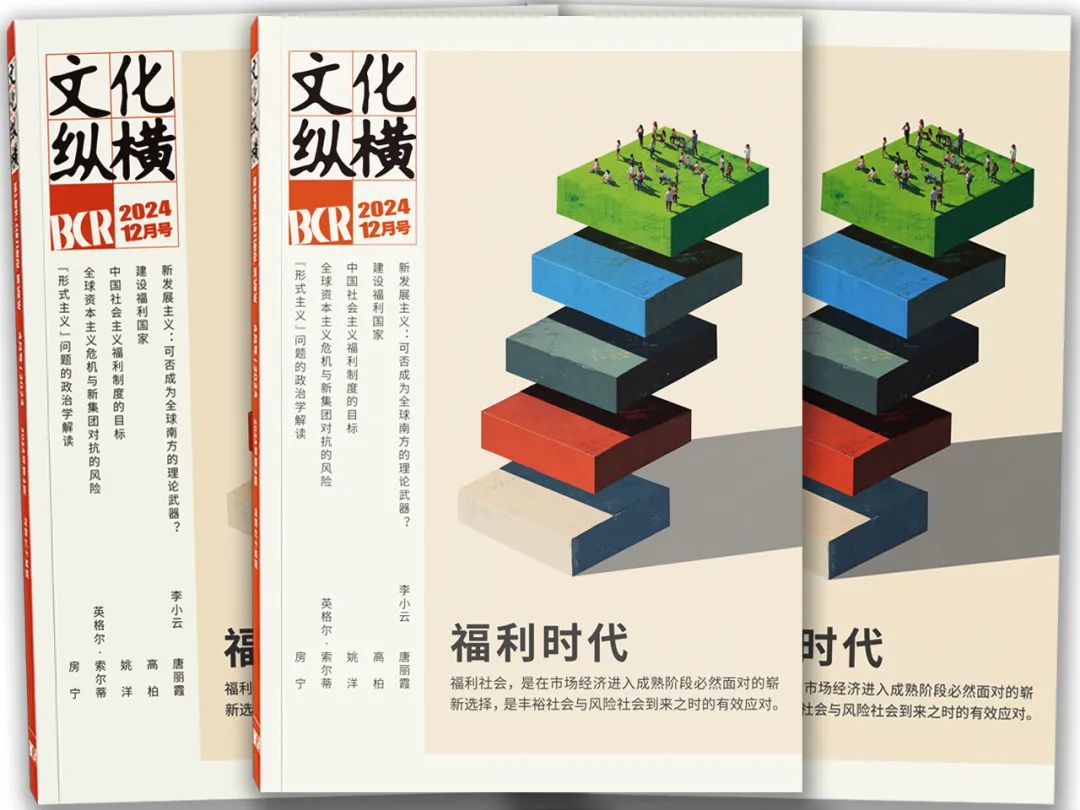
2024全年
6期一次
发货
,看得爽快,更享折扣
购买2025/2024全年
赠送文创周历 (仅剩133份)
2024+2025双年、2025+电子刊,
组合下单更优惠
【导读】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公园,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城市的
建置
。
公园之“公”,对应于现代国家的“公”民,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意味。
由于近代城市市民的居住环境
普遍
简陋,公园为所有人平等地提供了宜人的休憩与交往空间。
以公园为线索,可一窥中国城市生活的现代转型。
上世纪初,我国各大城市在规划中开始
引入西方的公园理念,且常在公园中设置图书馆、演讲台和体育场,意在鼓励市民锻炼身体、规范公共行为、宣传现代知识。
不同城市的公园,基于城市自身的属性又各有不同。
北京作为故都,其公园多以帝京遗产为基础,上海的公园则以租界兴建的西式公园为主,辅以一些对社会开放的私人园林。
不仅如此,公园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是近代知识分子交游集会的重要场所。
新文学流派、文化启蒙运动、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的固定活动场景之一,便是北京那些王公贵族曾经嬉游的传统园林。
而对于平民来说,由于门票不菲,仍旧更习惯去各类寺观中休闲游乐。
因此,
北京的公园很大程度上并没有那么“公”
,而是悬浮于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上的。
与此相比,
上海诸多私家宅园向公众免费或低价开放,倒是使这座城市更具有公共性了。
本文为
《文汇报》
2023
年
6月11日
刊发的文章,原题为《
“公园北京”的现代性》,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近年来民国北京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热点。相对于上海等沿海口岸城市而言,作为古都的北京历史遗产更为丰厚,现代转型也更为复杂。但也正因为此,对于探讨中国城市的现代经验来说,北京研究或许包含着更丰富的理论潜力。出于这样的自觉,不少学者尝试通过对民国北京史的深入考察,探讨不同于西方主导的都市现代性的“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林峥的《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
便是这一努力的最新成果。
作者在“绪论”中明确提出“公园作为一种方法”来探讨北京之现代性的独特意义。
清末至民国年间,一系列皇家禁苑相继开放为公园,这种对帝京遗产的转化、改造与利用,最典型地体现了近代北京对待传统的态度:
“不是将‘老北京’客体化、博物馆化,而是将其纳入‘新北京’的日常;过去与现在不是一刀两断,而是过去生长在现在之上,获得新的生命。”
全书围绕这一思路,选取万牲园、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城南游艺园和陶然亭五个个案,生动地展示了近代北京公园中新旧交融与互动的图景。
▍
“以游乐之处,养成社会精神”
北京的公园既多以帝京遗产为基础,它们多少继承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国家维度。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开辟社稷坛为中央公园,便充分考虑到它对于民国首都的象征意义,不仅选址“当九衢之中,近接国门”
(《本园创办之经过》)
,开园日期亦有意定在双十节这一天。此外,民初北京的公园开放运动本身亦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主持中央公园建设的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同时也是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中央公园董事会中,政府高官亦占据主体地位。而在中央公园之前,1907年在三贝子花园基础上创办的万牲园更是清政府主导规划的产物。这是近代意义上北京的第一座公园,也开启了鼎革后皇家园林坛庙开放的先声。
作为自西方引入的现代建置,公园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休闲游览的空间,更蕴含了保育身体健康、规范社会行为以及输入现代知识的启蒙价值观。万牲园创立之初,便包含了“以游乐之处,养成社会精神”
(《论开博览园事》)
的用心,并有意与“国政之维系”联系起来。中央公园也明确以“市民的精神,日见活泼;市民的身体,日渐健康”
(《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与未来》)
为建设的目的,将人的身体与精神纳入政府管理的范围。
公园里设有图书阅览所、网球场、音乐堂等多种文体设施。1925年以地坛为址兴建的京兆公园,更是将公园的教育功能发挥到极致。园内建有“世界园”,地上绘制世界地图,游客入园后可对世界大势一目了然,另外还设有通俗图书馆、演讲台和公共体育场等。凡此种种,都可以明显看出主事者的启蒙诉求,体现了他们自上而下的教化眼光。
《公园北京》一书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聚焦特定人群对不同公园的各具特色的使用,以此结构全书。
作者选取五座公园,与传统士绅、新文化人、新青年、普通市民、政治团体这五种人群的生活及表现一一对应,由此呈现与分析近代北京公园的多种功能。不难看出,除了昙花一现的城南游艺园外,其他公园的使用者带有明显的精英色彩,彼此之间亦有重叠之处。

1930年代,中山公园凉棚茶座
▍
从公园茶座到《小公园》副刊
在这五所公园中,中央公园与北海公园均与新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央公园的茶座——尤其是著名的来今雨轩——是民国北京新文学最重要的文化空间之一。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志摩等新文化人,均是中央公园茶座的常客。
在新文学史上,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即在来今雨轩举行。1923年起,胡适、徐志摩等定期在中央公园茶座聚餐,成为后来新月派的雏形。到了三十年代,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定期在来今雨轩举行聚餐会或茶会,召集京派的成名作家或后起之秀谈文论艺。
饶有趣味的是,由萧乾主编、主要面向文艺青年的《大公报·小公园》副刊,有意识地将公园中的茶座搬到报纸版面上,从中发掘有资格参加“线下”聚会的年轻作者,从而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空间,与中央公园形成同构的关系。
公园茶座与报纸副刊分别作为物质的空间和隐喻的空间,彼此支援,相互生发,共同成为酝酿京派文学的温床。
 中央公园(1928年更名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旧影
中央公园(1928年更名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旧影
中央公园吸引京派文人,得力于其便利的位置和清幽的环境,北海公园在这两方面亦不遑多让,且因其毗邻北京大学,更受到新青年的青睐。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及其周边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中心,由于中央公园已为上一代的新文化人所占据,1925年新开放且更契合青年学生的精神气质与审美趣味的北海公园,遂成为他们的领地。
《公园北京》别具只眼地揭示了北海公园与以“新青年”为主体的新文学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后者赋予前者以诗意的乌托邦色彩,前者则帮助后者确立某种群体性的精英身份”。
北海公园作为审美乌托邦的意象,恰恰提示了新文学的普遍主义取向。
这种超越性的文学想象,也暗示了公园与北京本地生活之间疏离乃至暌隔。
 北海团城,
佚名,约摄于1940年代
北海团城,
佚名,约摄于1940年代
书中专章讨论的另一处人文名胜陶然亭,也与新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陶然亭地处宣南,是清朝京师士大夫结社雅集的胜地。民国以后,伴随着士大夫文化的衰歇,陶然亭逐渐荒废败落。
然而在五四新文化感召下有志于社会改造事业的革命青年,却看中了因偏处一隅人迹罕至而便于展开活动的陶然亭。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进步社团多次在此召开会议,互通声气,彼此联络,在革命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饶有意味的是,以陶然亭为中介,早期革命者亦暗中接续了传统士大夫的经世关怀,发展出一种新型的超越北京本地的普遍视野。
陶然亭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高君宇与石评梅凄美而不失壮烈的爱情故事。英年早逝的共产党人高君宇生前常与女作家石评梅到陶然亭散步,两人去世后先后安葬于此,成为陶然亭新的风景与典故。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曾指出中国的园林名胜保持着丰富的符号学特征,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清代陶然亭即以香冢、鹦鹉冢等墓葬遗迹闻名,墓碑成为此地独特的文化符号。高石墓在汇入这一传统的同时,镌刻进了不朽的革命记忆。职是之故,1952年陶然亭成为建国后北京兴建的第一所公园,并很快成为革命纪念的胜地。
无论是寄寓于北海的新文学想象,还是铭刻于陶然亭的革命记忆,都超出了北京自身的社会生活图景。
北京公园的创建者和使用者,拥有着不受地方限制的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视野,这使得北京的公园在很大程度上悬浮于这座城市之上,这也提醒我们去思考它们的“公共性”的限度。
“公园北京”延续了清朝帝京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北京在地的一面多少受到了压抑和遮蔽。皇家禁地开放为面向公众的公园,凸显了全新的政治价值理念,但象征意义实际上大于现实实践中的公共性。
在实际运作中,公园不菲的门票费用和种种规范性的秩序要求,往往将普通市民排除在外。
▍
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秩序
实际上,在现代公园诞生之前,北京城并不缺少满足平民休闲游乐之需要的场所,尤其是城内外的各类寺观,往往集宗教活动、庙会节庆及游赏宴乐等功能于一身,成为北京市民最爱光顾的地方。更有意味的是,现代公园依托全年一贯的星期休息制,因而主要服务于国家公务系统中的官僚、教师、学生、知识分子等新兴群体,而北京旧有的游玩之地则带有鲜明的季节时令的色彩
(参见鞠熙《民初北京公园理念与传统公共空间转型》)
。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秩序。进入民国以后,伴随着现代公园的兴起,北京传统的游览娱乐空间日渐凋敝。1935年,金受申撰写长文《北平历史上平民游赏地纪略》,感慨“时过境迁,昔日胜迹,今为丘墟;昔日禁掖,今则阛阓”。尽管如此,诸如什刹海这样的去处,虽然杂乱不堪,仍是市民消夏的首选。就在同一年,师陀在《什刹海与小市民》一文中写道:“倘若拉住一位‘北京’市民,问北平地方那里顶好玩,他的回答一定是什刹海而绝非‘中央公园’。”什刹海正是金受申笔下的“平民游赏地”之一。
 北海金鳌玉蝀桥,
阿尔方斯·冯·穆默(Alfons von Mumm),摄于1900-1901年
北海金鳌玉蝀桥,
阿尔方斯·冯·穆默(Alfons von Mumm),摄于1900-1901年
在时间维度上接续并转化帝京遗产,在空间维度上悬浮于本地普通市民生活之上,“公园北京”向我们展示了其现代性的复杂面向。若与近代上海做一粗略的比较,其中的丰富意味或许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
上海是中国最早建有现代公园的城市,以1868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创建外滩公园为肇始,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租界共建成十五座公园。这些西式公园成为上海都市现代性最典型的代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华界才开始规划和建设公园。然而
在清末至辛亥前后,上海出现了一股私园开放的潮流。豫园、张园、愚园等私人花园纷纷免费或略收费用对社会开放,成为知识分子交游集会的重要场所,拓展了近代上海的公共空间
(参见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
。这一现象既应时势而生,也植根于本地的土壤。
晚近的研究表明,与过去的想象不同,中国的私家园林有着悠久的开放传统。尤其是明代的江南园林具有相当的开放性,成为“园主向公众展示财富和品位的重要手段”
(柯律格《蕴秀之域:中国明代园林文化》)
。近代上海的私人花园延续并改造了这一传统,虽然使用者亦以绅商等精英群体为主,但他们与本地市民生活却有着更紧密的联结。
其实近代北京亦不乏私家宅园,但却不曾出现类似上海的私园开放现象,这其间的差异透露出两座城市公共空间的不同性格
,也提示我们进一步思考“公园北京”的现代性的独特意义。
本文原载《文汇报》2023年6月11日,原题为《“公园北京”的现代性》
。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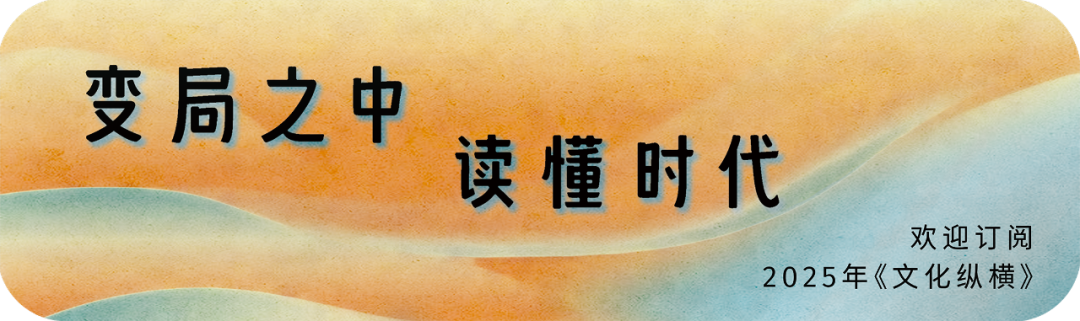
订阅服务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