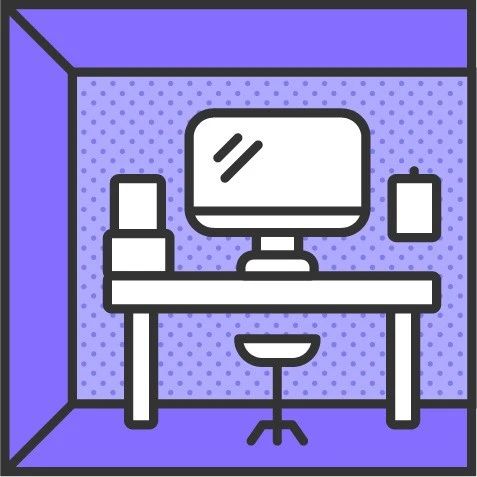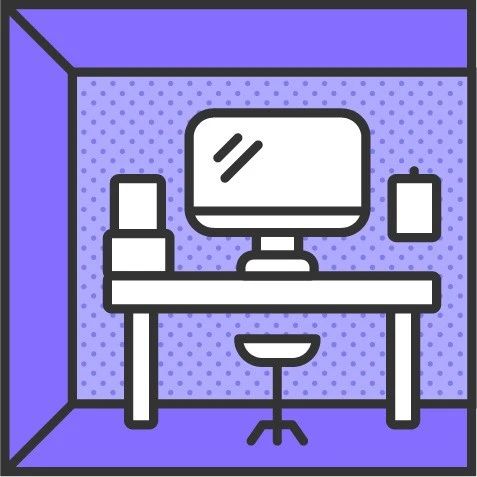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50多年的学术生涯基本上都是在英美精英大学出任要职。其出版于2021年的自传《四海为家
(Home in the World)
》获得学界和大众的广泛好评,中文版近期在内地出版,同样广受注目。
森的优秀和杰出,即使不是世界公认,也是少有人反对吧。然则,在赞赏之声充塞,还有众多赞赏者趁机塞入私货话语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唱唱反调,以此表达对知识的尊重,以及在根本意义上是向作为学者的他致敬。
关于饥荒理论与历史
森的学术论著极其丰富,其中关于饥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理论,聚焦于赋权问题,可说是其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石。首先是论断饥荒往往是因为分配、配给上的“赋权失效”
(entitlement failure)
,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粮食供不应求,或者说前者往往远比后者严重。进而论断,如果信息能够自由流通——如果存在能促使信息自由流通的能力即新闻和言论自由、以及相应的动力即和平的政治竞争——,那么,赋权失效本来不会出现,饥荒本来可以避免。
这个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毕竟,绝大多数现代社会的政治正当性都是来自人民主权原则,不可能明知存在赋权失效还置之不理、任凭饥荒发生。然而这也只是形式主义的逻辑上的道理,信息自由和竞争性政治能否以及如何形成,对于免除饥荒究竟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
(即是说是否存在可为替代而起到同等作用的政治安排)
,这始终是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
森将中国的大跃进与印度西孟加拉的饥荒并列作为其理论的范例,默示1950年代中国和1940年代印度的政治环境的共通性,这是极为可疑的做法。就新中国而言,自建国伊始就面临围堵、侵犯、胁迫,总之是极度严苛的生存环境。当时相互纠缠的台海危机、从东欧解冻风潮传来到百花齐放再到反右、庐山会议、中苏争执和角逐等等,正是这个环境的体现,舆论一律走向极端自有其历史特殊性。所以大跃进不能视作无事生非,毕竟对抗性、压迫性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不可能有和平竞争的国内政治;随后的饥荒即使本来可以避免也并不能归因于欠缺森所认定的制度元素,毕竟这种灾难在70多年来的中国是特例而非常态。
形式主义道理很容易变成神学,就是自以为跨历史时空而普适,无视信息自由和竞争性政治需要物质基础,也同时有其功能限度以及物质代价。对历史的无视,这不仅是知识上傲慢,政治上其实就是对既有的世界范围的霸权和压迫性的默认兼掩盖,这是很多森的理论的应用者的通病,他自己又是怎样则必须详加考量。
关于应对灾难的政治经济学
赋权失效理论不仅是关于饥荒,而是作为关于应对灾难的政治经济学的普遍理论。最具典范意义是全球新冠瘟疫及其防控,三年期间世界范围的主导舆论套用森的理论达到极致,在明白无误的抗疫失败这个不利现实面前,更加要宣传自由主义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最优论。
然则,就理论的应用而言,至少在三个关键节点上必须经受质疑、挑战。
一是无视信息与知识的差异,即,无视病毒的演变和影响机制,是惟有透过集体的学习和发现才逐渐从“不可预期的完全未知”转为“部分可预期的部分未知”。信息不存在或被曲解就将其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自欺欺人。
二是无视这种学习和发现是集体行为、一个集体过程,即是说所需要的是合作性政治。从而,将竞争性政治推到至高无上地位,将其任何对立面一概斥之为威权甚至暴政,这也还是自欺欺人。
三是无视灾难的强制性,以为个人化的“自由地选择”
(free to choose)
以及相应的政治竞争必定是应对瘟疫的最优模式,而现实结果却是走到对立面的“自由地丧失”
(free to lose)
。归根究底,这是因为应对强制性灾难需要集体行动,需要的是建立在合作性政治基础上的权威、决断。
不能说森的应对灾难的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大流行的实际经验面前破产了,能够判断的是,那种神学式的理论应用确实是傲慢地无视上述的瘟疫和抗疫的特殊性,结果就是其种种断言被事实胜于雄辩地驳倒了。
关于“自由就是发展”以及师生之争轶闻
“以自由看待发展”论——或者说“自由就是发展”论——,这应该是森的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思想的逻辑总结、归宿。按照这个理论,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又是发展的手段,前者是建构性质,后者是工具性质。
有一种对这个理论的阐释,强调自由与发展的分离甚至对立,说森的意思是自由优先,甚至是宁要自由不要发展。顺带一提,这个阐释相当于曾经流行于香港社会尤其是反对派政治圈的格言“猪的权利”,即,不以
(他们所理解的)
自由为至高准则的发展就是毫无价值。事实上,多年前森到访香港,当时对此关注的本地舆论就是很自我感动地宣扬这个阐释。
然而这个阐释未必符合原意。作为一个印度知识分子,森必定是很熟悉甘地的格言“贫穷是最恶劣的暴力”,由特定的历史环境
(尤其是特指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所导致的贫穷,本身就是自由的对立面。而且,很受森的理论影响的联合国建立的人类发展指数,其三大组成要素是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生活标准,前两者是建构性质的自由,后者则是明白无误指向经济发展
(联合国是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
,就是说发展本身就是自由的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