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作家。
1935
年出生,大江健三郎
10
岁时,日本投降,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新宪法的实施及民主思想教育,对他日后反对侵略战争、关注社会问题及人类命运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江健三郎的很多小说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或者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有家人朋友的影子,因而更令人瞩目
。1994
年,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宣称,大江健三郎
“
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幻想世界,浓缩了现实生活与寓言,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扰与怅惘
”
。

大江夫妇和长子大江光在富良野(大江夫人绘)
大江健三郎作 许金龙译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
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
上面这节诗,从我年轻时和它邂逅以来,虽然其透明的意思并不能经常显现,但对于我实在非常重要。并且,最近我有了一种体验,一束新的光芒洒进我和它的关系中,于是我决定写一篇短小的故事。诗作者的性格,似乎不是大声张扬一类的,这在作品中也看得出来。我也知道,诗人死后,有一些研究者和他一样以令人钦佩的沉静态度注释、编纂他的遗作,但在我们这个国家的风土里,为数更多的评论家不断发出异样的共鸣,用扭曲的浪漫主义语调追怀作者,所以,我也就没有向人说起自己对这首诗的理解。
本来我相信,那么年轻便和这首诗相遇,那时候我已经完全理解了它。因此,对于研究这位诗人的著作,我既无关心的能力也无留意的余暇,甚或可以说,我是有意识地回避那些权威性的解释(至少在某一段时间里是如此)。那期间,我对这首诗的认识固执得无法更改。而现在我则对柳田园男派的教育体系心仪不已:年轻时追随良师“学习”诗的读法、用身体的感觉“记忆”,更在灵魂中“感悟”……
谈到年轻时候我在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和这首诗的相遇,以及留下的深刻印象,首先要说说那位诗人在上面两行诗后述说的童年往事(诗人那时只有二十多岁,却把这首诗当做“老年人的诗”来写,我觉得,这就是同为少年的我被吸引的原因)。
每次到一位住在深山边缘的朋友家去玩,他总是面对山坳吹着口哨,唤来黄鶯,让我听黄鶯唱歌。不久朋友到市里的医学院读书,直到两人都头发斑白的时候,我才和这位已经在城里当了医生的朋友重逢。但是,说起这件往事,他却说已经想不起来了。
但(我的灵魂)记着
并且,一首连我也不敢相信的诗篇
涌到我的唇边
为了你的老年
我把它
记下
少年的我读到我以为是这样构成的诗句,体味到了迄今为止通过印刷品从未感受过的激烈感情。身体里燃着火球,那热气嗤嗤蒸腾,眼泪像水珠一样喷出,茫然不知所措……
确有此事,我深有感触。那是新学制高中三年级的暑假,我回到也是位于深山边缘的家的事情。现在翻开这位诗人的年谱看看就明白,那年七月,不知为什么,我本能地被创元社出版的丛书中的这部诗集所吸引,立刻就去买了回来。被狭细的溪流分割开的栗子树林里,布谷鸟的啼叫,让我直接想起此前回乡时听到的嚣鸣。在这里,也有一位会巧妙地唤引黄鶯,并且从山谷的植被到宇宙的构成都能给予我包罗万象的指导的朋友离开了村子。本来我也到城里去了,却觉得朋友离开村子不太应该。以后我们无疑也会相逢,相互扬起斑白的头谈话的时候,朋友会承认把当年我告诉他的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吧。尽管他会微笑着说:想不起来了……那时候,我能够怀着沉静的自信回答说:但(我的灵魂)记着么?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可是……
这首诗的每一个字的写法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虽然我按照在新学制教室里养成的习惯,非常熟练地把小时候按正体字记下来的汉字改换成了当用汉字①,但我确实可以感到,诗人所使用的汉字和假名,每一个都是不易移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为自己的老年而写下的东西……
鶯,在中考用的数学草稿纸上写下这首诗然后去打量的时候,我曾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文字,翻开直到父亲去世之前一直放在他枕边的字典查看,上面却只写着“小鸟的名字”和这个字的读音。我很失望,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字,翻开一看,果如所想,从那以后,字典便开始对我有了特殊的意义。
螢,环绕着火
+
“虫”,意思是发着光做环状飞行的虫。那么,鶯不也像是环绕着火,发着光,一边歌唱一边做环状飞行的鸟么?前面说到的那个春天,在栗树林和小河中间的竹丛里啼鸣的篱完全就是这样的……

现在,通过在自己耳边复苏而又瞬间消逝的嚣鸣,我理解了鶯这个字几千年前的字形和发音,以及外国人对此所做的解释。我觉得,就像以前我通过暮色降临时分河岸上肯定飞起的片片流萤的意象媒介,领悟高深的秘密一样。我所领会到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还无法表达,但那不会是别的,应该是和我抄录下来的这首诗密切相关的东西……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
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
现在,我已经渐入老境,如果用自己的语言把十八岁时所感受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可能就是这样的吧——像一只萤火虫,朝着超越个体而又包含个体(我的灵魂)的聚光点飞翔,我由此而充满活力。这样的事情,很早以前,和(我的灵魂)密切相连的自我已经清楚;而这以外的事情,只要是(我的灵魂)以外的存在个体,就永远不会明白……
在那以后的第十个年头出生的大儿子,因为头盖骨缺损而造成的残疾,使他六年来不能通过语言和做父母的我们进行交流。儿子最初积极地发出自己的话语,是通过鸟的鸣叫这个中介。他出生以后,虽然一直沉默不语,但听觉是很敏感的。我和妻子注意到收音机和电视里一响起作为效果音的野鸟叫声,儿子就会表现出一些细微但很新鲜的反应,于是,就用录有野鸟鸣叫的磁带代替了摇篮曲。那时,一位外国诗人住在东京,我们颇有交往,最近的韵记忆发生了一些混乱,在寄给我的圣诞贺卡上竟这样写道:你的家在森林旁边,经常有鸟的叫声,真让人怀念。
录有野鸟叫声的磁带,是
NHK
技术部录制的,每一声鸟叫后面,都由一位女播音员以非常平静的语调播报鸟的名字。当然每次都是把鸟叫和播音连在一起听。这样过了两三年的时光,我们带着仍然沉默不语的儿子到群马县北轻井泽的山间别墅去。妻子打扫房间的空隙,我把儿子扛在肩头,站在初夏时节高原上的桦树林里,暮色宁静而浓重地垂下。不远处的小湖,是法政大学的学者们在二战以前组织的工会把从湿地流出的小河堵截起来而形成的。在这很有些来历的古老的别墅区,我们也有幸被允许建造了一座山间别墅。
在那个人工湖里,不断传来秧鸡的啼叫。我正这样想着的时候,那一瞬间,肩头上的儿子发出了清澄的声音:
是秧鸡呀!
从那一天起,我和妻子开始用录音机和儿子游戏,在播音员说出鸟的名字之前按住暂停键,让儿子回答。有时还到能够直接听到野鸟叫声的地方,享受儿子告诉我们这个那个鸟名的乐趣。儿子似乎提不起特别的兴致,但从声音里感觉得到,他是在凝神倾听并认真思考之后才告诉我们的:这是山雀,这是燕雀,这是三光鸟呀……
在我听来,大多数的野鸟叫声全都一样,啊,鷥!在儿子开口之前突然听辨出来的时候,我喜不自禁,又抑住几乎脱口而出的冲动,和着儿子的声音说:这是鶯呀!
那样的时候,我常常回想起二十岁以前,自己被那首诗深深吸引、翻开字典查阅鶯字正体的情景,进而又想到那位少年时代的朋友像诗里所写的那样,用我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口哨(我感觉他那尖得刻薄的唇形自身就含有音色的秘密)呼唤黄鶯的往事。
于是,我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在诗人和他的那位朋友的少年面影旁,我和我的朋友、儿子(既然我和朋友都还是少年,和儿子在一起生活是很不合情理的)一起坐着,像重叠的赛璐珞画一样。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我明白了,这一行诗的意义就生存在我的内心和身体里,而那时早已死亡的友人的灵魂则像鶯鸣一样漫山遍野闪耀着光芒,我自己的灵魂和儿子的灵魂恰相一致,与此呼应,这就是诗里所说的但(我的灵魂)记着……
另一方面,即使青年时代过后,我和因事故不幸死去的朋友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心理上的分歧,儿子也很明显地以和我全然不同的性格成长着。就算是由一个记忆连接起来了,那把友人、儿子和我从内部系在一起又从外部覆盖起来的令人怀念的东西,称之为(我的灵魂)无法言说。作为一个孤独的灵魂,我也加入其中。
儿子进了小学的特殊年级②。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不可理解,那时他既没有发作癫痫,动作也很灵敏,所以过了一年就可以独自上下学了。空闲下来的妻子便在房前房后的空地上种植了很多和“杂树”名称很相称的小灌木。从高原边缘的稀疏林木一直延伸到邻居家的绿色通道,和我家的小灌木连接上了,于是庭院里开始有小鸟飞来。绿眼鸟,山雀,鹎鸟,特别是鹎鸟,经常出现。和其他小鸟相比,显得粗野的兰鹊也来光顾。早春时节,盯着绑在石榴树初露嫩芽的浅墨色柔软枝条上的兽骨脂,黄鶯也显露了身影。
儿子不久以前还对录有野鸟啼鸣的磁带十分热衷,可对真的野鸟叫声却毫无兴致。用三棱镜片矫正以后眼睛仍不太正常的儿子。要看到在那细网状的树枝之间快速跳动的小鸟当然是很难的,但小鸟经常是停在庭院里的树木上啼叫的。
清晨,我看到几只山雀匆匆飞来,像阵雨一样急促掠过。第二天早晨仍然如此,我深感奇怪,过了几天,一个朝露未消的清晨,我抢在山雀前头一看,瘦弱的杂树上密密麻麻地缠绕或悬挂着的小青虫,让我吃了一惊。此外,妻子也经常给小鸟补充一些饵食。
就这样,小鸟日渐增多,并不停地啼鸣,儿子却没有对此表示出兴趣。
义幺听磁带记住的野鸟叫声,可能和这一带的野鸟叫声的音高不太一样吧,那准是在深山里幽静的地方录下来的。我说。
——不管是在北轻还是在伊豆,儿子的耳朵都是那么灵敏,连老远老远的夜鹰叫声都……
妻子带着一种很怀念的情绪回答,其中也表示出对我打诨式的支吾其词的微妙批判。那时候,儿子的身体和心理明显处于向另外一个层面移动的阶段,妻子首先表现出了不安——我的内心似乎也有共振——所以,那意味深长的对话就留在了记忆里。
总之,妻子一方面为儿子升入特殊年级而高兴,另一方面,也在体验儿子倏然间把多达几十种的关于野鸟的认识全部失去的丧失感。他的感受性好像被笼罩上了特殊的光环——用一种和超越了我们日常经验的东西相关联的方式。如果确实如此,就让儿子留在家里,不去打搅儿子和小鸟啼鸣共度的时间就好了。我们是不是没能准确理解孩子在和小鸟的声音一起成长(用妻子的话说,就像阿西西的圣方济各③似的)期间发出的话语呢?
可是,当我从搁置已久的磁带中选出飞到院子来的野鸟叫声想让儿子重新学习的时候,妻子好像担心将会出现不自然的逆转一样制止了我。儿子因为和那些表面看来大体相似、细细观察又各有不同残疾的朋友们的来往,特别是因为他在教室不断听到调频广播节目,所以,便急速地表现出对人工制作的音乐的兴趣……
是一个星期天。和儿子一起在餐厅时,黄鶯突然叫了——只有我“嗯?!”地反应了一下,妻子欠身看了看那个小小的鸣叫者是否啄食到了用麻绳绑在枝条上的兽骨脂,然后讲起了一个让人感觉可能是偏离了她的心中所想的故事。
过早辞世的做电影导演的父亲那时因为结核病而卧床度日,他给落到院子里、叫声特别好听的鶯起了个名字叫“小式部”④,我自己呢,则给一只还很幼小、在“皓皓开可”的叫声后面总要再加上一声,听起来像是“皓皓开可匹”的小鶯起名叫“可匹助”⑤。虽然还是小孩子,但我也感觉到,与父亲相比,自己的语言表现不够文雅……儿子呢,对鶯叫和我们的谈话都毫不关心,从那时起,他沉湎于周日早晨吉田秀和主持的好像永不中断的调频广播节目里播放的莫扎特。
也就在这一时期,我因为被京都的法国文学研究者
S
氏的一本著作感动而读了他所写的关于那位诗人的书。迄今为止,所有的导读者都对那首我以为极为重要的诗表示冷淡,这次我却读到了
S
氏恳切的解读。但那解读却颠覆了我从少年时代起形成的确信!
虽然这么说,但还是能够理解,作为那位诗人的专业研究者,大概只能这样解读,因为他坚定地按照刊印诗集时作品的前后顺序来理解,并把那首诗蕴含的思想联系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阐释框架里。
首先,
S
氏给这首诗和排列在前面的一首诗《毋宁说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赋予了一种关系。
人们歌唱
辉煌而短暂的日子
可是我并非如此。诗人继续讲述对他非常重要的隐喻——广阔延展在世界上的“泥沼”,通过他所喜爱的纪德的作品,这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我不歌唱
短暂而辉煌的日子
毋宁说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
而关于“鶯”的诗句,则是作为一位老人从诗人那里看到这首诗后所作的回答而写下的:是呀,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老人深信,住在山边的儿时朋友的灵魂,就是用口哨唤来的黄鶯。可是朋友却连那往事也想不起来了。所谓灵魂就是这样靠不住的东西。所谓(我的灵魂)是无法言说的。但(我的灵魂)记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那只鶯忘记了的,也正是(我的灵魂)……
按照
S
氏的解释,诗人并不相信灵魂的自发性,认为是来自外部的东西把乐器般的灵魂敲响的。毋宁说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灵魂外部光芒闪耀的日子造访我的灵魂,像把灵魂这个乐器敲响了似的,那就是他们在歌唱我的今天。不存在自发地唱出中心力量之歌的所谓(我的灵魂),可是(我的灵魂)记着作为乐器被敲响的歌……
此外,还有一首短诗(作者不详)作为被这样记忆着的内容附录其后。
S
氏提醒人们注意:最末两行字数相同,和前面的诗的结尾用意一致,是相互照应着的。
吞食水上的暗影
虽与花香和谐异常
音乐会却无尽无休
我被这种解释说服了,但幽深博大的寂寞也随之而来。少年时代那个特别的日子,身体里燃着火球,热气嗤嗤蒸腾,像水珠一样喷出的眼泪。难道那仅仅是一个对诗的语言毫无经验的少年误读的结果么?还有,死去的友人的灵魂,像鶯的鸣叫声一样漫山遍野地闪耀着光芒,我的灵魂追逐他的灵魂,相互重叠,又和智力发育迟缓只能理解野鸟叫声的儿子的灵魂相互映照,这样的感受,难道也只不过是建筑在误读之上的沙垒么?
通过
S
氏的文章,我获得了不曾达到的明晰理解,体味到了一种愉悦,而悄然涌到脚下的幽深博大的寂寞,其规模也是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朋友去世好多年了,过了壮年的我也离死不远了吧。剩下有残疾的儿子。那时候,本来就分崩离析的三个灵魂失去两个,一个残破,所谓(我的灵魂)之类,无论对友人、对我还是儿子来说,不过都是脆弱而不确定的东西……
这认识应该是正确的。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残存着“或许、或者”一类的留恋,并由此去寻找不易公开的通道,我感觉到一种恭谨的灵魂慰藉升腾而来。而且,受一种表现欲望的鼓动,我很想写一首诗,就用老人的语调:为了你的老年我把它记录下来。至于那个你是谁,则茫然不知……
这是发生在暮春时节的事情。为了送儿子去乌山的一家福利培训所,我们早早就出了家门。天空晴朗,巴士也不拥挤,几个一看就知道是刚刚入学的小学生表情都很快活。我抓住车厢上的管状扶手,一边跟儿子搭话:上培训所已经好长时间了呢,几年了?——四月十号就第六年了。儿子以他独特的正确表现方式回答道。
在电车中转站,并排站在被长长的石斧状上下行线包围着的月台上,我们不再交谈。下行线一侧水泥铺设的斜坡上,只有青苔和开放着的蒲公英,我所面对的上行线一侧的斜坡上,则簇生着青草和也在开放着的诸葛菜。少年时代,从自家旧宅整套的有朋堂文库丛书中拿出《通俗三国志》借给我,告诉我山谷河岸上茂盛的油菜科一年生植物是疏散到山里的城里人播撒、名字叫诸葛菜的,就是那位我称之为格兄的朋友。在那个月台上,我反复回味这件每年都会想起一次的事情。生长着青草的斜坡上并排站立着吐出细芽的光叶榉,从光亮的深紫色的枯壳里伸出长叶的朴树,坚固地缀满厚实花片的八重樱,在那对面,则有竹丛在摇曳窥望。从那高坡处马上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警报响了起来……朝那个方向上行的电车开进来了。
我想,就因为我侧耳倾听时产生了放心感,才忽略了儿子像突然发热似的异变的前兆(虽然急救医院的医生说过,身体整体舒缓地运动也是可以挽救生命的)。朝着那辆放慢速度要停下来的车身,儿子像被缓缓地吸引过去似的倾斜。我想从斜对面把他抱住,但动作比想法慢了半拍,一个巨大而沉重的东西把我耸出的肩和头部的一侧,就依那样的顺序一击,二击。我抱住儿子的身体,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很短的时间里,我感觉我昏了过去。
……伴随着浓重的怀念,我回到那个春天的一个瞬间:我和格兄非真非假地格斗着从庚申山的斜坡上滚落下来,头部被打击了一下。同时,又为心里明白自己是在努力不让儿子的脑袋直接碰到月台而感到安心。是一种分裂的感情状态……
随后苏醒过来一看,自己的两只胳膊什么也没有抱住,像枯萎了似的被放在身体两侧,并不冰冷的水汪在半边脸上,我用一只眼睛望到眩晕的晴空和遮在上面的黑色的头,也知道周围已经围起了窄窄的人墙。我想从水汪里抬起头,半边脸很疼,又害怕地停住了。我看到儿子胆怯地在我的额头擦拭着的整齐手指沾着红色污渍,也就明白刚才觉得是水汪的原来是我自己的血泊……
这样的话,在车站的站务员分开人群叫来急救车之前最好还是不要动弹。还应该鼓励仍在癫痫发作后遗症状态中的儿子,让他不要再摇动。于是我试着发出了细弱的声音,却似乎不能回应头脑里的念头,结果变成了非常滑稽的醉汉般的语气:义幺,义幺,好难受呀,究竟是什么呀。
随后,针对从斜上方的竹丛里传来的鸟鸣,很明显,还针对着比那更高层次的东西,儿子回答道:
——那是黄鶯呀。
所谓(我的灵魂)无法言说
我把那证据告诉你吧。
①日本政府于
1946
年规定公文、法令和报刊等使用的汉字,共
1850
字;后曾做过增补和调整,
1981
年改称“常用汉字”。
②日本一些小学为照顾残疾儿童而设置的特殊年级,一般把小学六年分为两或三个年级。
③圣方济各,出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亚地方的阿西西,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据说他可以对小鸟说教。
④式部:日本古代宫中对女官的称呼,明治时代
(1868-1912)
后期也曾被作为女学生的别称使用过。
⑤助(
suke
):在日语中作为接尾词使用时,多用于名词性词语后,使该词语人名化,并表示该人的某种特征。
(作者按:本作品从杉本秀太郎氏编著的岩波书店版《伊东静雄诗集》和筑摩书房版《伊东静雄》获得了教益,谨在此致谢。)
原载于《世界文学》
2000
年第
5
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相关阅读:
散文品读|大江健三郎【日本】:天皇用人的声音讲话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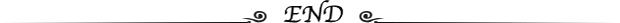
《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010-59366555
订阅微信:
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
[email protected]
投稿及联系邮箱:
[email protected]





